長期以來,蘇聯黨史都在講述這樣的觀點:11月8日夜晚即攻打冬宮勝利後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兩項最重要的法令——《和平法令》與《土地法令》,尤其是後者宣佈:“立即無償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一切土地屬於人民的財產,並把土地交給勞動者使用”。

據說這一舉措解決了千百年來勞動人民對土地的渴望,布爾什維克黨立即得到農民的擁護,進而導致了十月革命的凱歌行進。於是在國內戰爭遇到敵人反撲時,農民爲了捍衛自己的革命成果自願參加紅軍,成了革命堅不可摧的堡壘。
中國人對此容易理解,因爲根據官方教科書的解釋,土地革命是中-共革命勝利的主要原因,由於“解放區”的土改和“減租減息”獲得農民支持,才保證瞭解放戰爭勝利。這就使我們感覺到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十分相像。
但是俄國《土地法令》的敘述中有很多含混和語焉不詳之處,難道是布爾什維克一個黨派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嗎?是該法令宣佈以後農民才獲得土地的嗎?土地是“人民的財產”?什麼樣的人算“人民”?注意法令裏只說是“勞動者使用”,那所有權歸誰?是公有、集體所有還是個人所有?是以什麼標準分配土地的呢?這些問題現在仍好像是一盆漿糊。
實際上中俄兩國的土地構成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歷史上一直都是土地私有,平民地主的土地大都來自購買和繼承。而俄國地主的前身服役貴族的土地是國家劃撥公有土地以及連帶上面的勞動力的方式形成的,雖有少量購買土地但其基本土地構成是國家給貴族土地作爲徵戰的交換條件,俄國的兵制始終和土地聯繫在一起。俄語“地主”(помещик)一詞原意爲“主人”,並無漢譯中土地所有者的意涵。

在農奴制時代的村社制度下,沙皇把若干公社劃給某“主人”作領地,公社成員作爲農奴受其束縛供其役使,但這只是一種“統治-服從關係”而不是產權關係。18世紀以後哥薩克軍隊和普魯士式普遍兵役制興起,貴族兵役制的作用衰落。
宣佈,貴族的服役不再是強制性的,此後兵役和土地使用權相分離。此前農民對貴族的“勞役”關係並沒有解除,形成一種權利與義務不相等的狀況。農民們認爲貴族的土地本來就是屬於農民,爲了戍邊徵戰擴充版圖暫時讓貴族擁有使用權,既然不打仗土地就應該“物歸原主”。
1861年的農奴解放,農民的份地中又被地主割去大量的好地。因此“分貴族土地”在1861年後是一種民間共識,沙皇政府也多次商議如何解決土地矛盾,其實早在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後,沙皇與貴族的關係惡化,據說這個“反動沙皇”差一點就要剝奪貴族的“土地使用權”了。從19世紀70年代民粹派組織的“土地重分派”、“黑分社”這些名稱就可以得知當時“分田地”的呼聲有多高。

自由主義儘管經濟觀點傾向市場與私有制,但也反對以強權化公爲私。1905年立憲民主黨成立時就對農民宣佈說,“我們要辦的第一件事就是給你們土地+自由。”1906年新建立的俄國國家杜馬圍繞土地問題展開激烈鬥爭。農民議員團提出“勞動團104人”議案,要求國家剝奪“地主”。當時在杜馬中居優勢地位的立憲民主黨對此表示同情,他們在國家杜馬中呼籲要“糾正現存的土地分配不公正性”,要求通過立法無條件、強制性廢除大地產。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當時並無“平均地權”的理論。經典馬克思主義相信資本主義會消滅小農,代之以農業資本家和農業工人,農業資本主義化被理解爲自由私產破除“共同體軀殼”即私有化過程,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厭惡作爲傳統“共同體”的公社,支持私有化,希望加速農民分化。
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1885年勞動解放社黨綱對農業只有“唯一要求”,即鼓勵農民自由退社,而根本未提“地主”。至於“土地國有化”更是恢復“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反動主張。
普列漢諾夫警告:“人民專制”下的“革命”可能會造成一種“反動”的“政治畸形現象”,“有如古代中華帝國或祕魯帝國,即一個在共產主義基礎上的革新了的皇帝專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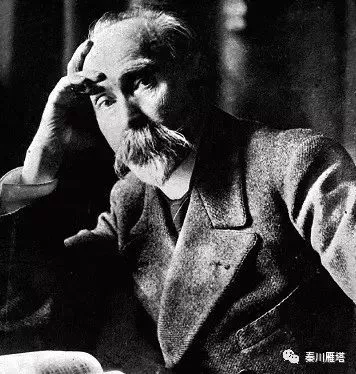
當時俄國杜馬中,只要稍微帶有左派光譜的黨派,從到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民粹派後續組織的社會革命黨、人民社會黨人以及農民黨團的“勞動派”,無一不把“公平、公正解決土地問題”視爲第一大要務。
據不完全統計大約有十幾個黨派提出:儘快儘早完成農民多年來的夙願——“收回割地”,所謂“割地”指1861年改革中被貴族割佔原公社土地,“收回割地”就是把這些土地從地主那裏奪回來還給農民。
當時就連那些被認爲是保守的右翼黨派也不敢放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原始鏈條的清白,因爲他們知道這些土地並不是合法積累起來的,只是強調“地主經濟商品化程度較高”,不要盲目摧毀,或者用社會震盪較小的國家“贖買”方式來化解這一社會矛盾。也就是說,從1861年以後“分地主土地”是一種全民共識的“政治正確”,不但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主張,該派甚至一直疏離農民運動。
俄國農民是自發地仇視地主,而他們在知識界的代言人是社會革命黨。1907年沙俄在鎮壓了民主運動後推行“警察式私有化”的斯托雷平改革,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又使1/5的農民成爲“獨立農場主”,導致農民兩極分化破產狀況嚴重,農民對地主的仇視發展爲對當局的仇視,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才意識到農民的情緒可用。儘管如此,列-寧一派仍然未能有效介入農民當中。列寧承認說,“社會民主黨人在土地使用形式的問題上……總的說來接受了民粹派關於分配土地給農民的主張”。
布爾什維克在二月革命前的最後一次關於土地問題的特別代表會議並沒有討論分地問題。更何況1917年以前,布爾什維克在農村只有4個支部,494名黨員,就是在走出地下以後的1917年農村也只有203個支部,4122個黨員,與在農村具有百萬之衆的社會革命黨無法匹敵,所以即便它想去搶佔農民運動的潮頭,也無法與之爭奪領導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到第三年,也就是1916年由於俄國在戰場上接連失利,民怨沸騰,沙皇權威削弱,沙皇政府不起作用、不能領導國家已經是人所共知的現象。在絕大多數農民眼中,籠罩在沙皇身上浪漫光環消散,基層法制鬆弛,各地已經自發地興起“奪地”運動,政府已無暇顧及農民搶佔地主土地的事件了。

如前所述,地主土地多來自國家的劃撥和1861年農奴制改革中化公爲私的“割地”,而私有農民土地則來自斯托雷平改革對村社的瓦解。這兩次專制制度下的化公爲私改革很不得民心,民間“開倒車”的“反改革”呼聲一直就很高。戰爭期間政府自顧不暇,民間自發地就出現了利用傳統村社剝奪地主和“富農”——斯托雷平改革中脫離村社的私有農民的浪潮。而這時地主早已成爲“死老虎”,要麼把土地交給管家自己逃往城裏成爲“不在地主”,要麼賤賣拋售土地把資金轉移到其他領域。
繼1905年的第一波奪地運動之後,1916年開始第二波分地高潮,各省的鄉委會要求:地主的、國家的、皇族的、教會的、政府的“全部耕地和牧場轉交給鄉委員”,並把“地主的所有農具、牲口和財產均應如數交給鄉委會支配”。皇權鬆弛後,農民提出來分配皇室土地、國有土地和大莊園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最重要的是恢復公社對獨立農民的權威,重新迴歸農村公社。
史料明確記載,當時湧現出的“自發奪地鬥爭”,對“貴族莊園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經過農村公社來組織和協調”完成的。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意志並不在於消滅地主的肉體,主要目的並不是“打土豪”,而是“分土地”,然而鄉委會約束不了農民的行動,農村每天都會發生“農夫對老爺實行暴虐”事件。但是有組織殺人的案例並不是很多,也沒有羣衆性“鬥地主”的“情感渲染”,除了土地,被農民拿走的主要是農具和農業設備。前沙皇官吏的土地因其政府倒臺而不受保護也都被當地的村社佔有。總體而言,比起中國的“暴力土改”程度不可同日而語。
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當然知道首先需要做的是分給農民土地。這是多年來反對派承諾過的主張!現在輪到他們第一次可以大展鴻圖圓農民的夢,怎麼能輕率行事呢?連列寧也承認“二月革命就已經向農民保證要給農民土地”。
臨時政府答應,土地是一定要分的,但是不能在戰爭狀態下毫無規劃的“亂分”,前方正在打仗時怎麼分?如果在全國丈量、統一規劃沒有出來之前任由各地村社自作主張分土地,擅自改變土地制度,勢必會造成農村和前線的雙重緊張和動盪,造成不同區域間的苦樂不均,將直接關乎到戰爭輸贏的結局。
於是新政府要求農民稍作忍耐,等到戰爭塵埃落定,等到臨時政府能站穩腳跟,就召開了立憲會議,進行了全國摸查,一定能夠完成俄國農民等待了幾百年的夙願。“臨時政府堅持認爲重新分配土地必須以慎重和合法的方式來進行”。

臨時政府針對農民自行佔有土地的行爲,在3月19日發表關於土地問題的決定中說:“土地問題不能用任何搶佔的辦法解決,……應當通過人民代表機關制定法律來解決土地問題”。它要求農民在法律的框架下有秩序有步驟合理地“分地”。
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革命黨人要求農民停止焚燒地主莊園和分地活動,呼籲“不要把土地社會化的偉大事業變成隨意私自佔有土地”。其黨魁切爾諾夫說,用非組織手段奪取土地是不幸的,他呼籲農民代表蘇維埃有組織、有秩序地分配土地。切爾諾夫反對各地“自行奪地”。他號召農民耐心等待一個合理合法的時機,不要在戰爭中帶來後方的“震動”。
1917年初在第一次全俄農民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社會革命黨同意臨時政府的主張,認爲“解決土地問題是將來立憲會議的事”,擅自行爲奪地、分地將會被視爲非法行爲。
此時,農民已經顧不了那麼多了,後來者唯恐叫別人佔了先機或者拿到土地者害怕得不到承認,於是發生了農民情緒的激進化的過程。絕大部分人贊同不經官方許可自己行使革命權力。據統計,86·6%的鄉農民執行委員會堅持革命立場,3·6%置身於階級鬥爭之外,9·8%委員會維護地主的利益。在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上臺執政前,農民們已經完成了總數爲16298起“土地”革命行動中的10210起。
也就是說,在列寧的“革命”一年前,在他還待在瑞士流亡地哀嘆此生可能再見不到革命的時候,對斯托雷平改革滿懷憤恨的俄國莊稼漢已經在後方“自發革命”、即展開了自發奪取和分配土地的風潮。“到了1917年秋天”即臨時政府末期,“農民騷亂已經遍及俄國縣份的91%”。不但對地主5800萬俄畝土地的奪佔早已告成,而且對退社農民土地的收回重分都已經接近尾聲。

早在十月革命的《土地法令》頒佈之前,俄國的土改就已經開始並完成了大半,這項運動既不是臨時政府也不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而是農民依託傳統農村公社組織集體行動,才造成如此大的衝擊。現在俄國學者普遍認爲,“在沙皇末期的1916年秋到1917年春,農民攻擊地主的行動已基本完成,而布爾什維克對此並無影響”。
然而,主張合法分地的黨派延誤了時機,叫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鑽了空子,當時黨內的策略是:“搶佔先機以換取農民的支持”。在1917年8月底的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才彌補性提出,在土地問題上承認“農民奪取土地的既成事實”。他們意識到,在這種情況下誰進行阻抗,誰將會喪失羣衆的支持,因此在革命動員過程中,要不遺餘力地擁護農民已經基本完成的“土改行動”。
鑑於革命後再沒有全國範圍內的“平均地權”,如果把十月革命前的這次大規模的土地調整看作是“土改”的話,我們可以說,俄國的土改先於革命,而且並不是布爾什維克主導的,是農民自發完成的。這是與中國土改最大的不同,它也直接導致了俄國的戰敗。
布爾什維克天花亂墜的畫餅,讓農民心馳神往,一下子被認爲是最理解農民的政黨,但是他們策動革命的宣傳目的達到之時,也就是許諾壽終正寢的時刻。就在1918年剛剛完成分地運動的農民,馬上就面臨着新政權“餘糧收集制”的殘酷打擊,他們這才感覺到之前的許諾與支持不過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