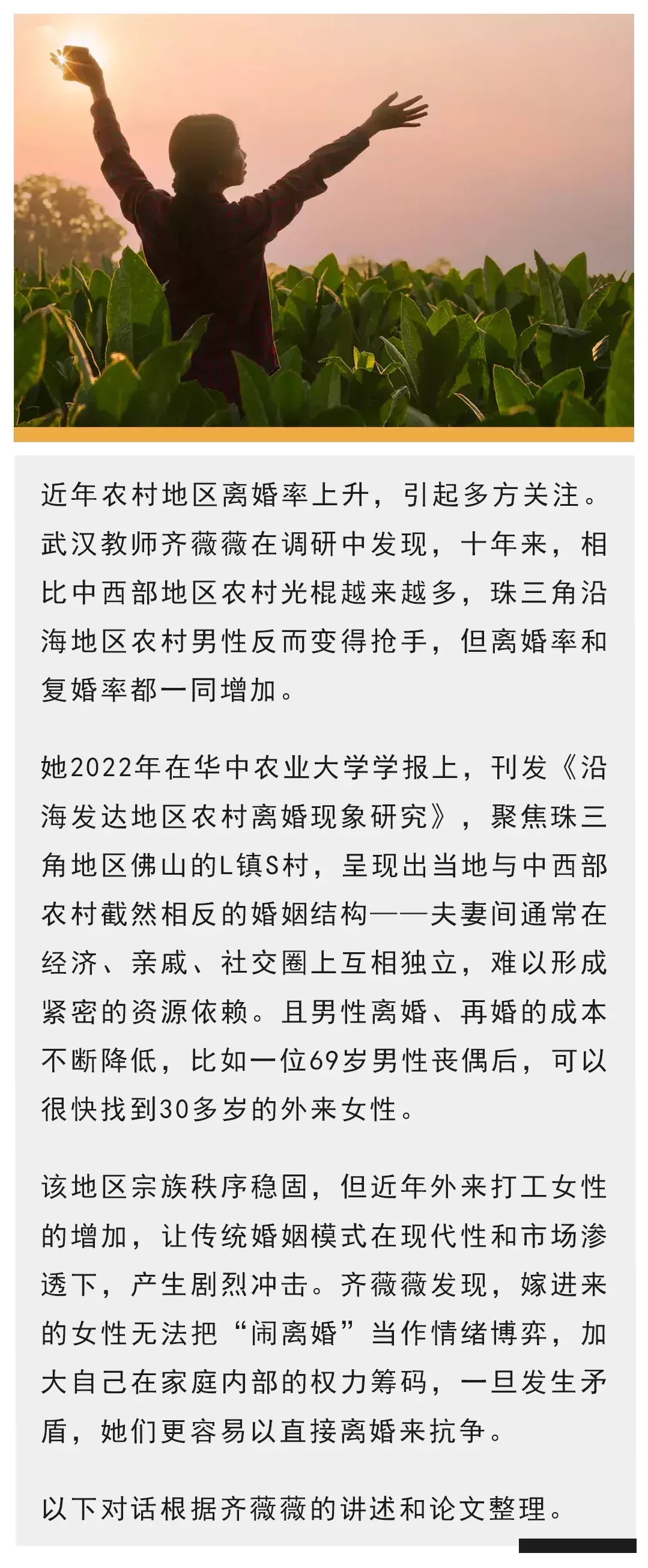
“男性離婚成本低”
問:爲什麼選擇S村做調研?在近年裏,當地的離婚率具有怎樣的樣本意義?
齊薇薇: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是“基層治理”,在讀博過程中做過數次村鎮模式調研,到S村之前,去過華北地區、中西部地區,大部分都是經濟相對落後的地方,所以我也想到沿海發達地區看看。S村2019年正在開展產業轉型,是願意接待我們調研團隊(由4名博士生和2名老師組成)的村子之一。
當地的離婚問題是我在調研中偶然發現的。相關機構工作人員告訴我,離婚現象越來越突出。我注意到,這裏離婚率升高的同時,復婚率也在升高,而且中西部地區男多女少,S村這裏的性別比是倒掛的。
當地的離婚率作爲樣本具有一定特殊性。因爲經濟發達,這裏的村莊實現了就地城鎮化,與中西部地區呈現鮮明對比。珠三角地區一直都有大量外來勞動人口湧入,而L鎮是全國最大的傢俱生產基地,外地來打工的女性居多,再加上延續下來的大家庭文化,又讓樣本具有珠三角地區村莊的共性——它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衝撞之後產生的家庭模式,這種衝撞必然產生不和諧、不穩定,與離婚率的升高有一定的關聯。
問:你在研究中提到這裏是“婚姻高地”,怎麼理解它的形成?
齊薇薇:在我們調研的2019-2020年,已經顯現出這樣的情況——外地女性很願意嫁到這裏,而本地的女性資源也不會外流,她們不願意找外地男性結婚,這就形成對本地女性的一個“婚姻擠壓”——適婚男女性別比失衡,導致其中一種性別的人口找不到配偶的情況。
因爲在這樣的情況下,本地男性既可以找外地女性結婚,又可以找本地女性,外地人口是本地人口的2倍。所以即便這裏是東部沿海地區的農村,但當地的婚配邏輯跟城市是逐漸接近的。
問:爲什麼本地女性不願意找外地男性結婚?
齊薇薇:這裏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人們都傾向找經濟條件更好的人做自己的另一半。對珠三角這裏的女性來說,這個地方就是周邊最富庶的,她爲什麼要嫁到別的地方?
與男性相反,當地的女性在婚姻市場中處於劣勢。大量外地女性與本地女性共同爭奪男性資源,性別比倒掛,女性資源遠多於男性,有許多競爭失敗的未婚女性青年。
問:既然是婚姻高地,爲什麼反而會導致離婚率增高?
齊薇薇:我們訪問了村幹部、村民小組長,還有婚姻登記處、婚姻危機幹預的工作人員,發現離婚通常由女性提出,許多都是年輕夫妻,30歲左右,認識時間不長,閃婚閃離。在這個地區,男性的離婚成本是很低的。
他們不愁找不到對象,如果離婚了,可以立刻轉身,找個更年輕漂亮的。我們在近十年的數據中也發現,當地再婚人數同樣不斷上漲。男性在婚姻市場中的絕對優勢,使他們再婚變得更容易。
中西部農村常見的光棍問題,在這裏並沒有出現,即使那些家庭條件差、身體有殘缺的男性,也能順利結婚,儘管他們很難找到本地女性,但可以找外地女性解決婚姻問題。我在村裏遇到一個69歲的老段,他自己有房產,子女也都成家了,愛人生病去世後,不久就有人給他介紹對象,他很快就與一位30多歲的外地女孩再婚了。
問:這樣看來,無論外地女性還是當地女性,在這裏的婚姻市場都處於劣勢?她們爲什麼還會主動提離婚?
齊薇薇:農村地區女性提離婚,多數情況下是一種博弈的手段。她想通過“鬧離婚”來改變自己在家庭當中的地位,博弈不動,只能順從,如果她又不願意順從,纔會真的選擇離婚。
一個80後男性,雖然家庭條件一般,經濟沒老段那麼富裕,而且他前兩次婚姻都是因爲性格不合,離了。他還是很快找到了第三任妻子,女方是外地人,比他小9歲,還是頭婚,在村裏做社工的過程中認識了他。兩人結婚沒多久,妻子覺得他不怎麼做家務,再次提出離婚。婚姻幹預中心的工作人員進行了調解,但他並不打算改變自己,也不怕再次離婚,於是第三任妻子也離開了他。

問:這跟中西部地區還是挺不一樣的。
齊薇薇:對。中西部的農村女性是沒得選,農村有許多光棍,但是都不富裕。不過,隨着那邊性別比例越來越懸殊,結婚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在我的老家湖北孝昌,村裏的離婚率近幾年同樣翻倍地增長,我看到民政相關數據,發現離婚率上升的同時,結婚率在直線下降。
婚姻裏兩人的權力地位也反轉了。我在之前的調研中發現,中西部地區的男性很怕老婆跑了。他們提到,“花幾十萬討一個老婆,對方不高興,拍屁股走了,彩禮全損失了,再結婚變得更加困難。”當幾十萬彩禮的經濟權握在女性手裏,她們可以用“鬧離婚”來博弈,實現家庭當中的主導地位。我們見過一些“小鎮貴婦”,在家裏不參與任何勞動,對孩子不管不顧,說一不二,又要求男性給她提供很好的生活。
而在珠三角這裏,女性沒辦法用提離婚的方式進行博弈。這裏沒有彩禮,女多男少的情況下,男性離婚成本低,再婚成本也低,女性想改變家庭當中的權力結構,變得非常困難。即使她想搏一搏,但是男的根本不怕離婚,博弈不動,她也不願意順從這種權力結構的話,就直接離了。
宗族秩序下的博弈
問:由於外來女性增加,婚配邏輯接近城市,這跟珠三角農村原本維繫婚姻的方式產生怎樣的矛盾?
齊薇薇:珠三角的村莊經濟很發達,人卻很傳統。我們去調研的地方,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宗祠,家族之間也有很強的聯繫網絡。這裏村集體的經濟實力支撐他們舉辦大量集體活動,它強化了村莊的共同體意識。當地幾乎每個月都有傳統的集體活動,祭祀、迎神,賽龍舟就是其中最隆重的一項。
宗族性較強導致村民的大家庭與家庭責任觀念比較重。我們看到了不少大家庭制度的遺留,例如在多個子女結婚之後,家庭內部還沒有進行財產上的分割。有一位男性村民,結婚了11年,他弟弟也已結婚6年,妹妹結婚7年,但是這個家仍然沒有分。小家庭之間已經獨立,但是共同財產和房屋都沒有明確的劃分。兄弟結婚之後多年仍然與父母同居,這種現象在S村不是少數。
一個外地女性嫁入本地,除了與新三代直系家庭的磨合外,最爲重要的是要適應家族內部女性的圈子,特別是適應婆婆的圈子。外地女性在適應本地家族活動中是非常被動的,語言作爲第一道生活的關卡,往往就可能會將外地媳婦排斥在家族活動之外。
問:所以這種適應成本的增加,是導致外地女性提出離婚的主要原因?
齊薇薇:其實她們與本地女性不同,反而不一定會因此提出離婚。有些外地女性遇到老公出軌,男方提出離婚,女方是不願意離的。她從外地嫁過來,戶口也遷過來了,離了婚之後,不知道戶口該怎麼辦。因爲她也不想真的把戶口遷回去,兩個人最初在一起的時候,女方的父母通常是反對的,她不知道離婚後怎麼去面對自己的家人。
但外地女性的流入既增加了本地女性需要面對的婚配壓力,又讓本地男性擁有更多婚配選擇,降低了男性離婚的成本。
問:相比之下,本地女性是什麼情況?
齊薇薇:她們最多的兩個離婚原因,分別是家庭瑣事和婆媳矛盾。訪談中我遇到一對本地夫妻,結婚剛半年,還沒有小孩,兩人都跟男方父母住在一起。婆婆非常強勢,家裏什麼都由她管,但妻子也有自己的主見,婆媳之間經常產生矛盾。丈夫護着自己的媽媽,站在媽媽的立場,說妻子的不是,有時還要求妻子跟媽媽認錯,最終導致妻子提出離婚。
還有一對認識兩個月後就閃婚的本地夫妻,婚後同樣跟男方父母住在一起。小孩出生1個月左右的時候,婆媳開始鬧矛盾。有一次孩子生病得了肺炎,妻子想帶孩子看西醫,但婆婆認爲中醫更好,兩人就發生爭吵。丈夫站在婆婆那一邊,逼得妻子也只好妥協。後來,妻子想帶孩子回孃家住,繼續養病,婆婆又不放心,不肯讓她把孩子帶回去,她只好一個人回孃家,憋了一肚子火,不願意再回夫家了,想讓丈夫來道歉。結果她在孃家住了三個月,丈夫都沒有來接她回家,就堅決提了離婚。
問:這是她們無法博弈之後的結果?
齊薇薇:當地的宗族祠堂、祭祀活動是以男性爲主導的,股東和股民代表以及核心的村莊幹部也基本以男性爲主導。在諸如賽龍舟這樣的社會生活領域裏,雖然開始有少部分女性參與龍舟賽事,但是社會生活領域裏的規則建立在性別分工秩序之上,仍然是男性主導。
當地男性與社會集體活動的互動非常頻繁,因爲參與村莊公共活動最多、付出最多的人,會得到村裏最高的評價,也最有面子。在珠三角地區,人們的宗族觀念很強,面子不像華北地區通過私人之間的互動形成,而是個體與集體互動才能得來的東西。
但以女性爲主體的活動領域基本都是家庭活動,在這樣的一個生活秩序下,女性通常只有在大家庭裏,成爲“婆婆”的角色,纔會真正獲得話語權。

問:面對依然有較大影響力的宗族文化和宗族結構,這幾年本地女性發生了什麼變化,讓她們得以選擇離婚?
齊薇薇:現在,當地的年輕人基本都是經濟獨立的,夫妻雙方都有自己的工作,而非一方是家庭主婦。但是結婚後,他們仍然按傳統方式,即便不跟男方父母住在一起,也經常會在一起喫飯。家裏只有一個兒子的話,兒子一定會跟父母住一起,有兄弟的情況下,父母會選擇其中一個兒子一起住,一般是小兒子。房子沒那麼多的話,父母也很樂意跟兩個兒子同居。
在同一個屋檐下,婆婆依然要求兒媳聽話。下班後回到家,丈夫什麼都不用幹,妻子不僅要承擔家務活,還要照顧丈夫和小孩。但這些女孩不僅經濟獨立,同樣也有很多是獨生子女,受過中等或高等教育,希望跟丈夫保持平等的關係,而不是自己一個人承擔家庭的付出。
家庭的“去公共性”
問:經濟獨立,是當地婚姻關係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嗎?
齊薇薇:像村裏的70後或60後,他們的婚姻關係非常穩固,因爲他們是當地創業的一輩,很多人做傢俱產業,年輕時生活很艱苦,結婚後既要承擔父母的養老,又要養育子女,所有事情都是夫妻相互協作才能完成的。他們的經濟收入也都集中用於實現家庭的共同目標。女方嫁到男方家裏,也會努力融入大家族,因爲家族和村莊會規範約束夫妻雙方的行爲,否則他們都會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
但80後、90後一輩的年輕夫妻,在經濟富裕的環境中長大,大部分是獨生子女,一邊享受父輩創造的經濟條件,一邊又在結婚後繼續與父母生活在一起,依靠父母的支持,這樣他們的婚姻也不存在共同的家庭目標,公共性也逐漸消失了。
問:當地的經濟發達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齊薇薇:在80後90後的成長過程中,這裏一直保持着地租經濟的發展模式,跟江浙的經濟發展還不太一樣。
我在S村調研時,農戶會告訴我他每年有多少土地租金收入,後來也去他們當地的股份合作社問過股份分紅的情況——這裏每年集體收入高達上千萬,股份分紅到每家每戶有幾萬塊錢,這還算比較少的,多的話一年一家能分得十幾萬。
他們有自己的宅基地,自己建別墅,能容納下幾代人。地租經濟就夠他們生活了,人們可以在本地找一個差不多的就業崗位,不需要跟外地的人去競爭。當地人是低度參與勞動力市場的,一旦不用拼命適應現代社會,也就有更多機會保留傳統習俗。
問:除了地租經濟的發展加固傳統習俗外,華南宗族文化還受到哪些影響,得以穩定延續?這跟其他地區有什麼不同?
齊薇薇:我們調研中發現,中西部農村文化瓦解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人口外流,當村民們沒有集體活動,也沒有任何交集,文化就很難延續下來。那邊的老人在家庭中的話語權越來越微弱,基本上是年輕人在主導家庭關係。
但是在宗族觀念很強的珠三角地區的農村,它從70年代就開始發展經濟,整個文化又是延續性的,老人掌握着各種資源,也掌握了家庭的主導權力。
問: 經濟獨立的年輕人跟這些保留下來的傳統,如何爆發矛盾?是這種矛盾導致你所說的,現代性對當地個體、家庭和村莊的塑造比中西部農村更深、更快?
齊薇薇:儘管現在內部小家庭已經形成獨立的財產單位,但是小家庭又共同嵌套於大家庭之中,按傳統家庭秩序,股份社分紅收入仍然由父母掌握,子女還會上交給父母一些伙食費。
有一個80後本地男性,跟外地女性結婚,他自己掙的錢還是交給父親。到了老婆生完孩子後,女方在家帶孩子、沒有工作,手裏也沒錢了,每次花錢都得向公公要,跟老一輩人常拌嘴。最後,女方無法忍受這種家庭關係,提了離婚。
我記得一位30多歲的本地男性,在村委會工作,工資一個月將近1萬塊錢,妻子在一傢俬人公司做會計,一個月收入多少錢他不清楚。他掙的錢一部分自己花,一部分上交給父母,妻子掙的錢也是妻子自己花。他們雙方互相不知道銀行卡密碼,也不知道彼此有多少存款。其實,他作爲哥哥,已經分家出去住,只是平時喫飯還會常回大家庭一起。婆媳矛盾偶爾爆發,女方還是提出離婚——她在經濟上是獨立的,不需要依附於丈夫。

問:你在研究中提到,夫妻關係必須在情感和公共性的共同作用下,才能保持相對的穩定,而這裏的婚姻結構是“去公共性”的,所以更容易離婚,這具體是怎麼發生的?
齊薇薇: 在過去的農村家庭裏,生育是夫妻的共同目標,兩人爲了孩子,進行一種家庭再生產。但現在的家庭結構倒過來了,夫妻是基於感情、愛情進行的結合,孩子並不構成我維繫婚姻的必要條件,費孝通提到的夫妻、孩子這種基本三角結構消失,穩定性也沒了。
家庭作爲一個社會組織,是需要共同目標的,在S村,夫妻雙方的經濟實力都足夠他們過上很好的物質生活。以前農村人會希望孩子到城裏上學唸書、讀大學,希望孩子有一個好的未來,甚至實現階層躍升。而本地的勞動力市場更青睞於招收本地人,當地父母也更希望把子女留在身邊工作,不喜歡他們到外地去,所以孩子已經不再構成家庭的共同目標。僅靠人的情感,又是不確定的。
早年的農村女性是出於物質原因,沒有自己的收入,導致她沒有辦法離婚,還有的人是願意爲了子女不離,家庭的共同目標超越了她的個體價值。我在S村看到,這樣的結構已經解體了,現在沒有超越個體感受的價值體系來讓人維繫婚姻了。鎮上婦聯的工作人員發現,過完年,因爲丈夫出軌前來諮詢離婚的本地女性非常多,許多是很年輕的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