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種下不久的綠天鵝絨海芋夭折了,我和男友開始排查令它過早枯萎的罪魁禍首是誰。最後,男友在購物軟件檢索出一款營養土,他意有所指地展示出商品詳情頁面的對比圖,“你看右側這個作爲反面案例的土,是不是有點像我們家的呀?”
被商家用來襯託自家產品的反例土顏色黢黑、透氣性差且容易塌陷,和我圖便宜買的土一模一樣。這不是我第一次在購物這件事上撿芝麻丟西瓜了,自從七月開啓同居生活以來,我誤把硅膠質地的冰塊模具買成塑料的,保鮮膜買成保險罩,牙膏買成迷你版試用裝……原因無他,唯摳門爾。每次臨下單之時,我都會鬼使神差地購買備選項中價格最低的那一個,頻頻出錯也不足以使我回頭,我始終秉持着“這次發揮不好,下次我還這樣”的喫虧心得,在小家中爲非作歹。

男友有些不解,爲什麼買對商品這麼簡單的事情,我卻可以一再搞砸。如果是出於想省錢的心理,可是後來又總是因此損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那爲什麼不改改呢?“很難改,這是歷史遺留問題。”回答他時,我正低着頭專注地給購物軟件上的虛擬農場澆水,目標是在幾個月後領到一小箱我並不愛喫的水果。
要是媽媽在身邊就好了,我想,媽媽一定會懂得。
我謹慎行使家中“財政大權”,卻在要緊關頭掉鏈子的樣子,和我媽如出一轍。小時候家裏經濟條件不好,四口之家中只有爸爸這一個勞動力,但沒有工作的媽媽並沒有停止工作,她負責打點家中的所有事,包括把完全不夠日常開銷的錢掰成許多瓣兒,直到勉強夠用爲止。至今我們仍會拿她十幾年前買的劣質DVD機來打趣,“最近我不太行,像DVD機”,它在買來幾天以後就光榮退役。
媽媽的“摳門”事蹟不勝枚舉。比如,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家就沒怎麼用過洗潔精。媽媽會去超市或雜貨店拿一些過期的牙膏,這是她心中最好的清潔劑,能有效清理污漬,最重要的是,它是免費的。我房間裏的許多陳設都是媽媽在外“薅”來的:附近保險公司棄置了的玻璃櫃、複寫紙,爸爸工作的廠裏多餘的桌椅,小姑父賣掉房子後無處安置的沙發……別人丟掉的垃圾,來到我們家就搖身一變成了寶貝。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的歲月裏,媽媽的“摳”爲我們的小家添磚加瓦,功不可沒。

後來家中的狀況逐漸轉暖,我偶爾能有出門旅行的機會,家裏也重新裝修了一回。我期待看到新家的改變,然而暑假回家時,我滿心歡喜地推開房門,隨後就崩潰大哭——牀是堂姐家淘汰了不要的,書桌是用舊門的木材改裝的,衣櫃和新房最不搭調,還是千禧年間的城鄉結合風格。大張旗鼓的裝修不過是新瓶裝舊酒,其實什麼也沒改變。
衛生間洗手檯上的櫃子,我一碰,櫃門就散架了。搖搖欲墜的櫃門壓垮了我最後的心理防線,這使我和媽媽大吵一架。我不明白,脫貧好些年了,劣質DVD機的陰影怎麼還是揮散不去呢?爲什麼我們節衣縮食了這麼久,好不容易擁有了翻新舊生活的能力和資本,媽媽還是要固執地留在過去,用現下流行的話來說就是“沒苦硬喫”呢?
美國作家約瑟·比林斯說:“有幾種節儉是不合算的,比如,忍着痛苦求節儉就是一個例子。”所謂的“不合算的節儉”,是我們家代代相傳、奉若圭臬的行動準則。小時候我和媽媽一起讀書,看到一則小小說,故事大概是有個人去喫自助餐,爲了喫回本兒而胡喫海喝,最後犯胃病進了醫院,反倒花掉比一頓自助餐更多的錢。我在心裏偷偷嘀咕:媽媽就是這樣的人,笨笨的。
更費解的是,人居然可以在完全不理解一個人的情況下,最終潛移默化爲這個人的分身。
我在圍繞着媽媽的過度節儉行爲而產生的笑聲中,出乎意料地成爲媽媽的翻版。上大學以後,雖然家境算不上富裕,但父母在生活費上從未苛待過我。對,我們一家人的摳門僅針對自己,從不針對別人,甚至對除自己以外的人會尤爲大方。所以,父母的限定性慷慨使我理所當然地成了同學中的小富翁,只不過有些跑偏——我成了吝嗇鬼葛朗臺那種類型的富翁。

通常來說,我一頓飯的花費不會超過5元錢,不喫水果,不化妝,不怎麼出門。難得去其他城市看個演出,明明盤纏足夠,還是選擇坐二十小時的綠皮火車硬座,睡在通宵經營的麥當勞,用一身的痠痛贖回幾百的車旅費。別人問起,我的藉口通常是坐火車更加傳奇和浪漫,也很符合搖滾青年對於“在路上”的某種想象。但實際上,我僅僅是捨不得。我的腦內永遠懸掛着一個計價器,它每時每刻都亮着紅燈,提醒我能不花則不花,畢竟生命寶貴不可浪擲,金錢更是。
其實,作爲靠父母接濟的大學生,我省下的那仨瓜倆棗根本無足輕重,我心裏明白,卻停不下來。這種明明意識到自己在做無用功,卻還是難以擺脫的慣性,讓我有些明白了媽媽的心態:也許對我們來說,“我很節儉”的感受要比實際能省下的錢更重要。我們不允許自己是個不節儉的人,我們不能有不節儉的行爲。
忍着淡淡的餿味喫下隔夜的麪包以後,我坐在工位上邊捂着隱隱作痛的腹部邊想,也沒窮到沒飯喫的地步,我究竟何以至此?得出的結論是: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積穀防饑”的行爲習慣、未雨綢繆的遠見……除了它們,我還在媽媽身上“遺傳”到一種匱乏。
《情緒詞典》一書中指出,如果一個人在童年時長期生活在物質貧乏的環境之中,就會經常體會到一種匱乏,而這種匱乏的感受會深深地影響到這個人日後的行爲模式。哪怕這個人後來的生活不再貧乏,但內心的匱乏感也難以被消退。一般而言,有些經歷過匱乏的人反而會產生不理智的消費衝動,通過“暴發戶式”的消費,來彌補內心的空洞。而另一部分人,則是走向另一個保持匱乏狀態的極端,客觀條件得到了提升,心理狀況持續着匱乏。這種匱乏的感受在心理學中的術語是“稀缺心態”(scarcity mindset),指的是一種認爲自己所“擁有”的少於“需要”的感覺,它使人聚焦於當下的稀缺,忽視未來所需要償還的代價。

顯然,媽媽和我都是後者。《財富自由》中表明,過度節儉會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當節儉導致一種被剝奪的感受時。這種感受使我發自內心地相信,我應當過一種艱苦的生活,輕鬆、愉悅和享受,是與我無關的奢侈品。所以,我十多年沒踏進理髮店,所有髮型都是自己操刀完成的;我總是購買臨期打折的食品,以至於再也不願購買正價的新鮮食物。許多個盛夏的午後,我在外玩得又渴又累,整個人幾近脫水狀態,仍然捨不得買一瓶礦泉水,因爲景區自助機裏的水要比正常價格貴一倍。忍一忍,我對自己說,不能花冤枉錢。
無盡忍耐的結果是,我錢沒省下多少,人卻憔悴了許多。過度節儉成了我性格中的一部分,當面對一件事時,我會更傾向於採用自己熟悉的、能感覺到安全的經驗去應對,即便它並不那麼正確。我和金錢的關係,影射了我和自己、我和媽媽、還有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我對自己十分苛刻,正如媽媽對自身的苛刻,我無法輕盈地參與到這個世界的精彩之中,因爲我看不見“勤儉節約”和“過度節儉”之間的分界線。
我一度節儉到“走火入魔”的境地,把任何一種我認爲不合理的購物都歸結爲消費主義的陷阱。我在南方讀的大學,冬天沒有暖氣,我又捨不得買厚的被子,只能在空調被上疊蓋各種衣物,晚上睡覺一翻身便會抖落,於是我灰溜溜地拾起它們,重複一件疊加一件的動作。當時的室友實在看不下去了,她問我“你至於嗎?”,許多次,我也這麼問自己,在乾渴到喉嚨疼痛也不願買水的時候,在一再買錯物品的時候,在逞能喫下所有食物,然後腹痛到崩潰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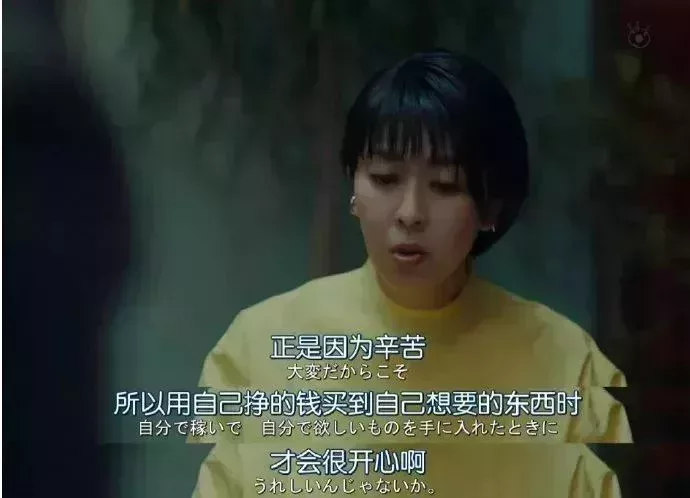
不至於,這真的不至於。我需要直面自己的匱乏與不安,如若不然,只會滋生出更深的缺失。頭髮又長過肩了,這一次,我就去店裏剪個新發型吧,改變從頭開始。
我知道,也下定決心,要樹立新的消費觀念。生活不能被簡化爲生存,飲食也不能退化爲維持生命體徵的一種行動。適度的“摳門”當然沒什麼不對,要開源,也要節流,畢竟連“股神”巴菲特都厲行着勤儉之道,認爲善用摳門的方法或是抵禦通脹風險的法門。但是,凡事皆有度,過度的節儉只會造成得不償失的後果,而這後果的滋味,我已經嚐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