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因爲有過多次在影院中途退場的慘痛觀影經驗,如今的我在看電影前,始終還是需要某瓣評分的信心支撐。不看不知道,徐崢導演的影片《逆行人生》,在沒有正式公映前,便遭遇了許多指摘:“一幫窮人花錢,看富人演自己”,不過,這反而激起我看這部影片的衝動:一個45歲的中年白領,如何在大廠裁員之後開始送外賣?拋開喧囂的評論,迴歸常識與常情——這樣一個故事,還能打動我嗎?故事之外,它還能告訴一些別的東西嗎?

影片開頭,是導演精心設置的一幅中產生活圖景:乾淨整潔的大房間裏,全職在家的媽媽和奶奶做好早餐,爺爺晨練回來,睡眼惺忪的女兒醒來,叫醒晚上加班回來睡在沙發上的爸爸,即將上國際學校的她,在餐桌上用英語和爸爸開着玩笑。然而,你能看到這幅場景是緊繃而脆弱的,鬧鐘至少響了三次,所謂中產,不過像一根緊繃的發條。發條很快崩掉了——作爲公司一個開發小組的負責人,高志壘突然被“優化”了。

如果說,整部電影中,高志壘的中產失業,是一個吻合於經濟下行、大廠裁員背景的現實設定,那麼,緊接着的老父親腦卒中住院,之前家庭投資的P2P暴雷,則顯然是把發生在很多人身上的案例集中呈現在了主人公身上,這種戲劇化的設定,難免會讓人感覺有一種“無巧不成書”的失真之感。
看到這裏,我忽然湧起一種奇怪的念頭,如果說在十多年前,我們在賈樟柯的《天註定》中還能看到那一個個由真實新聞事件連綴起來的普通百姓的絕望抗爭和背後的社會思考,那麼在當下的熒幕中,我們只能看到一個個脆弱無力的個體與羣體,所謂思考,則更多內傾於主人公自身——你的心態夠不夠好,你夠不夠努力?《逆行人生》無疑就是這樣的作品。在現實主義的大旗下,對身邊普通人的命運呈現也僅止步於此,一時不知道該苛責誰。
不過同樣作爲中年人,高志壘的逆行人生,那種東方式的情感表達確實打動了我——一遇到困難,家庭中的男人只能獨自扛下所有——失業兩個月後,經歷重新求職中的年齡歧視,黑中介騙錢,房貸斷供後,辛芷蕾扮演的妻子肖妮最後知道這一消息,流着淚說:“這個家不是你一個人的。”

不管怎樣,高志壘終於決定送外賣了。據統計,截至2024年,中國外賣行業從業人員數量已超過1300萬,網約車從業人員數量也超過600萬,毫無誇張地說,這兩大增量龐大的行業,已成爲不少失業人羣爲數不多的次優選擇。
逆行而下的人生,最難完成的轉變是心態,對於一箇中年來說,這種打碎重建的過程尤爲艱難。讓徐崢這樣自帶喜劇色彩的演員,演出一個外賣員的信賴感,並不容易。

當高志壘剛到外賣工作站時,站長看到他一幅都市白領的穿着,就直言他幹不了,直到他囁喏地說:“我找不到工作了,我需要錢”時,才被勉強接納。當他真正進入這個行業,才發現送外賣並不簡單,在這個被算法統御的系統裏,同樣存在着從青銅到鑽石的騎手等級和行業內卷。
超時,差評,還有面對昔日同事時的尷尬,高志壘初入外賣行業的悲催,最終以一個極富象徵意味的鏡頭達到高潮。低血糖還有內心的憤懣,讓他從摩托車上重重摔倒在地,幫客戶代買的魚從袋子中蹦出來,躍入蘇州河中,傷痕累累的他,對着手機努力自拍一張笑臉的照片,卻始終無法完成系統“微笑計劃”的服務要求,被迫停業三天。這段時間裏,同樣難以接受的是他剛剛出院的父親,他難以接受自己辛苦培養出的同濟大學的畢業生,最終要去幹苦力。這也是對於很多中年人來說,難以真正脫下長衫的原因。

影片中,主人公心態轉變的關鍵事件,是在激烈爭吵過後,父親在70歲生日來臨之際偷偷寫下的一封遺書,看到兒子生活得如此艱難,老人不願再爲他們增加負擔,準備選擇偷偷離開這個世界。從編劇角度而言,這一情節多少有些突兀甚至誇飾。飽經認世閱歷的老父親,僅僅因爲已躋身社會精英的兒子突然失業跑去送外賣,自己生病之後行動不便,便採取如此激烈的方式,顯然不合常理。但那種情緒本身,我確實理解到了,即在脆弱的中年人背後,還有一個更爲脆弱的老年人。

電影隨後討巧地用了一個場景完成了轉折。兒子一邊爲行動不便的父親洗澡,一邊流着淚說:“再苦也沒有你們那會苦,我們至少還有紅燒肉喫。”這一事件成爲全家人無論是心態還是行動上變化的轉折點:父親雖然不去醫院做理療,堅持靠自己鍛鍊重新站了起來;母親重新操持起小區的小賣部;高志壘則重新調整心態,虛心向其他騎手請教,主動幫客戶倒垃圾、幹雜活;妻子則在家教小孩子打架子鼓,還成爲一名主播;女兒雖然沒去國際學校,卻變得更加用功懂事。
也是在這之後,電影裏的高志壘纔看到了同樣有血有肉、一個個鮮活而努力的外賣員羣像:“追愛騎士”楊大山努力跑單,爲了迎娶自己心愛的女子;“單王”大黑,拼命的背後是要替因爲自己轉單而遭遇車禍失去一條腿的年輕人;“老摳”拖着受傷的腿跑出醫院不願花錢,因爲家裏還有一個等待白血病手術的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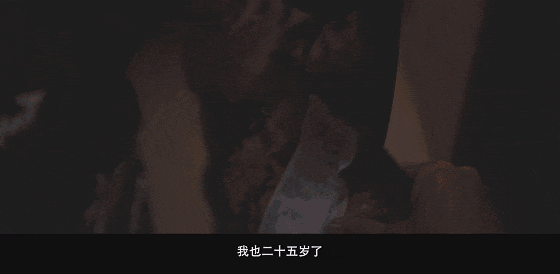
傍晚時分,坐在“老摳”位於一片垃圾場的房子外面,兩個男人五味雜陳的調侃,還有黑暗中摩托車上迎風飄揚的“老摳”送給高志壘的一朵小黃花,讓人動容,即使是再破敗的垃圾場也能開出花朵,再卑賤的底層依然蘊藏着人性的美好與偉大。這一瞬間,很自然讓人想到《送你一朵小紅花》的電影與同名歌曲,一個同樣走出內心困境,重新與家人朋友建立了深厚情感聯繫的故事。
當然,很多觀衆對這部片子的批評,正是來自這種特殊羣像集體出場,又一起完成了“正能量”的強價值觀敘事,但當高志壘終於成爲“單王”,在領獎臺上說出,“我們大家都是很努力的。我們都足夠努力了,所以我們值得被尊重,我們也值得更好的生活”時,我明顯聽到旁邊座位上一個中年人幾乎難以抑制的抽泣聲。

平心而論,這部影片也打動了同樣身爲中年人的我。走出影院,我忍不住回想,這樣一部在許多細節上其實難以經得起仔細推敲的電影,爲何會打動不少如我一樣的中年人?爲了合理化主人公送外賣的選擇,導演將諸多社會問題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有的評論者甚至直接點出:“一月一萬多的月供,用借唄或者微粒貸就能搞定,何至於要在斷供兩月的壓力下跑去送外賣?”
是啊,這已不是一個“一分錢難倒英雄漢”的秦瓊賣馬的時代,爲何一定要送外賣?情節方面,這部電影另外讓人詬病的地方在於,外賣固然是危險性較高的行業,可導演爲了情節的推進,竟在其中安排了三場並不相同的車禍,多少顯得技窮。但是,爲什麼它依然打動了我?

回答這個問題前,我想起了另外一部動畫電影《長安三萬裏》,據說,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中年人,在看完這部電影后紛紛落淚。爲何又是中年人?就我自己來說,那是幾個人和一個充滿少年氣息時代的凋零史,滿屏的詩歌不過成爲它們的註腳。中年人,在最需要摒棄感性的時候,只能在動畫片裏想象性地告別青春與詩歌。
回到這部影片,我想說的是,它可以在現實中與我共情。那種中年老男人面臨職業變故時,在家庭位置中的進退失據,無法訴說;那種痛苦地打碎自己重建尊嚴的艱難過程,同樣讓人唏噓不已,感慨萬千。
影片中那些看似雞血的臺詞:“把掌聲獻給每一個努力的自己”,其實只有當你真正褪下孔乙己的長衫,成爲一個普普通通的勞動者的時候,才能感受得到。就像賈冰飾演的站長說的:“幹外賣最重要的是心態。你總以爲你已經脫掉了孔乙己的長衫,但你還沒成爲駱駝祥子。你總以爲你是坐車的, 但你其實是個拉車的。”

這句人間清醒的點題之詞,看起來是撫平和掩蓋經濟下行、階層滑落過程中種種的社會體制問題與矛盾,卻未嘗沒有現實意味——當苦難來臨,你還能做什麼,牢騷滿腹,進退失據,還是放下身段,建設自我?
然而,成爲駱駝祥子以後呢?祥子單純的理想不過是擁有一輛真正屬於自己的車子,靠自己的勞動換取更好的生活,他又得到了什麼?時代已然不同,被拋灑出去的個人,似乎只能回到自身,回到一個樸素的真理:活下去,像個人一樣活下去。熟悉吧,幾十年過去了,從《芙蓉鎮》到《逆行人生》,我們得到的教益,不過是從“像牲口一樣活下去”到“像人一樣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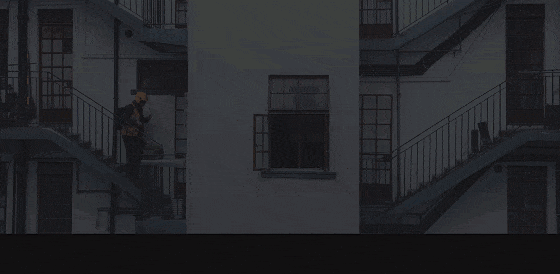
作家梁曉聲在散文集《人活着》裏面,曾談到在國外遇到做清潔衛生的普通人,還有受過高等教育開飯館的普通人,同樣受到尊重而內心平和。這份平和,既來自一份有保障的收入,也來自個人尊嚴的不容侵犯。接受採訪時,他談到:“當外部不利環境向你撲面而來,整個時代都淪陷於物質崇拜的時候,你不能處在這個鄙視鏈的上端,靠什麼維持自己的自尊?我認爲除了文化和人格,沒有別的。”
只是,在我們的時代,談物質崇拜,已多少顯得言不及義。對於一箇中年人來說,如何維持自尊地活着,或許真的需要加上一份心態,一份由“卑以自牧”切換爲“卑以自存”的心態。年前,我的一位作家朋友,開始在孔網賣舊書。他告訴我,當自己翻看着一本本殘留着青春回憶的書時,突然一個人在房間哭得難以自制。我不知道,他哭過之後,是不是真正脫下了長衫,我只知道我們已很少談論家國,杯子碰在一起的時候,並沒有夢想破碎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