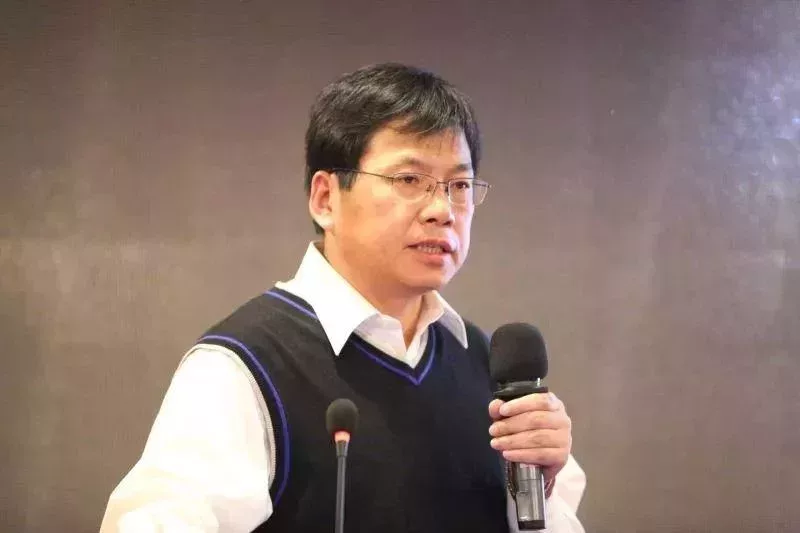
經濟自由——自由之母,憲政之路
作者:劉軍寧(著名政治學家)
在我國,個人的自由一直是一個重大的問題。而經濟自由尤其如此,先是受到錯誤對待,完全誤解,直至現在又幾乎被徹底遺忘。在市場化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我們絕對有必要重新認識經濟自由。本世紀傑出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兩本鉅著最近在中國的出版無疑爲我們認識經濟自由提供了寶貴的鑰匙。
人們對經濟自由的輕視,或者說蔑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經濟自由被當成一種與庸俗的商業活動聯繫在一起的、低級的、可有可無的自由。所以一些有崇高理想的人常常傾向於把牟利的勾當交給“平庸”的商賈或政府去擔當,以確保自己可以全力以赴、信心百倍地拋開經濟自由去孤立追求政治上的自由和“解放”。然而,誠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指出的:“不幸的是,人們從這樣一種信念中所得到的保證是完全不可靠的”(第88頁),“離開了經濟事務中的自由,就絕不會存在…那種個人的和政治的自由”,(第20頁)“沒有經濟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沒有意義的”(第98頁),因爲這樣的自由只能是少數統治者的自由。
經濟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礎
在所有的自由中,經濟自由最爲根本,也最爲珍貴,因爲通過經濟自由的運用,人們可以獲得運用其它自由所必需的物質基礎,基於自願交換的經濟自由由於有極大的互惠性,通常不會對他人造成傷害。在自由市場經濟中,經濟自由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個人可以進行自由的交換,自由地獲得、佔有、使用和處置自己的財產;二是基於資源交換的經濟自由意味着這些活動不受政府的幹預。經濟自由通過限制國家權力的數量和作用範圍,從而鞏固了自身。經濟自由結束了“只有通過政府才能致富”這個自由主義者和自由人的夢魘。而“通過政府致富”可是說是“魚肉百姓”的同義語。
經濟自由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得最爲廣泛的自由,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的關係最爲密切。掙錢與花錢可以說是經濟自由的最活生生的體現。貨幣與權力的對抗即是經濟自由與政治權力的對抗。貨幣的發言權越大,權力的發言權就越小。只有希特勒這樣的“私天下”者纔不在乎他自己掙多少錢,這類人要的是天下。當帝王與草民在金錢面前完全平等時,自由就存在了。所以,哈耶克認爲,“錢是人們所發明的最偉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現代社會中,只有錢才向窮人開放出一個驚人的選擇範圍,這個範圍比在以前向富人開放的範圍還要大”。(《通往奴役之路》,第88頁)剝奪了錢的作用,即是剝奪了窮人的自由。以前,有錢也買不到軟臥票,就是一個註腳。一個買不到軟臥票的人會享受到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嗎?所以,這裏是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雙重失落。
再以外匯管制爲例,表面上,實行外匯管制禁止的只是炒作等投機行爲,波及到極少數以貨幣交易爲職業的人的經濟自由。然而,哈耶克卻看到了另一面。他認爲,外匯管制,“是對個人自由的壓制,使個人完全屈從於國家的專制之下,是把一切後路都斷絕掉的殺手──不只是對富人,而是對每一個人。一個人不再能進行自由旅行,不再能訂閱外國書報雜誌,一旦一切對外聯繫的工具僅限於那些爲官方意見所認可的人,或者官方認爲必要的人,則它對輿論的有效控制,將遠遠超過十七和十八世紀任何專制主義政府所曾經施行過的控制的程度。(《通往奴役之路》,第91頁)
可以說,經濟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沒有經濟自由,政治自由和其它自由就很容易從人們身邊被奪走。換句話說,其它自由的有效運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人們獲得、佔有和使用財產的自由。比如說,沒有辦報的經濟自由能享受到充分的言論自由嗎?對經濟自由和財產權利的伸張也意味着必然要求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一個權力太大的政府肯定要以犧牲個人的各方面自由爲代價,一個腐敗得不到有效制止的社會必然對人們的經濟自由和財產權構成重大的威脅。
作爲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當代傳人,哈耶克認爲建立在經濟自由和財產權基礎上的社會不僅是最有效率、最爲繁榮的社會,而且在道德上也優越於其它社會。因爲這種社會是最自由的社會,自由是一切價值中最重要的價值。自由市場是進步與文明的引擎。市場中的自由(經濟自由)是一切其它自由的保障,併爲其它自由的擴展提供了最有效、最可靠的途徑。另一位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弗裏德曼發現,一個自由競爭的繁榮的市場經濟,在社會中造就了無數個由小到大的、以小爲主的經濟權力中心,從而阻止了政治權力向中央的集中。
人的有限理性及其自由選擇
自由市場經濟之所以成爲當今最普遍的、唯一可行的經濟形式,是因爲它是人們經過漫長的探索和積累所得到的最契合人之本性的經濟體制,市場經濟超越國境的可行性也恰恰證明瞭普遍的和不變的人性。自由市場經濟也最契合人的有限理性,因爲它可以自發地運轉、自動地配置、自動地調節,而不需要人的全知、全能。計劃經濟是建立在計劃者的全知全能的假定之上,由於這樣的人不存在,無限的理性不存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就註定要破產。沒有人能夠駕馭如此複雜的市場經濟,所以任何駕馭這一經濟的努力,尤其是防止以駕馭市場、克服無政府狀態的名義來把經濟送入“鳥籠”之中的企圖都是對自由的葬送。
取消市場,取消作爲自願交換的經濟自由,即是取消了一切的自由,打開了通向奴役之路。經濟自由和一切自由都依賴於市場,產生於市場。一個社會中,市場的空間越大,政治權力強製作用的空間就越小,自由的空間就越大;市場的空間越小,政治權力強製作用的空間就越大,自由的空間就越小。市場消失了,包括經濟自由在內的一切自由也就都窒息了。所以,“我們不能無限地擴大公共行動領域而仍讓個人在自己的領域中自由自在”。(《通往奴役之路》,第63頁)
以哈耶克爲代表的當代自由主義者要捍衛市場經濟,是因爲市場經濟是通向正義與自由社會的手段,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有權支配屬於他的東西,支配他從他先輩那裏合法繼承的東西,支配對他的能力、勤勞和運氣的獎賞。這樣一個充滿個性與多樣性的社會必然優越於每個人不過是棋子的棋盤社會。
任何自由都是選擇的自由,自由本身不能與特定的結果相聯繫,否則就排斥了選擇。自由的精髓正是允許人們進行選擇,並承擔相應選擇的後果。經濟自由也是如此,它意味着人們可以在不同的買主與賣主之間進行選擇。自由是實現美好生活的重要條件。雖然並不是每個自由人總是能作出好的選擇,但是不是自由作出的選擇肯定不是一個好的選擇,政府的功能就是允許個人在追求美好生活中作出個人自己的選擇。所以,好的政府肯定是幹預公民自由選擇的權利受到嚴格限制的政府,即有限的政府。所以,政府即使是處於善良的動機也不應該越出爲保護個人的自由而爲其設定的行動範圍。
如果一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個人的自由,如果承認選擇的自由是一切選擇的前提,那麼自由選擇的廣泛存在本身就爲個人的自由創造了條件。然而,進行這些自由選擇的人是不是全是有責任心的人呢?有些人是,有些人不是。即便如此,也只有在自由的條件下,才能培養出人的責任心。自由的環境也許不是培養責任心的全部條件,但卻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而且在這種自由的環境中,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都是有責任心的。比如說,多數人與花別人的錢相比,更能把自己的錢花到有效的地方,花自己的錢比花別人的錢更算計。任何無視這一基本規律的經濟體制和所有制都已被證明完全行不通。當然,說多數人是負責任的消費者,並不等於說,這些人都是品行高尚的人。
在自由的環境下,人們都能展現出人性中最高尚、最光輝的一面,當然也肯定會暴露出人性中不太高尚、不太體面的一面。儘管如此,這裏根本不存在存高去低的選擇。一旦低的東西被徹底去掉了,高尚的東西由於失去了對照也就變得不高尚了。而且去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低的表像的背後所潛藏着的人的基本本能是不可能、而且也不應該徹底抹煞的。所以,與頭腦中的理想世界相比,現實中的自由世界總是與衆多的缺陷、不足相伴隨的。另一方面,自由,尤其是經濟自由是培養美德的溫室,爲了給自己積累財富,人們必須節儉、審慎、勤勞。如果自由是最基本的價值,那麼,經濟自由就是一切其它自由的基礎。凡是損害經濟自由的,最終也必將損害到其它自由。對經濟自由的壓制必將導致政治自由的消亡。
無限政府:奴役之路
包括適用於經濟事務在內的自由選擇是美德的形成和發展所必需的,自由市場經濟帶來了自由的選擇,因而也促進了美德。當然,經濟自由絕不能保障其所帶來的一切都是美德,但是當經濟自由受到限制時,美德的出現就變得更加困難了。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政府直接擁有和經營大量的財富不可避免地要帶來經濟上的腐敗,這種腐敗表面上是官員自身的腐敗,事實上,卻是對整個社會道德狀況的敗壞。因爲官員的腐敗需要民間的配合。即使政府爲了幫助個人而插手經濟,也是害大於利,因爲這必將削弱一個人的道德,敗壞一個人的自立能力、進取能力及其對自己的責任心,以及對他人的關懷,並導致個人對國家的依附,而國家已經自動證明,它自身是不可依附的。
哈耶克發現,自由的重要性,並不取決於行使該項自由的行動是否具有崇高性。行動的自由,即使是從事平凡而日常事務的自由,亦與思想的自由同等重要。…人們常常把通過“行動的自由”稱爲“經濟的自由”來貶低這種自由的價值。…更重要的是,是否存在着純經濟的行動,以及對自由的限制是否能夠侷限在那些所謂的“經濟”方面,都存在着極大的疑問。(《自由秩序原理》,第36頁)經濟自由是一切其它自由的保障,併爲其它自由的擴展提供了最有效、最可靠的途徑。舍經濟自由去追逐政治自由和其它自由,無異於緣木去求魚。
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無非是要創造更多的財富以改善人類的生存狀況。公民若是沒有從事經濟活動和支配自己財產的廣泛自由,也就沒有創造財富的自由,因而也就創造不出大量的財富。所以,要把創造財富的自由落實在社會制度上必然表現爲以財產權爲基石的自由市場經濟。沒有經濟自由,其它自由可能隨時會被剝奪;沒有財產權,其它權利都是空話。沒有屬於每一個個人的財產權與經濟自由,就沒有自由市場經濟。相反,計劃經濟則導致政府權力的嚴重膨脹,政府幹預的範圍無限擴大。哈耶克認爲,首惡乃是無限政府,所以任何人都沒有資格行使無限的權力。(《自由秩序原理》,第195頁)而經濟自由正是阻礙無限政府的屏障,達至有限政府(限政)的通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