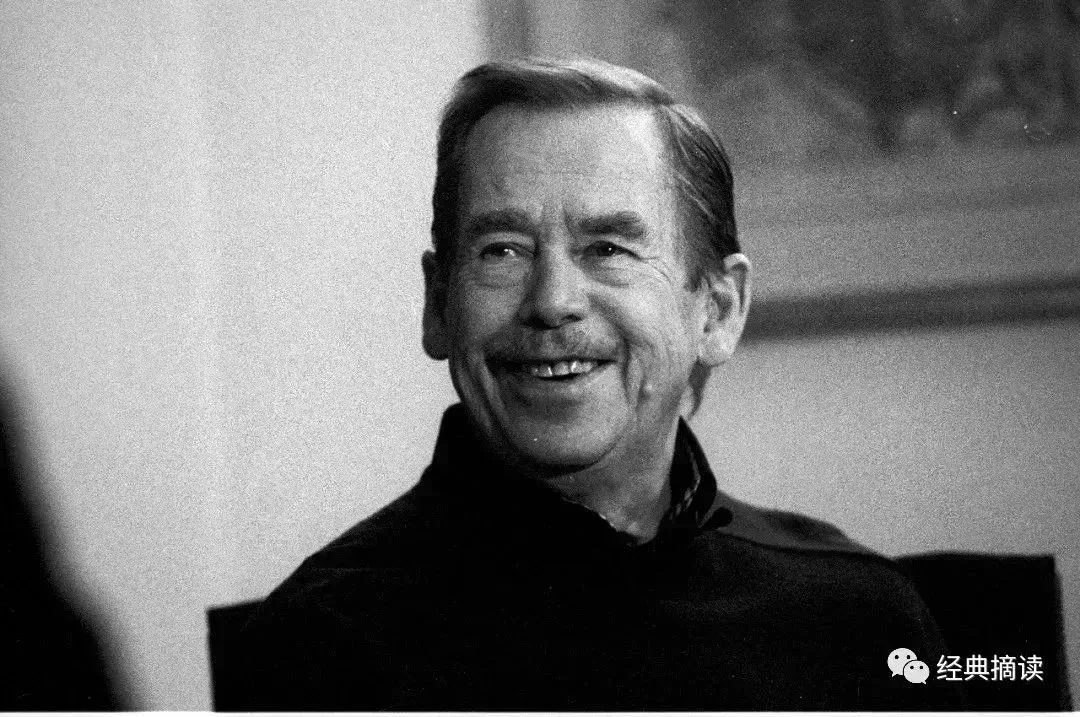
《哈維爾文集》序
哈姆萊特是莎士比亞最著名的劇作中的最著名的角色,瓦茨拉夫·哈維爾是當代捷克劇作家、思想家。我在閱讀哈維爾的作品時,常常由他想到了哈姆萊特。一個是經典劇作中的虛構人物,一個是現代荒誕派劇作家;一個是爲報殺父霸母之仇的王子,一個是在世紀性鉅變浪潮中成爲國家領導人的公衆人物,二者有何關係?我看到的共通之處是:對存在的意義的不斷追索,對人間苦難悲天憫人的情懷,對流俗之見的質疑和挑戰,對當下經驗的超越。
在人們的印象中,哈姆萊特是延宕不決的典型,他遇事不能決斷,永遠沉浸於對自己的提問:“活,還是不活,這是一個問題。”其實,哈姆萊特並不缺乏行動的大智大勇,他要在行動中探求人生或存在的根本意義,他眼神迷茫,實際是力圖從周遭的紛擾中求索善惡的本質,他視自己面臨的血海深仇爲小惡,斷定整個世界不過是一座大監獄。
哈維爾也是如此,他從社會生活的表面穩定和物質性追求與滿足中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墮落與衰朽,他鄙棄經世不變的格言:“政治即權力的藝術”,他在鬥爭中堅守良心的維度,在行動中體現存在的意義。
當然,哈維爾並不全然等同於哈姆萊特,他並不時時耽溺於內心的思索與獨白,而總是體察社會生活的脈動,他長於自省,但行動上並不猶豫反覆,他是有血有肉的劇本人物——他的劇本,莎士比亞的劇本——即典型的理想人物,他的生活曾與舞臺相關,然後從舞臺走向世界。
存在與責任
和哈姆萊特一樣,哈維爾始終擺脫不了“活,還是不活”這種問題的糾纏,他認爲,人與動物——它們僅僅受生存本能的支配——的根本區別是用下面這個簡單的問題即對生存本能質疑:是否真應該活着,如果是,那又是爲什麼?他知道,人們會找出各種理由,有物質方面的、有精神性的、有鄙俗的、也有理想的、說明生命值得留戀。哈維爾不滿意這樣的回答,因爲上述種種生活的內容既可以賦予生命以意義,也可以使這種意義喪失,既可以成爲活的理由,也可成爲不活的理由,他不要從生活裏各種具體的價值和理想中找理由,而要人作爲這些價值和理想主體即人類存在中找理由。
生活不時會給人極大的樂趣,使人自發地感覺到生命是有意義的,但這些事情不過是漂浮的虛無海洋上的“意義的島嶼”,其間的間隔會對意義構成威脅。另外,對生活中的樂趣也可以追問:“這又怎麼樣呢哈維爾感興趣的不是這些隔絕的島嶼,而是它們的底層,他想知道它們實際上是不是連綿的海底山脈的可見峯頂。
哈維爾的思考過程極其艱苦、曲折,他的結論具有形而上學的抽象性,晦澀性甚至神祕性,但思路還是清晰的。他認爲,雖然人具有獨特性,即只有人才是自己向自己發問的存在物,但他同時認爲人在意義問題上並無特權,“歸於生命的每一種,‘存在性’意義在本質上都意味着與‘意義的總體’的神祕性,即存在的意義相關……”人應該與宇宙達成新的、深刻的、充分的統一。並不僅僅是我們渴望與存在的意義相關,存在的意義本身也趨赴我們。
在哈維爾的抽象思辯中,人生的意義和存在本身的意義是相通的,另一方面,人又是這樣一種奇特的存在物,被拋向存在的根源處和被拋向現實世界不是獨自分離的兩回事,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回事。“如果我們不是起源於存在,我們就不能得到被拋入現實世界的經驗,而如果我們不是存在於現實世界,我們便不能得知源於存在的經驗,”這就是人與存在的異化:不能停留於原地,要通過與現實世界的遭遇來規定自己,實現自己。
由此產生了哈維爾長久思考,總是對於他視野中心的另一概念:責任。在他看來,責任是人的身份(IDENTITY ,又叫“認同”,即人之所以爲人,人區別於其他存在物的特性生成、持續和消亡的基本點,它是基石、根本、重力的中心。什麼是責任?說到底這是人與現實的二元關係:負責任的人和他對之負責任的人與事。
責任從何而來?宗教信徒將其理解爲他與上帝的關係,其他人將其歸結爲人與社會的關係:它來自教育、文化、傳統,等等。這些回答都不錯,但哈維爾並不滿意,他認爲這是把責任(此處有缺漏)我曾說過,“人的身份不是一經選定就終生不變的道路,相反,它要不斷地重新確立。事實上,人永遠是‘無牽無掛的’,我說這話時想到的是,信念是一種精神狀態,不能具體化爲完滿的,一旦得到就再也不變,不再成問題的東西,如果是這樣的東西,它就只要求人們爲此奉獻,而不要不斷地返回到出發點。“如果是這樣,就不是信念,而是狂熱的盲信,它對思想懶惰、性格懦弱的人有極大的誘惑力。還有這樣的人,”雖然可能本來確實不願意背離存在,但十分缺乏知識和道德的勇氣(包括不隨大衆特立獨行的勇氣),沒有這種勇氣是不能真正面向存在的。抗拒不了自我欺騙的吸引力的人以特別極端的方式面向存在,在此假象之下卻掩蓋着對現實世界的屈服。這種人所做的是‘緊隨觀念’,盲目地爲之服務……一個人越是狂熱盲信,他的‘信念’就越容易轉向另外的目標:可以在一夜之間變成信奉上帝,反之亦然,但獻身的激情卻是不變的。”
狂熱盲信使生活簡單,因爲對意識形態、教義和宗派的熱愛代替了對真理、自由和正義的熱愛,對一個目標的熱愛代替了對人民的熱愛,但代價是對信念的毀滅,悲劇發生了,本來是要承擔和解救世界的苦難,結果則是增加了苦難,狂熱和盲信者參與了鎮壓民主和大屠殺,只有在這時人們才發覺事情不對,但爲時已晚。
對於哈維爾來說,他的信念出自自身的力量,出自對生命意義的理解,而不是出自傳統的樂觀主義,即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廉價的樂觀主義者可以被一個外在的偶然事情推入悲觀的深淵,他們總是在熱情澎湃與虛無主義之間循環。哈維爾認爲,他比大多數人更少幻想,因爲他有信念,他不是對勝利抱有信心,而是相信生活。他不在乎世界上發生了多少事,只對事情是否有意義和有什麼意義感興趣,他認爲,沉默地、始終不渝地支持自己的立場,比高聲喧譁又很快放棄要好得多。
荒謬感
哈維爾被人們認爲是荒誕派戲劇家,當有人問到他的荒謬感和戲劇創作的關係時,他回答說,這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他強調意義與荒謬的互補性:荒謬即缺乏意義,這種感受愈深,對意義的追求就會愈積極;沒有同荒謬的經驗作殊死搏鬥,就沒有要追求的東西;沒有對於意義的內心深處的渴求,就會被無意義所傷害。
哈維爾曾經深入地談起自己對於荒謬的體驗:“人們可能以多種方式體驗到荒謬:通過個人的自省,或通過交談;它可能是一陣強烈而短暫的情緒,也可能是人一生中深刻的、主導性的情感。雖然不能說荒謬感是我最強烈、最深刻和最基本的感情,但我覺得自己一直有看到世界荒謬一面的強化傾向,因此我可能比別人對這種情緒更爲敏感。”“在我的理解中,荒謬感決不是對生命的意義失去信念的表現,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義的人,那些把意義當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體驗到缺乏意義是痛苦的,更準確地說,只有他們才能領悟到這一點,在令人痛苦的意義缺失狀態,它反而比在其理所當然、無可置疑存在時更真切地呈現出來,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麼是身體好一樣。我認爲,真正的無意義和真正的無信念表現得不大一樣,後者表現爲冷漠、無情、自暴自棄,把存在降低到植物水平。換句話說,體驗荒謬與體驗意義密不可分,只有荒謬是意義的另外一面,就像意義是荒謬的另外一面一樣。”
由此看來,對於荒謬,哈維爾這位荒誕派戲劇家和某些中國小說家的理解大不相同,對他而言,荒謬是令人痛苦、焦慮、理不當此的事,對某些中國作家而言,荒謬是世界的常態,是免去人的責任、令人寬慰的事,對哈維爾而言,荒謬和意義之間是一種既分又合、相離相依的辯證關係,而在某些中國小說家筆下,二者的關係不過是有你無我、相互否定。
哈維爾下面的話更能證明上面對他的理解:“荒謬是這樣的體驗,某種東西有意義、應該有意義或本來能夠有意義,即它本質上是人性的,但它卻全然沒有意義,或喪失了意義。因此,荒謬是體驗到與存在脫離接觸,體驗到賦予意義的力量的瓦解,體驗到一種人性,它發現它欺騙了自己,‘迷失了方向’——正因爲如此,它迴歸自己正確的道路:意識到意義的缺失,渴望意義自己再次出現……荒謬是體驗到面對存在之‘我’與屈服於現世存在之‘我’的對照,是體驗到孤獨之人與他自身的對照……在荒謬中,世界的異化並不是必需的,我們並沒有被‘先在地’拋入荒謬中,相反,荒謬是這樣的東西,它並不已然存在,而我們將自己拋入其中。難道這不正是真正的荒謬開始之處。
因爲持有上述見解,哈維爾主張,不能把荒謬當成先天消極,甚至應當嚴加斥責的東西,在某些地方,荒謬的體驗可以推動事物前進。在許多情況下,正是這種對於世界的疏離和異化的感覺,這種拋棄了舊有的俗套體驗的感覺,打開了新鮮、銳利而有洞察力的眼界,這獨具一格的眼界使我們直面真理,並通過它的懷疑能力衡量出意義的真實份量。
生活在謊言還是真實中
哈維爾並不生活在精神世界和內心生活中,他關注現實,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與一般政治家或政治活動家不同,他從精神層面看待政治,以道德的標準評判社會和政治生活,他鬥爭的目的是人性的迴歸。

1968年,以蘇軍爲首的華沙條約國部隊突然襲擊,侵佔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扼殺,推行改革的總書記杜布切克被擄掠,然後靠邊。靠坦克維持的蘇式政權大搞清洗和逮捕,然後推行“正常化”。表面安定的局面有了,人們噤若寒蟬,但這死水一潭的局面對整個民族意味着什麼呢?
1975年4 月,哈維爾寫下了致總統胡薩克的公開信,揭示安定掩蓋下的危機和全民族付出的道德代價。哈維爾在信中說,如果只看日常生活的表面,只從統計數字和官方報告來衡量,國家成功地獲得了安定,但如果從社會的道德與精神復興,人性和自由的擴展,人的尊嚴的提高這種角度看,社會並不是安定的,而是處於空前的危機之中。因爲人民對政府的服從、社會表面的團結,根源只是人們的恐懼。他們重複自己並不相信的話,做自己並不情願的事,是因爲在這個國家幾乎每個人都有生存的壓力,在本質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損害,都有可失去的東西,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感到擔憂和恐懼。
與恐懼相聯繫的是善惡觀的淪喪和言不由衷。“在這些情況下,政府工作人員上上下下都在搞腐敗,他們隨時隨地敢於公開收受賄賂,寡廉鮮恥地爲一己之私利和貪慾行事,這種情況在最近10年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現在真正相信官方宣傳和盡心支持當局的比任何時候都少,但虛僞之徒的人數卻在穩步上升,以至於每個公民都不得不變得口是心非。……無望導致冷漠,冷漠導致順從,順從導致把一切都變成例行公事——有人把這當成‘羣衆投入政治’的例證,現代的‘正常’行爲的概念就是由這一切構成的。這個概念實質上是極可悲的。”
哈維爾指出,人們愈是徹底放棄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對超越個人的目標和價值感興趣,放棄“向外”發揮影響的機會,他們就愈加把精力轉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大練“內功”,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他們裝修住宅、購別墅、買小車,他們滿意地享受着選購這種牌子或那種牌子的洗衣機、電冰箱的自由,而沒有分享經濟決策、參與政治生活和發揮才智的自由。人們把真實生活的無可奈何的替代方式當成人性的生活。當權者對待這些只能自保的生物採用的手段是有效的,他們選擇了最不費力的路,但完全忽視了他們必須付出的代價——對人格的粗暴踐踏和對尊嚴的無情閹割。
哈維爾尖銳地指出,秩序建立了,但代價是精神的麻木、心靈的寂滅,表面的安定取得了,但代價是社會的精神和道德危機。人們匆匆放棄昨天還拒絕放棄的立場,社會良知昨天還認爲不好的事,今天便被理解,明天就被視爲理所當然,後天就成了楷模。在最近幾年,對於什麼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人們的評價不同了,社會的道德態度變了,這種變化比想像的更爲嚴重,因爲人們日趨麻木,對麻木的自知力也在下降。“誠然,國家有安定的局面。但難道你不會說,它安定得像停屍房或墓地。
在《無權勢者的權力》一文中,哈維爾用“後極權主義”來指稱他所在的制度,“後極權”並不表示不極權,而是說它與古典的極權方式有所不同。其特點之一是,這個制度起源於一個社會運動,它宣稱對於歷史發展和社會矛盾有“正確認識”。
簡言之,後極權主義十分依靠意識形態,它的原則是將權力中心等於真理的中心。“在這個制度下,生活中滲透了虛僞和謊言;官僚統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名義下被奴役;把徹底使人渺小說成人的完全解放;剝奪人的知情權叫做政令公開;弄權操縱叫做羣衆參政:無法無天叫做遵法守紀;壓制文化叫做百花齊放;帝國影響的擴張說成是支援被壓迫人民;沒有言論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鬧劇式的選舉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殺獨立思考成了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佔領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爲政權成了自己謊言的俘虜,所以它必須對一切作僞。它僞造過去,它僞造現在,它僞造將來。它僞造統計數據。它假裝沒有無處不在、不受制約的警察機構。它假裝尊重人權,假裝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什麼也不怕,假裝從不做假。”
哈維爾的深刻之處在於他指出,後極權制度的出現和存在,並非歷史的錯誤,而在於現代人性中,明顯地有使得這個制度產生,至少是容忍這個制度的傾向。“人們被迫生活在謊言之中,但他們能被迫這麼做,只是因爲事實上他們可以這樣活下去。因此,不僅是這制度使人性疏離,同時,是疏離的人性支持了這制度……這成了人性墮落的寫照。人們作爲人失敗了的見證。”
哈維爾主張反抗謊言,應付人性和道德危機的方式,就要鼓起勇氣真實地生活。這是要重新承擔責任,從自身條件出發,不放過每一個自由表達生命的機會,不指望今天的犧牲能帶來明日的收穫,人們只能管耕耘,而不能問收穫。
道德與政治
蘇聯入侵以及隨之而來的高壓,毒化了社會生活的空氣,使人精神退化、心靈萎縮。哈維爾認爲,社會和民族面臨的不僅是政治危機,也是道德危機。隨後爆發的“七七憲章運動”——哈維爾是其主要的領導者——目的不是要爲危機求得政治解決,而是要表明一種道德立場。他強調,運動不是出自理智的計算,而是受良心驅使。這是公民對道德墮落真心實意的反應,堅持要憑自己的良心行事,反抗壓力,衝破個人利益和恐懼的約束,重新像一個人那樣挺起腰來。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者,那些剝奪了言論和行動自由的人,正在抬起頭來、拒絕謊言、勇敢地行動,力圖行使做一個負責任的人的權利,恢復人的尊嚴和身份。
爲什麼這場運動的目標不是政權?哈維爾回答說,權力從來不會獨自存在,它支配人也來源於這些人。他說,我們這個社會的權力運作,並不簡單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權力支配另一些人,每個人都被迫成爲權力機器上的一個部件,因此常常很難指出誰要爲政權的所作所爲負責。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他一方面是奴僕,畏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隸主,想踐踏下屬。專制制度就是以這種方式把整個社會納入它的系統,使人不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創建者;人們既是囚徒,又是獄吏。當然,在參與和協助的同時,人們也有反叛之心。
在哈維爾看來,“七七憲章”運動的特色是公民意識的再生,是公民良知和自覺的甦醒。沒有公民就沒有政治,政治不能刷新公民操守,相反,公民操守是政治的前提。這就像建房不能從屋頂開始,只能從地基造起一樣,憲章運動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自由和權利是不可分割的:一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受到侵害,這意味着全體人的自由和權利受到威脅,如果一個社會人們因冷漠而孤立,對身邊發生的剝奪與迫害漠不關心,那麼任何人都休想從壓制中解放出來。
哈維爾申明,他所參與和領導的運動是要影響社會,而不是權力結構,它要向社會隱蔽的領域發出呼籲,指出人和社會的出路是生活在真實中。他把自己所欲達到的深刻變革稱爲“存在的革命”,它應爲社會和道德重建提供希望,這意味着要完全更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成一種任何政治秩序都無法代替的“人性秩序”。
在這個制度之下,各種組織結構將由新的精神即人性因素髮展起來,而非出於形成特定的政治關係和保證,問題是要復興諸如信任、開放、責任、團結、愛等價值。他表示,他只相信那些目的不是在技術方面行使權力,而是追求行使權力的意義結構,它們結合在一起是因爲對於某些共同體的重要性具有的感情,而不是對向外擴張具有共同的野心。這些結構是開放、動態、小型的,完成目的之後就會自行消失,不應該建基於悠久而空洞的傳統,不是爲形成組織所作的戰略性結盟。只有以共同體中每一個成員的充分存在爲基礎,才能保證極權主義不會在不知不覺中蔓延。這些結構應該作爲真正的社會自控組織的產物從下面自然地發展出來,它們應該同產生了自己的真實需要不斷對話,以獲得生命力,一旦這些需要不再存在,這些結構也要消亡。
當哈維爾發表上述見解時,他是被體制排斥的知識分子。若干年後,他還能不能堅持以前的道德理想呢?他是在竭力做到這一點,在一篇爲《政治、道德與教養》的文章中,他說:“我有責任再三強調所有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價值與標準在所有社會生活領域,包括經濟活動中的意義。”他批駁只用暴力革命和政權轉移來解釋歷史的觀點,說前政權是被生命、思想和人類尊嚴推翻的,“有人仍然宣稱,政治主要是操縱權力和輿論,道德在其中無容身之地,這樣說的人根本不對。政治陰謀其實不是政治……一個人也許參與搞陰謀輕易當上總理,但他的成功也就是到此爲止;人要使世界變得更好,不能靠搞陰謀……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這名稱,我唯一願意投身的政治——就是服務於周圍的人,服務於社會,服務於後代,政治最深的根基是道德……”
他在談到自己從政後的體驗時說:“儘管我每天都面對政治煩惱,但我仍然深信政治從根本上說並不是不光彩的事。要說不光彩的話,那也是不光彩的人弄的。我得承認,比起人類活動的其他領域,政治更能誘使人做出不光彩的事,因此它對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要說政治家必須撒謊或搞陰謀詭計,那是完全不對的,有人散佈這種說法是想打消別人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
哈維爾堅信,“如果我們不建設一個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國家,我們決不能建立於一個基於法治的民主國家。如果不以某種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爲基礎,最好的法律和設想得最好的民主機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內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權……沒有共同擁有和廣泛確立的道德價值和責任,就沒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正常運行。”
社會轉型和市場經濟
政治的巨大變化把哈維爾推上了重要位置,他執政期間,捷克的經濟體制緩慢地、相對於其他國家較爲穩妥地由計劃和中央集權型轉變爲以市場爲主的多元經濟。最令人注目的地方是,這個國家的體制轉軌在社會公正方面引起的問題是最小的。這當然是全體人民和經濟專家共同努力的結果。而哈維爾的有關思想和言論,也是這個較平穩地發生根本變化的過程的一面鏡子。
在發表於1991年的“我相信什麼”中,哈維爾從原則上闡明瞭市場經濟的長處和舊體制的弊病。他說,雖然他一直有社會主義傾向,但他知道唯一行得通的經濟制度是市場經濟。這是唯一自然的、可以導致繁榮的經濟,因爲只有它反映了生活自身的性質,生活的本質具有無限的、不可捉摸的多樣性,因此它不能被任何集中性質的智力所包容和計劃。企圖把所有經濟實體聯合起來,置於國家這個唯一的超級所有者的權威之下,使全部經濟生活聽命於中央(它自以爲比生活本身還要高明)的聲音,這是企圖反對生活本身,這是現代人僭妄的極端表現,他以爲自己對世界有透徹的瞭解,處於創造的頂峯,因此能夠支配全世界,他不知道自然、宇宙和存在和秩序是無限複雜的結構,他自己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舊體制之下的經濟產生於一種狂妄自大的、烏託邦的理性,它使自己凌駕於一切事物之上,當這種烏託邦理性付諸實施時,它肅清一切與之不合的東西。與這種崩潰的中央經濟歷史現象相伴生的,是言論審查、恐怖和集中營。
哈維爾說,雖然市場經濟對人像空氣一樣自然和不言而喻,但他擔憂並認爲危險的,是某些人的思想方式,他們把改革的某些方面變成意識形態,變成偏狹的教條和狂熱。有些人瘋狂相信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把市場和道德看成互相排斥的東西,有些人從左傾意識形態狂熱一下子變爲右傾意識形態狂熱,有人像當年擁護革命口號“一切權力歸共產主義者”那樣,利用現在的權位化公爲私。
哈維爾也清楚地看到,社會轉型期產生的錯綜複雜的問題,有許多是舊體制遺留下來的,有不少人仍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爲在前幾十年的建設過程中,自然的市場經濟機制被人爲地中斷,因此,現在發育中的市場經濟的問題,不能純然靠它自身求得解決。政府在發展經濟方面還應當起到巨大的作用,簡單說來,它的主要責任有以下三方面:一、制定遊戲規則的框架;二、作出宏觀決定;三、制定具體的日常經濟政策。而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國家的經濟領域的作用會越來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