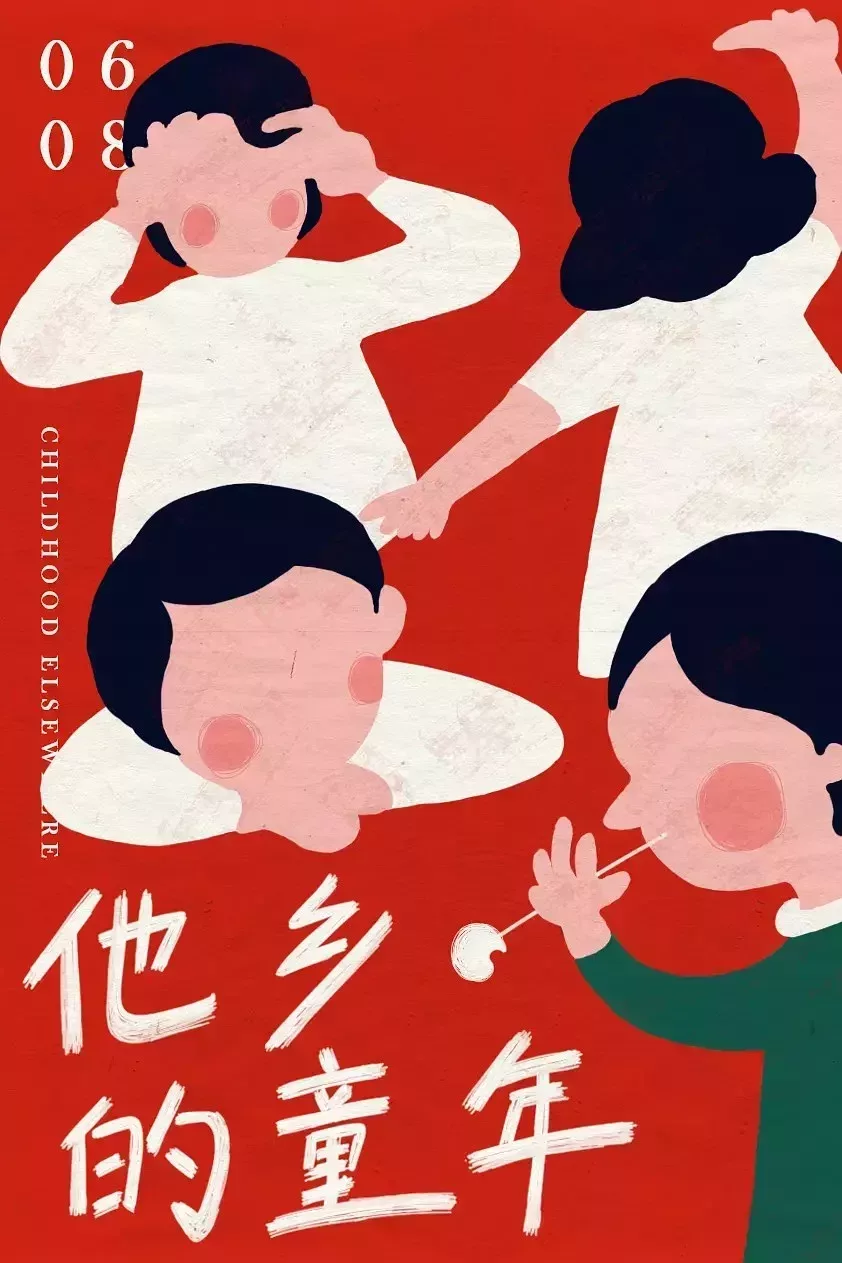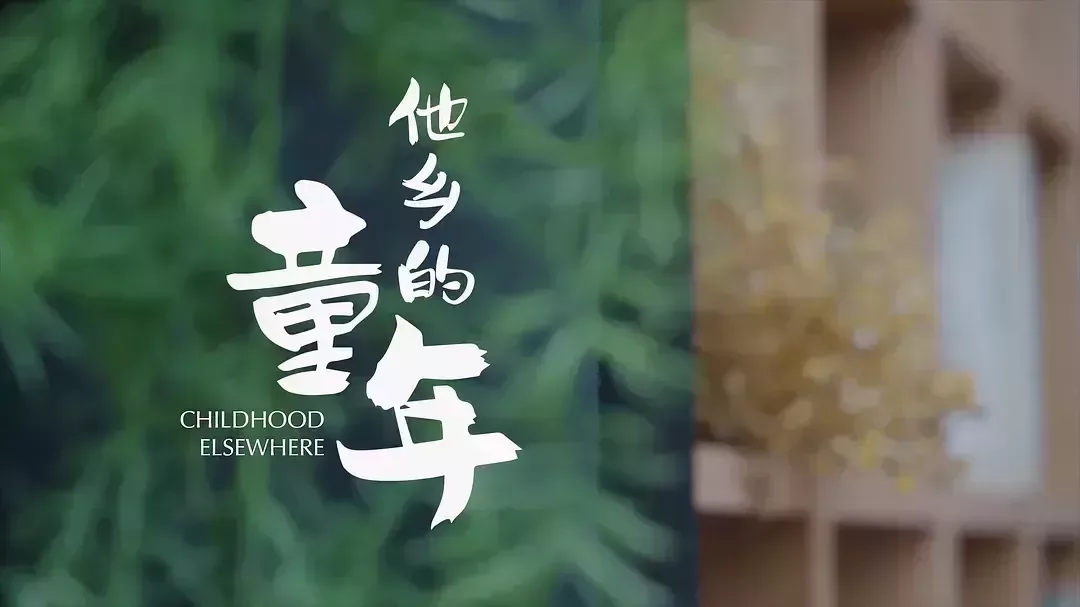
《他鄉的童年》播出了第二季,有人看了嗎?
以前覺得,不婚不育,有什麼必要看世上這些發達國家,怎麼教育小孩?
現在的心情變了。不是的,人應該被怎樣養育,不僅僅是童年的功課,是活着的每一天,都可以向自己提問的事。
朋友和我說過,「在畢業之前,爸媽爲我付出的錢,只能說是讓我活着。活着和好好養着不一樣,經濟獨立後,我爲自己所付出的,纔是真正的養育。」那是一種不討好,不拘謹,不用向誰彙報的新生活。
《他鄉的童年》第二季給人最強烈的感受,就是作爲一個大人,如何養育自己的情緒。
如果你也很愛生氣,很容易焦慮,覺得生活真的很煩很煩,歡迎進入這個,我認爲是送給成年人的舒心一課。
都不用去按摩了,氣統統順了。
很容易生氣,也許是我們越來越只能看見「健全人」了。
新加坡有一所幼兒園,被稱爲全納幼兒園。
在競爭激烈的新加坡教育制度裏,這是一間告訴孩子,你可以「等一等」的學校。
70% 是健全的小孩,30%爲特殊兒童。小孩裏包含了做過開顱手術,無法正常說話的孩子,我們熟知的自閉症兒童,視障小朋友等等。
無法行走的兒童,將獲得動物主題的輪椅,坐上去感受到的是「特別」,而不是「累贅」。

在這裏,所有的小孩都會用手語,不僅是爲了聽障兒童,也爲了那些學習說話比較慢的孩子,語言學得晚,沒事的,我們可以等一等,先用手交流。
特殊教育的學校哪兒都有,但全納學校,卻是少見的。
周軼君提出疑問:「爲什麼要這些特殊的小孩,跟健康的孩子一起上課?我一直以爲新加坡是一個以戰績爲導向的社會。」
老師回答說:「光有書本上的聰明才智是不夠的,你必須要學會如何互動,如何應用那些無形的東西,是這樣的互動使人之爲人。」
在我們的成長裏,那些所謂「不夠好」都被否定了,所以偶爾遇到需要等一等的時刻,會變得格外地沒有耐心。
前兩天上班坐扶梯的時候,電梯在中途突然停下,我被嚇了一跳,探頭一看是前面有人的行李箱壞了,書本散了一地,工作人員緊急按停。這樣的「中斷」讓我很煩躁,電梯上的大家也忍不住了,大喊着停下來幹嘛,繼續走啊。
此時工作人員蹲下來和對方一起撿行李,每個人從他們身邊邁過,略過地上的人和物。

這樣容易生氣,耐心消失的時刻,也常常發生面對孩童時,前段時間廣爲流傳的一條視頻,是飛機上的小孩哭泣,被陌生的大人拉到廁所鎖起來,美名其曰教育孩子。
當我們認同並實踐「每個人都應該不讓別人感到麻煩」的生活後,耐心就消失了。
周軼君在離開全納幼兒園時說:
「在這所學校長大的孩子,他們會看見,這個世界,不光有卓越的人,也有普通人,殘缺的人。」
小時候沒人教我們看見,但長大了,我們能做出「看見」的選擇。練習看見不夠好的人,不夠好的事,就不再會感到負擔,感到「費力地做了件好事」。
你有觀察過,自己一天時間裏什麼時候最煩嗎?
每天晚上十一點,是我的貓準時鬧着砸門的時間。
打開門,它經常哪兒也不去,只是蹲在門外與室內之間。走廊的盡頭是半人高的護欄,有墜樓風險。
和左鄰右舍完全不認識的情況下,長時間開着門,它不安全,我也不安全。
所以我經常會任由它嚎叫,時間可能會持續半小時,它煩,我也很煩,我會忍不住罵它,喊得喉嚨疼。
是看《他鄉的童年》第二季時,我從一個德國家庭那裏,意識到改變的可能。

周軼君去到一箇中德家庭中拜訪,對方家裏有個女兒,她的媽媽一邊接受周軼君的採訪,一邊回應女兒的聊天。
女兒讓媽媽看自己怎麼戴面具,戴反了,戴正了,都沒有關係。又或者是中途跑過來,找媽媽說面具壞了。
正在接受採訪的媽媽,會自然地轉頭看她,接話說:「壞了呀,那我們再重新做一個。」手上在做着新的面具,但依然可以繼續回答採訪的問題。
最後,女兒又戴上新的面具,媽媽和周軼君中斷了對話,兩個人把眼光都看向她,回應她。
一整個上午,周軼君都感到,這個家庭意外的安靜祥和,因爲「孩子被包容着,孩子被允許犯錯,於是也就不會用挑釁來吸引大人的注意。」

我低頭看到剛剛在大喊大叫的貓,此刻躍躍欲試準備跳起來咬我。
怎麼說呢,我需要承認,這份煩躁,是我的沉默帶來的後果。於是,我拿着手機,一邊看片,一邊走向玩具箱,抽出一整包彈力球。
8 顆扔完,再撿起來扔一次,16 個來回,就足夠讓貓感到滿足,而這個過程中,我也不需要停下自己正在看的劇。
我發現,當它得到回應後,就會蹲在我的腳邊,懶懶地趴着,不再發出喊叫聲。
沒有什麼樣的「心煩」是不可解決的,可能只是懶得解決,於是帶來更加倍的情緒負擔。
恐懼的情緒,比實際的冒險,要更危險。
在新西蘭,孩子從小要學習的事,就是玩。
新西蘭的小學,老師不會規定學生要遵守怎樣的規矩,他們操場被稱爲「無法無天操場」,孩子可以爬到樹上,房子上,鞦韆上不會限制人數。

每一個孩子的動作,都足以讓屏幕前的我們皺緊眉頭,看起來都充滿着受傷的可能性。
但校長任職的 7 年時間裏,發生過最嚴重的傷害,就是學生摔斷腿或者胳膊。「我以前的學校,有很多規矩和制度,但也每週都有人摔斷腿。」
也許是因爲不受限,反而更容易探索到,自己的身體邊界在哪裏。
學校不會管孩子玩得看起來風險有多高,但會帶領學生一起檢查每一根木棍,是否有釘子突出,教他們用錘子一顆一顆地敲進去。
孩子們舉着很長很厚實的木棍進行炮擊遊戲,教周軼君,要怎麼甩弄棍子,才能避免真的傷害到同學,他們還懂得走路時把樹枝撿到一邊,避免別人絆倒。
因爲對自己擁有掌控感,所有的限制被扔掉了,允許想象,允許冒險和發揮,於是連帶着講話都充滿自信,對世界有無盡的好奇心,他們會直接走上前問攝像機是怎樣用,可以玩一玩嗎?

那麼,爲什麼我們這樣的大人,還需要看孩子怎麼玩呢?
我想,可能比起對玩的想象力,我們更缺的是,對自己身體的想象力。
我們這些在 CBD 每天打卡上班的人,對自己的認知,往往是,腦子在變得越來越適應工作,也可以說是變得好用,但身體一日不如一日。
二三十歲的大人們,拖着這副殘軀,真的不想做點什麼嗎?身體比心承受得更多,它要承擔情緒崩潰的代價,也要承受年齡和工種的消磨。
這個夏天,一向不喜歡「動起來」的我,找到了讓身體好受些的辦法。我去學習游泳。
這個身體活動的前提,是要玩,不是要學會,不是要進步。
平時打工已經很辛苦,很難想象要帶着一種「自律」的決心讓身體也要「追求卓越」。
唯有帶着想玩的心,才能指引人放下恐懼,信任身體。體會到漂浮在水裏的快樂後,我雖然一整個夏天都沒有學會游泳,但我度過了,工作以來,最爲幸福的夏天。
在不工作的日子,和身體作伴,不是和手機作伴。
我們都要找到這樣一項身體性的玩樂,才能度過這城市裏的漫漫長夜。

這個片子裏有太多值得讓人想要標記的點。
法國的小朋友們,被老師派發的娃娃都是真實的寶寶長相。「她不是公主,她只是一個寶寶。」真實遠比虛假的符號更令人安心,也讓人與人之間,減少比較和打量。
不把孩子們互相比較的文化,在不同的國家教育裏多次出現。在新西蘭,學生寫論文「喫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被教授打了零分。大家都是平等的,爲什麼要做「人上人」,是爲了欺負下面的人嗎?
比較,競爭,內卷,幾乎已經融入我們的骨血,成爲像呼吸一樣習慣的事。偶爾換一瓶氧氣吸吸,雖不會對眼前的世界產生什麼改變,但見證,就是另一種程度的擁有過。

我們長大了,有更高的自由度,去選擇觀看什麼,相信什麼。
而我,則選擇在這樣的兒童教育片裏,花最小的成本,在一段時間裏把自己養得更舒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