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口號廣爲流傳。
國家興亡、匹夫有權,這句話卻從未聽過。
沒有權力卻談責任,如此的責權利不對等,卻依然被人津津樂道,這源於個人權利的缺失。
在古代,一切與“公”相關的詞彙,似乎都是褒義詞,比如公平、公正、大公無私。只要高舉“公”的旗號,就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壓倒一切。
而一切與“私”相關的詞彙,似乎都是貶義詞,自私、私慾、徇私舞弊。只要妄談個人的私利,就只能站在陰暗的角落裏、遭人唾棄。
很多人喜歡集體主義,否定個人主義。在古代的思想圖譜中,“個人主義”一直是個陌生的概念。
何謂個人主義?一言以蔽之,就是把個人‘當作’人來尊重。
古代的主流思想由儒、法、佛、道這四種組成,這四大思想與個人主義水火不容。

第一、儒家主張“大“我
“吾日三省吾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儒家主張自我反省,但目的卻是爲了人際交往而非個性解放,是爲了通過履行對他人的責任而達到秩序穩定。
儒家的“自我”概念,雖然講究自我修身養性,但儒家真正強調的卻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格局。個人修身只是這個宏大格局的起始點,而不是目的,個人不屬於自己,當然不能爲自己的權利辯護。
儒家的政治原則是秩序穩定,而非個人權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的社會纔是和諧社會。地位低的人對地位高的人絕對服從,愚忠愚孝被當作美德,這樣的思想怎會容忍個性的發展。
所以,儒家偶爾也會罵昏君,但不會罵皇帝,儒家同意推翻暴君,但不同意推翻暴政,皇帝輪流做,卻從沒像英國那樣產生過限制皇權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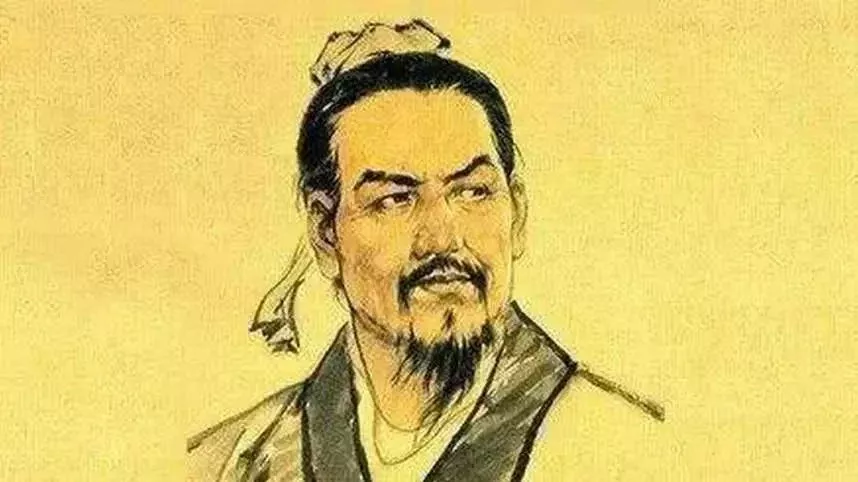
第二、法家主張“非”我
諸子百家中,法家離個人主義最遠。
在法家眼裏,民衆只是工具,只是牛馬。安平盡其力、有難用其命。
法家提倡用“法”來操縱民衆,所謂“法”,有功者賞、有過者罰,獎懲而已。法家提倡通過操縱法和權,建立一個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度進行壓迫統治,從而在極短的時間內增強君主的實力。比如法家是全人類第一個提出連坐制度的思想學派,他們強迫民衆背棄一切倫理道德相互監督告密。
因此,法家不是以人爲本,而是以君爲本。只要能夠增強君主的實力,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個人權利當然也在這個代價之內。

第三、道家主張“忘”我
道家主張天人合一、順乎自然。道家強調的是人的自然性而非社會性,主張忘掉功名、利祿、禮教。
在政治上,道家主張無爲而治, 他們認爲爭取個人權利毫無意義,最終都會歸於自然。
因此道家沒有介入社會,而是選擇了逃避。或縱情山水、或隱居終南,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這樣的道家不可能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來保證每個人所需要的個人權利。

第四、佛家主張“無”我
北美的清教徒認爲自己雖然在這個世界,但不屬於這個世界,他們要在塵世中建造一座山巔之城。
山巔之城就像佛家的機鋒一樣,也是一個萬能的隱喻。我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無法被隱藏。清教徒表現自己、實現自己的慾望不言而喻。
但佛家不同,佛家主張超脫,就是擺脫塵世中的本我,去極樂世界生活。
佛祖對弟子說:他只教兩件事,一是受苦受難的事實,二是脫離苦海的可能。從塵世獲得超脫的方法,就是心甘情願的喫苦、一心一意的打坐。
因此佛教徒沒有清教徒那樣的野心,他們不想待在這個世界,只想儘快往生極樂。
所以佛家不可能像個人主義所提倡的那樣在這個世界裏表現自己、實現自己。佛家的世界觀決定它不可能沿着個人主義的方向發展。
古代社會,儒法佛道這四種主要的思想,雖然都有自我的元素,但儒法主張改造社會,用禮儀和等級制度來規範個人,儒法最不願做的事就是顛覆社會秩序,因此外儒內法便成了官方顯學。
而佛道也不像西方那樣主張解放個人,而是提倡退出社會,不與等級制度衝突,因此雖然不是顯學,也未遭到全面打壓。

歷代的統治者都十分擅長用這四大思想來壓制個人主義的發展,用天道、民族、大義等等這些大帽子來壓制個人的慾望與價值,提倡剋制、犧牲、順從、守舊的順民品質。把所有人都打造成一個合格的臣民、家庭的一個部件、國家機器的一個螺絲釘、血緣鏈條上的一個環節,這也造成了缺乏自尊與榮譽感的奴隸人格。
古代的思想圖譜上,大概只有楊朱一人公開宣揚“爲我”的思想,但卻遭到全面的封禁。
孟子把楊朱和墨翟放在一起批判: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他們如此氣急敗壞,無非是個人主義對等級制度的瓦解。倘若每個人都有了自我的意識、爲我的可能,那麼等級制度自然便很難維持,這便是個人主義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