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巍出了新歌《我心燦爛》,九年前許巍曾以單曲形式發表了另一首作品《燦爛》。九年時間,可以讓一個少年完成義務教育,卻不能讓許巍在燦爛的心情裏順利畢業。如今的許巍是一個失去時態的人,他的創作沒有新歌老歌的概念,都是同一批關鍵詞,同一批邏輯下生產的同一批心情,只是分階段發佈而已,階段性發布如同給歌迷做思想彙報——我在這套世界觀裏生活,心靈時刻得到大保健。
在國內的音樂圈,許巍是少數擁有信徒式歌迷的藝人,這是他與汪峯、鄭均、樸樹等歌手的本質區別,外界經常將這幾人放在同一座標系裏比較,但許巍如今的路徑完全不同,他的作品已不完全在音樂賽道里競爭,而是靠提供類似身心靈的精神服務進行復合售賣,許巍的自我重複,大愛主題,是給信徒的良藥,這種理念需要反覆宣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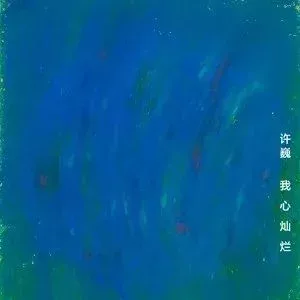
許巍近二十年的音樂有很強的迷惑性,主要許巍的狀態唬人,從一個搖滾個體戶變成了一個閱盡千帆的出世高人,質變的原因是什麼,而許巍的個人經歷,與感言式歌詞就成了問題的答案,本來許巍的個案並不具備普遍性意義,但因爲觀感良好,加上許巍自己以身試藥,許巍的音樂也隨着人設的改變成了殘酷生活的百憂解。
跟隨許巍,不是跟隨音樂,而是跟隨人生境界,許巍的作品如精神瑜伽,提供到達境界的方法論,展示修爲成果,對於有此類精神需求的人來說,許巍是最好的選擇之一,總不能選擇瓦依那吧。滾圈這個賽道許巍跑了二十年,沒有任何競爭者,他作爲唯一的生產力,無休止的重複也不會造成通脹,供需關係決定了市場。許巍用音樂佈道,信徒拿心靈買單。

很多人喜歡許巍低調的性格,他與行業的疏離感,確實容易讓人心生好感,但性格上的討喜,不應取代對其作品的真實評價,由於許巍性格低調,埋頭做音樂,所以他的作品便是好作品,這個邏輯不成立,也沒有這個道理。
許巍作品特點是無聊無趣,大而無當的人淡如菊,很難帶來任何審美上的愉悅,最多算養生指南。生活觀雲看海,內求自在平和,不是認知層面的事,而是人設層面的事,如果說許巍對傳統文化有所領悟,可能在於他發現了國民性的特點,盲從,願意相信成功者,願意相信神蹟。
許巍本身便是個盲從的人,好在他純粹,能做到真信,他的音樂轉型源於偶像交替,從西方到東方,從涅槃到佛祖,許巍的粉絲心態並沒有變化,相信什麼就用什麼衡量萬物。

早期相信西方搖滾樂,靠絕望找尋美感,樹立想象中的悲情。第一張專輯《在別處》的黑暗氣質,受到西方搖滾名人故事很大影響,流於表面,不成功是市場正常反應,並非明珠暗投。《在別處》裏所謂的力量感都中氣不足,黑暗氣質全靠堆詞營造,強行疼痛,有沒苦硬喫感,求歡不得的都市情歌,非要和滾人不得志的境遇拼單,雖然這份失落符合地下音樂敘事的模版,但背後真正的問題在於,他追求高度市場化的西方搖滾樂卻沒有清晰的自我定位,說着汪峯的話,拿着樸樹的範,難免彆扭。
汪峯可以靠專業能力緊貼市場,追逐名利雙收,樸樹清楚自己的形象優勢,越脆弱越是大衆寵兒,而許巍沒有形象優勢,他的脆弱並不能帶來價值增益,同時他又無法像汪峯那樣緊貼流行文藝,歌詞對豆瓣熱門條目進行有意收集。許巍那階段的至暗時刻,在於對西方搖滾樂入戲太深——自己做了滾人寶典裏必須做的100件事,卻沒有成爲搖滾明星,搖滾樂就不再可信了。
於是西方不亮東邊亮,曬盡憂傷曬殘陽,開始逆練九陰真經,轉頭國學佛學,成爲傳統的弟子,一下子對接上國民性和文化符號,敲開流行之門,新大路瞬間無盡光芒,比搖滾樂可信。許巍的修爲是一種結果論,哪條路能帶來成功,信仰就在哪條路上,信仰從不缺席,但可以更換,像風一樣自由。
假設市場對許巍這套國學瑜伽不買單,許巍是否有勇氣這樣重複自己呢?《無盡光芒》《此時此刻》《愛如少年》這三張專輯除了製作精良程度有所不同,內在表達有什麼區別?如今許巍不僅沒有了時態,主題也是千篇一律的務虛,這三張專輯裏的所有的歌打亂重組,不會出現任何違和感。這三張專輯連創作用的高頻詞都沒有更換過,許巍的堅持已經出現了躺平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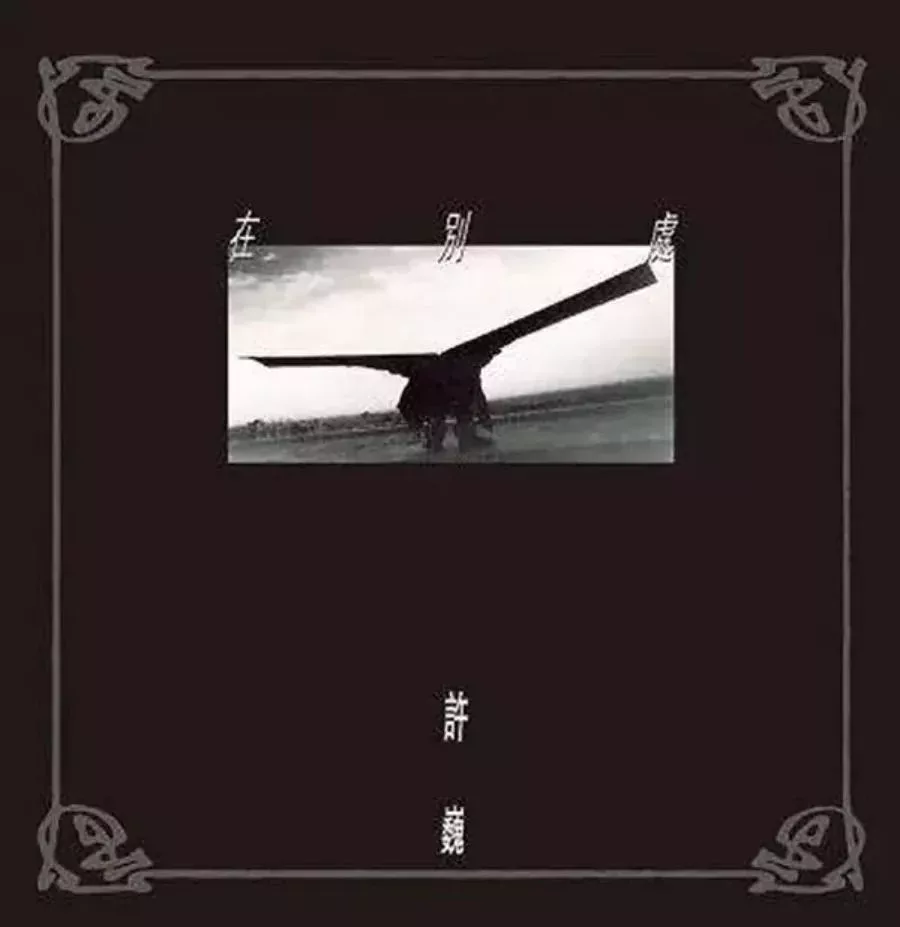
我不相信許巍意識不到這個問題,既然是看到一花一樹,雲舒雲卷都能有所感悟的高敏感人,爲何內心純粹,乾淨通透要靠無視現實來表現,這不叫活明白了,這叫玩明白了。
現在的許巍如同活在真空裏的人,用精神瑜伽屏蔽真實世界,盆景做森林,魚缸當大海,精神瑜伽幻燈片供養着他的真空生活,他已經沒有掙扎和表達了,在舒適區裏,他是真正的躺平者,出歌只是與信徒的內部交流方式,外人無需湊熱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