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壞規則者,最先得利”
一
一個人的過去,往往潛藏着其未來選擇的蛛絲馬跡。
因此,改變一個人是很難的。
這難,便是由他過往人生的經歷、故事、得失、榮辱、心酸、悲苦和愉逸所共同築就的一座城,任爾東西南北風,它自堅固無比。
王安石拜相後何以判若兩人,以至於知己舊友一個個遠離他,“諸賢盡不從”,乃至與其反目成仇?
這恐怕還要從宋仁宗時代講起。王安石這位後來在神宗朝簡直可以呼風喚雨,乃至左右宋王朝走向的“兩宋第一改革者”,在宋仁宗時代,則可謂是生不逢時,屢屢碰壁。
在很多事情上,我們分明能感受到,王安石和宋仁宗不是一種人,兩個人對政治、權力、治國理政等事務的理解,可以說是鑿枘不合。
講一件嘉佑六年(1061年)的小事:
這一年,宋仁宗決定開設一場制舉考試。宋朝的制舉考試是一種君主下詔特殊安排的考試,這種考試比普通的貢舉考試要難很多,而且考試地點就在皇宮,主考官就是皇帝本人,即”御試“。
這一年的制舉考試,有一個主題: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聽名字也知道,這是皇帝希望籍此選拔敢言有識之士。這一年皇帝出的考題,用一句話概括就是:
如今國家面對種種的問題和困頓,你覺得該怎麼辦?
考試完畢,閱卷的時候,滿朝大臣卻因其中的一張卷子吵翻了天。因爲大臣們發現,有個膽大包天的考生,在答題時把仁宗皇帝、中書宰輔全都狠狠地罵了一通,而且罵的相當“髒”。
面對如此狂悖的考生,大臣們形成了旗幟鮮明的兩派:
一派認爲,這樣的考生目無君上、罪爲大逆,定不能用。
另一派則認爲,這個考生才華出衆,正色敢言,“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
臣僚們對此張考卷爭執不休,事情一直鬧到仁宗皇帝那裏。宋仁宗閱卷之後,說了這樣一句話:
“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
意思就是,分明是我自己向天下士子求真言的,如今真的有考生以直言斥弊政,如果因此貶黜他,那天下人該怎麼看我?

仁宗皇帝最終決定留用這個瘋狂“詆譭”自己的考生,而且給了一個不錯的成績。
北宋的制舉考試,成績分五等,不過一等、二等是個幌子,從來不給任何人,所以實際上考試的前三名分別是:第三等、第四等和第五等。
這位大罵皇帝宰相的考生,獲得了第四等次的成績,他的名字叫蘇轍。那次考試獲得第一名(即實際第三等)的考生,是他的哥哥,蘇軾。
年輕的王安石非常看不慣蘇轍的狂悖,認爲他“專攻人主”,實在是別有用心。那時他的官職是知制誥,按規定,留用考生的任命狀書應該由知制誥來起草,但王安石堅決拒絕給蘇轍這樣的人起草任命書,誓死不從。
此時宋仁宗的寬容再一次顯現出來,面對王安石拒不起草任命書的任性,仁宗也不生氣,只是換了另一位知制誥來起草蘇轍的任命狀。
宋仁宗有“兩宋第一明君”的美譽,與中國歷史上的大多數帝王相比,宋仁宗的確稱得上是一位寬仁大度,胸懷明月的皇帝。
但所謂“寬仁大度”,其實還存在另一種看待視角,就是“軟弱拘儒、徘徊猶豫、瞻前慮後”。
仁宗是許許多多文人士大夫心中的“千古聖君”,但我想,王安石內心未必會這麼看。
比如,面對重大決策常常躊躇不決的仁宗皇帝,王安石就此專門給皇帝上過奏疏,這封奏摺的核心意思,就是說您作爲皇帝不能總一副“深拱淵默”的姿態,放任諫官、御史動不動批評皇帝,彈劾中書重臣;重要事項皇帝得自己拿主意,遇事別動輒集體商議;皇帝應該收回“威福之柄”,不能讓宰相和中書掌握那麼大的權力……
王安石心中帝王,應該是一位乾綱獨斷,殺伐果斷,不怒自威的皇帝。王安石所崇拜和嚮往的權力者,顯然是那種緊握權柄,生殺予奪說一不二的強硬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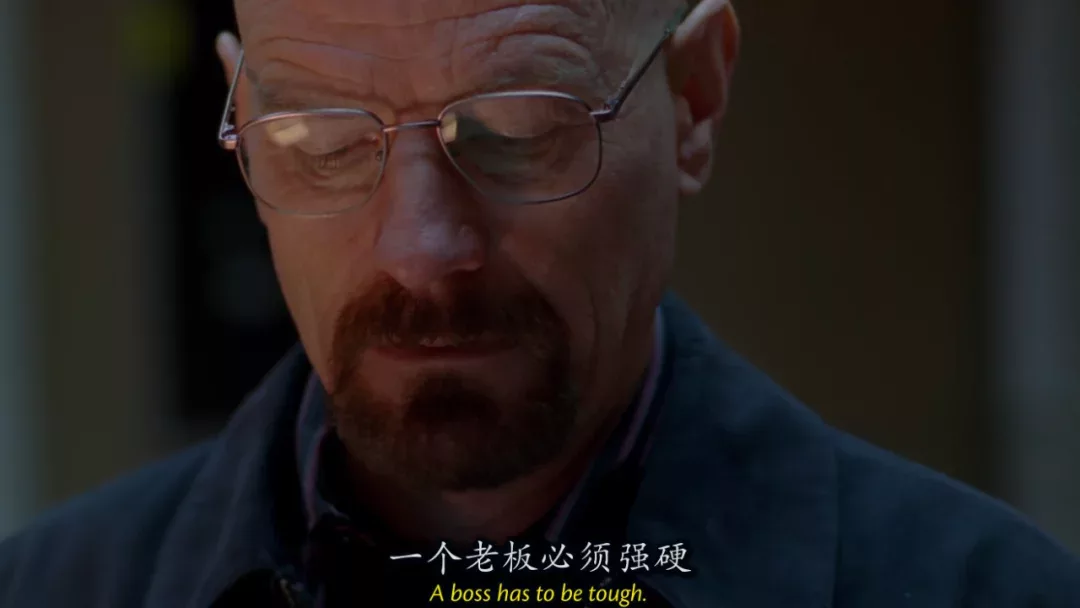
這倒解釋了,爲何王安石在人微言輕時,屢屢上書說朝廷應該廣開言路,用君子棄小人,而拜相之後,大權在握,卻馬上板起面孔,對“變法的反對派”們狠心狠手,冷酷薄情。
因爲經歷過范仲淹“慶曆新政”的王安石,確實曾經親眼目睹了,仁宗朝皇帝與宰輔如何被御史、諫官緊緊捆住手腳,因爲他見證了當年改革者所面臨的上下交困,也因爲他曾經親身經歷了改革舉措被羣而攻之,無可奈何的窘境。
二
王安石進入中書成爲宰相之後,對批評和反對自己變法主張的人,實施了雷厲風行的罷黜。
後來朱熹評價拜相後的王安石,說他“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這期間王安石的所做作爲,可參見我之前寫的另一篇文章《拜相之後,“開明派”王安石何以變成了自己最厭惡的模樣?》)。
王安石之所以能夠明火執仗地“排擯忠直”,核心的倚仗是獲得了宋神宗的信任與支持。
事實上,神宗皇帝對王安石在大宋朝堂上所掀起的“權術風暴”採取了默許乃至鼓勵的態度。
這不僅僅是因爲皇帝對王安石才能的欣賞,也不僅僅是因爲皇帝對新法的斂財效果感到滿意,另一個隱祕的緣由是:
皇帝本身也因此獲得了更大的權力,以及更多的自由。
歷史上真實的皇帝,其實並不像如今爽文短劇中刻畫的那般一言九鼎、唯我獨尊、無拘無束。
實際上,當一個好皇帝並不容易。尤其在北宋,方方面面給皇帝設置的條條框框非常多,遑論軍政改革這類的國家大事,就連很多芝麻大點的小事,皇帝也不得自由,動不動就會被御史諫官上疏規勸嘲諷一番,甚至被諫官貼臉開罵的情況也不在少數。

舉一個很小的例子:
仁宗皇帝在位時,老將王德用在民間遇到兩名絕色美女,他就把這兩個美人進獻給了皇帝。王德用倒不是一位阿諛逢迎的人,衆所周知,仁宗皇帝一直沒有兒子,滿朝文武對這件事都挺憂心的,王將軍進獻美女的初衷,很可能是婉轉地勸慰一下仁宗帝:
這倆美人姿色絕代,要不您再努努力呢?

古代帝王,可以合法地坐擁後宮佳麗三千,按理說這實在不算一件值得討論的事,但當時的諫官王素還是直接找到仁宗,詰問是不是有這件事?
仁宗承認確有此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何?”
堂堂君王,這已經是商量的口吻,但王素不依不饒,開始給皇帝輸出大道理。
仁宗無奈之下,只能把這兩名美人遣出宮,各賞了三百貫錢。爲此,仁宗皇帝還掉了眼淚,這眼淚,固然有對美人離去的惋惜,但恐怕更多是無可奈何的滋味。
宋神宗雖然比仁宗更任性,但綁在他身上的“繩索”,也同樣是千萬條,神宗皇帝就曾對臣子感嘆:
“朕平生未嘗作快意事。”
所以,當王安石將那些直言不諱、納忠效信的諫官御史一個個罷黜之後,神宗皇帝的身心自然也是舒暢的。
有宋一代,所謂的“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聽起來海清河晏,其實非常依仗一個異常脆弱的平衡機制。
這個脆弱的平衡機制,是捆在皇權之上的兩條繩索:
第一條是天道、法祖,即以“天命”和祖宗成法約束皇帝,天命不可違,你祖宗的話,你這個孫子應該聽啊。
第二條是御史臺諫對皇權、相權的監督、諫諍,這些諫官的工作,就是專門糾繩皇帝和宰相的過失妄爲。
對第二條繩索,前文已有闡述,王安石上任之後,迅速完成了對御史臺諫官員的“大清洗、大換血”,新的臺諫官都是攀附、認同王安石變法理唸的人。
很快,御史臺諫從以前可以“風聞言事”,即可以根據沒有證據的傳言進行彈劾和進諫,發展到禁止“越職言事”,即言官不能批評謗議自己職責之外的事情。
如果說仁宗朝是“百花齊放”,到了神宗一朝,朝堂之上便只有王氏“一花獨豔”了,政治風氣的崩壞程度,猶如斷崖。
而王安石,正是打破這一平衡的始作俑者,他破壞了自仁宗以來“寬容政治”的共識。
對於那第一條天命和祖宗成法擰成的繩子,王安石發表了每一箇中學生都熟記的驚天之言:
天命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什麼天道、祖宗、人言,都不必認真對待,統統都是文人士大夫扯的狗屁,哥們兒,你是皇帝啊!做你自己!你是光,你是電,你是唯一的神話,你可以爲所欲爲啊!

對皇帝的慾望、野心和志向,王安石採取了迎合的態度,對繩檢皇權和相權的鎖鏈,王安石以強力將其剪斷,面對這些做法,神宗怎麼可能不歡喜,不快意,不舒服呢?
可以說,放任皇權的任性,打破皇權、相權和文官集團的平衡狀態,是王安石主政時期的大敗筆——其對北宋王朝的影響之惡劣,遠勝於變法的強力施行,以及對民間的戕害。
君王乾綱獨斷之下,必然是御史臺諫萬馬齊喑。
短時間內,確實顯得高效,變法措施推的快,成果出的快,乍一看成績斐然。
但,這一切是以犧牲了王朝內部的糾偏和制衡機製爲代價的。
當皇權與文官集團相互制衡的脆弱狀態被打破,皇權獲得了近乎無限的自由,那寬容的政治氣氛必然已經轉爲偏狹與專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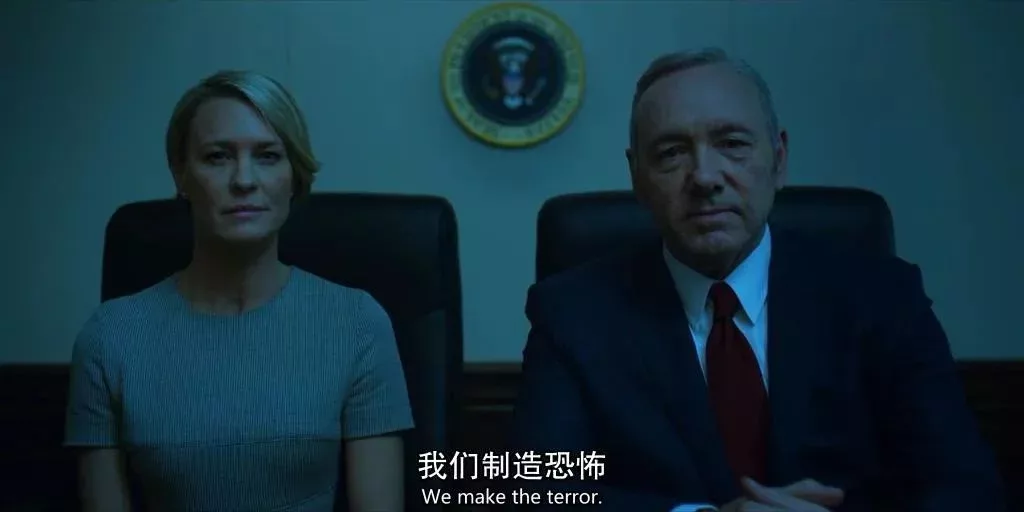
由此,臺諫制度已名存實亡,甚至演變成了黨同伐異的政治工具,劣幣開始驅逐良幣。
順從的、工具性的“新官僚”開始大規模上臺,他們服從、高效,只關心上之所欲,不關心下之所苦,政治風氣頹然大壞。
三
在清除異己的同時,王安石還在大力推進“一道德以同俗”。
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一派所撰寫的《三經新義》,竟取代了儒家經典,成爲了官學教材和科舉考試的標準讀本。
所謂“一道德”,其實就是一切以“王安石之學”爲準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你要麼迎合我,跟着我王安石的路線走,要麼就給我滾蛋。
這場漫長的“統一思想”運動,王安石一直推行到自己下臺的最後一天。
多年之後,蘇軾這樣評價王安石的所作所爲: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
翻譯成普通話就是:
文字、思想、理論的衰弊,從未像今天這般糟糕。而這衰弊的源頭,就是王安石。王安石的文字、哲學、理念,未必不好,但他的禍患在於,喜歡讓別人和自己一樣,容不得其他學派的聲音。
王安石“一道德”之下的學術文化,並不鼓勵多元性和多樣化。

後來蘇軾還形象地比喻:“王氏之學,正如脫槧”。
“脫槧”的意思,就是都是根據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千人一面,千文一腔,毫無個性,毫無思想,只有跟隨與順從。
實際上,這正是宰相王安石在變法之後,所着力追求的政治生態——不要思考,不要疑惑,不要提問,不要否定,不要抗爭,只要執行和結果。
四
談到王安石變法,北大歷史系教授趙冬梅有這樣的觀點:
“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對於宋朝最大的損害不在經濟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專制,士大夫參政空間被極度壓縮,批評糾錯機制失效,腐敗橫行,朝廷國家因而喪失了因應內外打擊的能力。國破家亡的慘劇雖然發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卻在王安石與神宗。”
這一觀點,其實與南宋高宗的看法一致,宋高宗評價王安石變法時曾說:
“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
面對這些指責,王安石或許可以狡辯說,雖然我排斥異己,堵塞言路,以雷霆手段推行新法,但我沒有私心,我的初衷是爲了國家好,我變法的目的是爲了富國強邦。
這話或許不假,王安石變法,也確實沒有爲自己斂財,但是——
目的很重要,可爲了達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和程序,同樣很重要。
古今中外,有許許多多的人間慘劇,究其源頭,往往會發現一個“良善的願景”。

爲了抵達某個想象中良善光明的願景,而放棄了寬容、法治和程序的正義,乃至動作、手段逐漸變形、扭曲,直至失控,那個想象中曾經無比美好的願景,往往會變成現實中最恐怖的噩夢。
所以後來哈耶克寫道:
通往地獄的道路,是由善良的願望鋪就的。
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古今褒貶不一,譭譽參半。
將北宋滅亡,全部歸罪於荊公,顯然不客觀,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但自王安石爲迅速推行變法,與神宗腹心相照地清除異己、打壓御史諫官之後,北宋朝堂一改仁宗時代寬和包容的政治風氣,羣臣之間羅織構陷、黨同伐異此起彼伏,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古往今來,世道的崩壞,往往都有一個相似的現實表徵:
就是正直良善的人因爲形勢所迫,而逐漸閉嘴,“莫談國事”。
大宋世道的頹弊危辱之風氣,就是從“尊崇信奉”安石之學開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