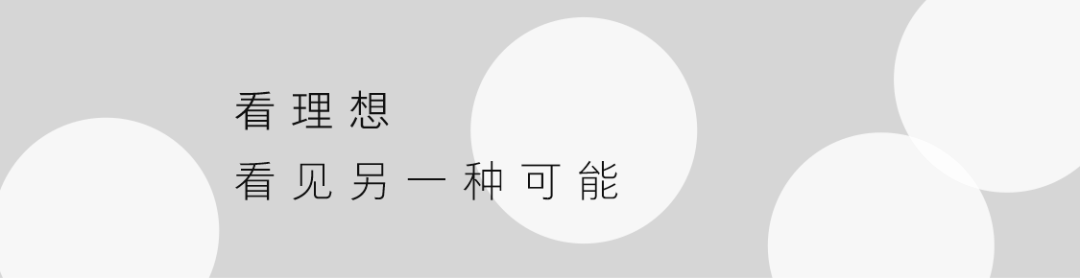
文 | 李厚辰
胡鑫宇事件再次引發社會對青少年自殺問題的關注。先放下許多近乎於陰謀論的爭議,青少年自殺問題早該引發全社會的關心。
根據WHO發佈數據顯示,中國每年有約10萬人死於自殺。根據《經濟學人》等的統計,我們的青少年自殺率在世界範圍內也居於前列。自殺已經成爲15-34歲人羣的主要死因之一。平均每十分鐘就有2人自殺死亡,8人自殺未遂,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
但另一面,該問題在國內卻諱莫如深。這顯然是個不可能知道確切統計數據,很難追責,很難切實追問原因的領域。當然,任何問題走入這個境地,也幾乎就是一個不可能被解決的問題了。
青少年自殺問題很難輕易總結出單一原因,不管是歸因於父母、學校或任何組織。當自殺成爲如此顯著且大規模的社會現象,上述任何一個方面都很難單獨構成。
胡鑫宇的悲劇不過是這場社會失序的巨浪中,被拋出浪尖的一個極端例子。在浪濤之下,是深埋於社會複雜結構中的機理,今天我們很難就這個問題輕易得出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法,不過探入這個問題,卻是重要的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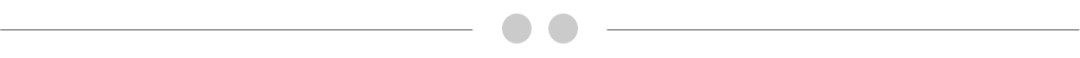
01.
真實社會中的青少年自殺
就在事件之後,北京市社會心理工作聯合會發佈了一封信《胡鑫宇,請給心理指導師五分鐘》,引發全網震動。這封高考作文風格的信,混合着毫無意義的道德高調,直觀的情感綁架,對名作名言的空洞引用,讓網友直呼“看了就想死”。
但這封信卻照應出一種“真相”,我們可以從這封信中一窺社會的“實然”現狀,就是社會上並沒有實質自殺幹預的能力。我們可以簡單將青少年自殺分爲兩個部分,一是引發自殺念頭和行動的成因,二是對青少年自殺的幹預。
我們也該清醒地意識到一種風險,良性的自殺幹預確實會在問題發生後起到挽救作用,但劣質的幹預非但無法起到問題的緩和,還會像上述這封信一樣,可能讓自殺問題加劇。
這是一個簡明的事實,青少年自殺問題,絕不是呼籲“多重視”、“多幹預”就可以緩解的。“亂重視”和“亂幹預”不僅不會緩和問題,反而會付出更慘痛的代價。
這就是所謂“真實社會”視角的一個簡要方面,我們的一切認識和分析,呼籲和主張,不能建立在幻想中的全能社會上,而要意識到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真實殘破的社會:部分心理工作者意識和能力的低下,父母對處理情緒問題缺乏足夠支撐,也缺乏精力和耐心,學校風聲鶴唳不願擔責,還有無數問題。
舉幾個最簡單的例子,提到青少年自殺問題,我們總是埋怨父母對孩子不夠理解包容、不夠耐心支持,但現在面對中考分流和高考的壓力,縣中模式席捲全國,而爲了提高升學成績,縣中模式大多采取寄宿制,這天然地隔絕了父母對子女支持的可能,在這樣的學校管理模式下,何談父母對子女的照顧?

《鼕鼕的假期》
再說到很多人建議學校加強心理健康老師對學生的支持,且不說全國到底有多少人有足夠的能力擔此重任,或各個學校有多少資源資金可以投入到心理健康老師中。
就單說這個職位本身,既然設置這個職位,真正介入學生心理健康,就肯定要爲結果負責,當學校和社會正批量化地製造千瘡百孔的學生,所有壓力都被壓到這個心理健康老師的身上,而他可能會爲發生的極端事件負責,承受家長問責,遭受社會輿論的抨擊,這個燙手的職位,又有幾個人敢去擔任呢?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結構”問題的真實性,青少年自殺問題,背後的成因是社會整體的,是與制度、文化、技術、管理高度整合的。面對如此巨大的重擔,任何單獨的家長、心理健康老師、社會機構,其本身精力、資源、知識、技術、意志力都是有限的,我們這個社會如何有限,這些社會主體就會同樣面對此種限度,都不可能單獨面對和解決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真實情況,即社會根本不具備足夠幹預青少年自殺問題的能力,呼籲“重視”和“介入”,既可能不會引發真正的行動,還可能帶來更多衍生問題。僅僅對“應該如何”的呼籲,不足以真正緩解青少年自殺問題的困境,我們需要進入這個問題的深處。
02.
再溯塗爾幹《自殺論》
現在回到上面兩個問題的第一個,即“引發自殺念頭的行動和成因”,這種歸因討論網上有很多,歸咎原生家庭和父母的是一大類,歸咎於學校和教育升學體制的也不少。同樣,有人歸咎於西方思想和意識形態,認爲“西化”是這些問題背後的原因,有人歸咎於手機、短視頻和遊戲。
面對生死問題,我們只需要很短的演繹,就可以把日常的偏見都裝進去。這種琳琅滿目的分析,恐怕無法讓我們真正認識這個問題。當然可能最有效的途徑是回到塗爾幹和他的不朽名著《自殺論》,相信我們可以從中找到這個問題的關隘。
這決不僅僅關涉“自殺”,背後站着的是我們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因爲幸運,還未被逼到邊界,但已然感受到疼痛的個體。
A.個體與社會
自殺,作爲個體對自己存在的終極否定手段。理解它既需要一定的理論框架,也需要歷史情境。古典時代的自殺,與現代自殺,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現象。
《史記》與《左傳》中有數量龐大,又具有代表性的自殺敘事,但那其中人物自殺的動機,都令今人費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記・魏公子列傳》中信陵君的門客侯贏。他在信陵君竊符救趙的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竊符救趙的計策爲他所策劃。但他在信陵君出發踐行此計後,直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他自殺的原因,甚至成爲一個需要解釋的歷史“公案”。

《夜以繼日》
不必牽涉太遠,我們繼續着眼在現代自殺的特殊性。其實就在我就讀初高中的時候,同樣面對很高的升學壓力,學校嚴格的規訓。但在那個時候,其實關注心理感受,進而考慮到終結生命的,比現在少很多。
差別絕對不在那個年代的人比較堅強,而今天的人比較脆弱,很多人會將這個問題解釋爲“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這當然是傲慢而錯誤的。
這其中折射出的“現代”問題,是個體意識的萌發,在塗爾幹的作品中,他所舉的例子是新教信徒自殺比例高於天主教徒。箇中道理並不複雜,越是現代個體,對其自主性、個體性的要求就越高,也越是敏感和關注自己的感受。因而在完全服從於某種外部規範的背景下,帶來的壓力與問題也就越多。
我們個體性的逐漸覺醒,重合商業經濟加速發展的過程,也就是最近20年的事。這一代學生,比起我上初高中的時候,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自我敏感和對主體性的期待和要求,實屬正常。
這是社會的自然進步,不是退步,更不可能走回頭路。我們不能說,“現在的學生服從性太差,對自我感受太敏感,不夠堅強”。因爲在現代社會,該問題的另一面就是類似自驅力的增強,對自我成就的要求增高,背後帶來的主動性和創造力,也不是過去社會可比的,這是社會真正發展的核心動能。
這不是問題的完整解釋,而僅僅是解釋的開始,在塗爾幹的論述中,這種“個人主義”的現代個體,就面對着他生活與生命的根本張力:個體與社會。
最簡單地說明塗爾幹的意思,是說現代“個人主義”的個體,需要以個體認可的方式參與和整合在社會之中。首先人不能爲自己而活,只能活在具有整合性價值和規制的社會之中;但現代個體又不能完全放棄自我,進入被逼迫的境地,這同樣導致自殺。
塗爾幹就是在個體與社會的這組張力中,來論述自殺問題的。
B.個體與社會語境下的三種自殺
在這個語境下,他將自殺分爲三種。
第一種是個體意識過強的自殺,在個人主義極端興盛的社會中,一切社會整合都被壓抑,集體目標、集體行動、集體價值不再被接受。但處於巨大社會中的個體,其實根本無法在其中尋找到個體行動的目標和價值,這個問題大概在今天被人們稱爲“存在性焦慮”,會導致人的虛無和脆弱。
第二種是社會整合過度的自殺。在與上面的情況完全相反的社會中,個體需要無個性的,甚至是掩蓋和壓抑個性地融入社會,個體生活在這種社會完全視爲無用。爲集體獻出生命被歌頌,個體漠視自己的生命,也漠視他人的生命。同樣會導致人的脆弱。
第三種既非個體過盛,也非社會過盛,而涉及到社會規制過程。將個體的計劃和欲求,整合進社會的過程中,既有價值觀的共通,目標的共有,也存在具體實在的社會規範。不管是從事商業的,或是任何社會分工與職能的,都在一定的社會制度、法律、組織的結構中進行。

《奧斯陸,8月31日》
但如果社會高速且無序地變化,個體容易無所適從,無法充分理解和預期社會規制對他造成的影響,就形成塗爾幹典型的“社會失範”觀點,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會導致脆弱。
在這種脆弱而喪失支持的情況下,即便是一個很小的挫折,也是足夠導致自殺行爲發生的。
因此在個體與社會張力的這一組極具現代性的語境下,以個體如何適應社會整合和社會規製爲視角,我們將自殺分爲這三類。
第一類比較典型地體現了北歐社會的情況,第二類讓我想起庫布里克電影《全金屬外殼》中沒有撐過新兵訓練營的派爾(Pyle),而第三種則出現在典型的社會動盪劇變,經濟危機發生之後,社會範式轉變之時。
那麼衚衕學以及他代表的學生羣體,符合其中哪種,或哪幾種的綜合,我想結論是一目瞭然的。
03.
塗爾幹視野的重要性
爲何要以塗爾幹的方式理解自殺,而不是我們尋常所言之“個體感受”的方式?尋常來講,我們對自殺的理解是“痛苦/刺激-反應”模式,人因爲痛苦而自殺,人受到刺激而自殺。
這條路徑走到極端,便會追求對人“刺激”的減少,甚至到對“自殺”對“死”避而不談的地步,彷彿只要少談論,少觸碰,就會少自殺。並認爲對自殺事件的關注和討論會導致模仿自殺的現象。
這種“痛苦/刺激 – 反應”的模式在實證上已經被從多方面證僞,比如自殺模仿這樣一種“合乎直覺”的現象,在2015年就有一篇名爲《Bringing Anomie Back In: Exceptional Events and Excess Suicide》的論文予以駁斥。

《陽光普照》
一種思路和視角,對應着問題的解決方法,當我們把自殺理解爲“痛苦/刺激-反應”的模式,能做的自然是脫離痛苦,或對痛苦給予安慰。從羣體角度來看,我們可以進行“風險排查”,找到處於“痛苦”狀態的人,給予安慰和紓解,這都合乎直覺,但合乎直覺的東西不一定正確,不一定有用。
在“真實”社會中,我們可以想象一次在學校中的“風險排查”,例如使用量表的方式找到了有抑鬱症“風險”的學生,一般會如何處理呢?我想多半會是讓他直接休學,學校擺脫風險爲主吧。從上述模式裏,這個學生就離開了高壓學業的直接“刺激”,豈不就進入到了安全的狀態?
但從塗爾幹的“個體與社會”語境中,學齡段的少年被排除出學校體系,如果家長沒有足夠的資源和精力對其進行照顧,這是否會導致他社會化的水平更低,在中期埋藏下更多風險呢?
這就是“痛苦/刺激-反應”模式在理解自殺問題上的缺陷,其解法合乎直覺的是“脫離刺激”,安慰痛苦。但一個人真的可以脫離社會建制嗎?他在什麼條件下,纔可能得到合適的安慰呢?請注意,這兩件事,都是有機運和成本的,甚至需要不低的機運和成本,才能完成脫離,得到安慰。
不僅如此,“痛苦/刺激-反應”模式總是讓我們想問,爲什麼其他人在面臨同樣壓力和痛苦下就沒有這樣脆弱的傾向呢?因而很多時候老師、學校、家長會在學生遭遇困境時,反過來責備這個學生抗壓力差,過於敏感。面臨這樣的差異,彷彿除了“先天要素”,無法找到其他解釋。
環境、制度的問題被“先天痛苦承受能力”壓抑,那家長和老師是否可以認爲自己“運氣差”,遭遇到了一位先天更脆弱的學生?這個視角我想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在這裏,我們可以面對這個嚴肅的問題了。自然介入真的有用嗎?這就像當一個人已經罹患絕症,其實治癒的機會不高。當一個人已經產生決絕的自殺傾向進而產生行爲時,我們能做的到底有多少?休學就可以好?喫藥就可以好?介入和監控他的人際和社交媒體使用就能好,而不是因爲這樣的過度介入導致其更嚴重的自殺意願?
說到底,到這個處境下,大多數家長除了將學生帶到精神科醫生那裏去獲得一堆藥物外,還有什麼是社會中廣泛可行的手段。當自殺的決定已經產生時,介入已經太晚,真正值得努力的方向,是減少念頭和行動的發生。
回到我們最開始分析的兩個問題:一是引發自殺念頭和行動的成因,二是對青少年自殺的幹預。對於社會中每個人而言,我們總認爲只能做後者,前者代表的是系統性的,社會性的結構和制度,這超出了我們的能力範圍,無法改變。因而唯一有意義就是找到並發現自殺傾向,並及時幹預。
但這種想法是不是就是問題所在?當我們都無法直面,無法討論真正問題時,這本身是不是就是自殺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即,一切問題的解決都被我們漠視、放棄和避開,因而社會中的個體被逼迫到否定自己存在的地步。
個體被逼到這一步,之前的所有問題都無法解決,無法回應,到這裏又有什麼可介入的呢?

《陽光普照》
當我們將孩子送進一間以嚴密KPI驅動的巨大縣中,在密集的課程和考試中,在末位淘汰和每月一次分班的逼迫下,孩子與父母區隔,以電話做聊勝於無的聯繫。在這個背景下,家長又能如何監控和發現風險?
反過來說,過度擔憂,笨拙地對普通的不快樂進行介入,甚至用藥,是否在發明更多新的,更嚴重的問題。我們如何培養能夠匹配當前社會規模的合格的精神科醫生和家長呢?
還是問題根本就出在縣中體制和中考分流。落實12年制義務教育,限制縣中模式的發展,多樣化辦學體系,打破對升學和學歷授予體系的壟斷,會不會纔是解決青少年自殺問題的方法?
尾聲.
因此這篇文章呼喚換個視角看問題,不要讓社會問題被心理問題掩蓋。我們其實很容易發現一個共通的問題背景,導致上述教育體系改革無法落實和推動的原因,與文章最初的那篇高考作文一樣心理疏導文章的出現,以及其背後機構的運營,是否有類似的原因?讓各學校可以開展“風險排查”,並粗暴進行休學停學,將責任完全壓給家庭的原因,又是否類似?
如果真有,那這個原因當然就是青少年自殺問題的社會歸因,和其可以得到緩解的真正方向了。如果對這個問題,你的答案是,我們做不了,我們無法改變,那麼很遺憾,青少年高自殺率便成爲這個社會的一種命運。
而家長的介入,精神科的藥物,甚至是社會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重視這種虛幻的文化進步,都不過是紙面上的“方法”,或者只是少數家庭可以承擔和負擔的幸運。
我們更有可能獲得的,要麼是漠視和問題的延續,所有人繼續諱莫如深;要麼是一場大張旗鼓的“精神衛生”排查,後者顯然更令人恐懼。
青少年自殺不是一種“病理學”的問題,而是一種“時代病”,是一個“教育問題”,而非一個“生理問題”。我想當我們都敢於討論,敢於直面這個問題的時候,真正的緩解纔開始進行。

*本文原名《一個嚴肅的問題——自殺》,聲明: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臺立場,歡迎提供不同意見的討論。編輯:蘇小七,監製:貓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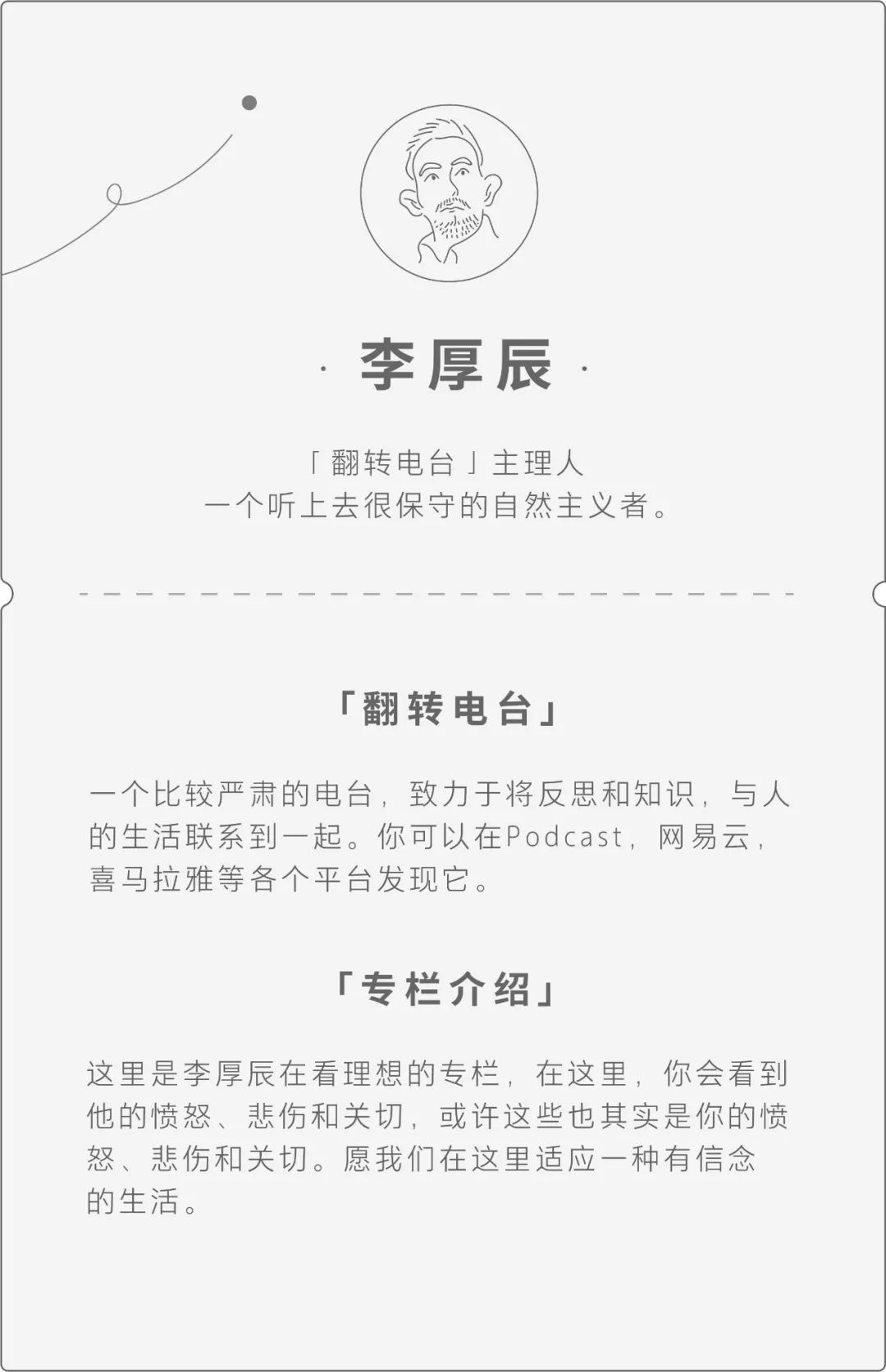
更多「李想主義」專欄文章
▼
慢慢地,我們學會了那些曾經不敢的事
查看更多往期內容
請在公衆號後臺回覆「李想主義」
轉載:請微信後臺回覆“轉載”
商業合作或投稿:xingyj@vistopia.com
📍發表於:中國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