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曰:“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一書中指出:“戰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簡單的準則是集中兵力。除了爲實現迫切的任務必須把兵力調開以外,任何部隊都不應該脫離主力。我們要嚴格遵守這一準則,把它看作一種可靠的行動指南。”可見,戰略的第一準則是集中,而要集中就要做取捨。
沒有捨棄就沒有戰略
“要取得相對的優勢,也就是在決定性地點上巧妙地集中優勢兵力,就往往必須準確地選定決定性地點並使自己的軍隊一開始就有正確的方向,就必須有決心爲了主要的東西(即爲了大量集中自己的兵力)不惜犧牲次要的東西。腓特烈大帝和拿破崙在這方面做得十分突出。”戰略是目標與能力之間的平衡。這種平衡可能是縮小目標,即在目標上做取捨;也可能是調整資源配置使之集中於主要目標,也就是在資源分配上做取捨。所以,沒有捨棄就沒有戰略。
華爲公司總裁任正非這位軍人出身的企業家深諳這個道理,他在多個場合反覆強調過:“戰略,戰略,只有略了,纔會有戰略集中度,纔會聚焦,纔會有競爭力。我們可選擇的機會確實很多,但只有有所不爲,纔能有所爲,我們有所爲的標準只有一條,就是不斷地提升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又如,“我們要學會戰略上舍棄,只有略纔會戰勝。當我們發起攻擊的時候,我們發覺這個地方很難攻,久攻不下,可以把隊伍調整到能攻得下的地方去,我只需要佔領世界的一部分,不要佔領全世界。膠着在那兒,可能錯失了一些未來可以擁有的戰略機會。以大地區來協調確定合理捨棄。未來3~5年,可能就是分配這個世界的最佳時機,現在我們就強調一定要聚焦,要搶佔大數據的戰略制高點,佔住這個制高點,別人將來想攻下來就難了,我們也就有明天”。
還有,“什麼叫戰略?‘略’是什麼意思?‘略’是指捨棄一部分東西。你不捨棄一部分東西,不叫略;沒有方向,不叫戰。對於形勢不好的市場,要敢於拋棄一部分,聚焦一部分,聚焦後有利潤賺就行了”。
華爲公司爲了成爲世界一流的通信網絡設備供應商,堅決放棄了信息服務業的機會。爲了集中力量開發GSM(全球移動通信系統,爲第二代移動通信技術標準)設備,放棄了TD-SCDMA(時分同步碼分多址接入,是由中國第一次提出的一種無線通信的技術標準);爲了向世界領先企業愛立信看齊,毅然拋棄了落後的PHS(個人手持式電話系統,俗稱“小靈通”)制式。
多年後,任正非在說到這個戰略放棄過程時還心有餘悸:“當年爲了一個小靈通,一個TD,差點把我的命都給搞掉了,爲什麼?八年啊,看到人家小靈通轟轟烈烈,大家寫報告,說三個月就能做出來,做不做?還有TD,到底上不上?你說那八年,我咋過來的?領導好難做啊!不做,錯瞭如何辦;做了,在非戰略機會點上,消耗了戰略競爭力量,會有今天嗎?現在輪到你們來領導世界了,你纔會感到是把你放在爐子上烤。”
進入一個新市場、開展一項新業務很容易,但要退出一個市場、放棄一項業務有多難啊!且不說資產處置、人員轉移安置的費用和損失,已經銷售產品的後續服務、配件供應,還做不做?如果不做,損失的客戶關係和聲譽,企業是否承受得起?所以,還是要在開始時就想清楚、下決心,有所爲,有所不爲。只有有所不爲,纔能有所爲。
機會牽引與資源驅動
伊迪絲·彭羅斯(Edith Penrose)在她的《企業成長理論》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一個富有啓發性的問題:“我試圖回答的問題是企業的性質中是否存在某些內在的東西,它既能激發企業的成長,同時又必定限制企業成長的速度。”
顯然,企業的成長首先在於對機會的捕捉,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成長是一個創業過程,是一種充滿企業家精神的活動。什麼是企業家精神呢?
筆者非常欣賞霍華德·H.史蒂文森的定義:“企業家精神是一種管理方式,即追求機會而不顧手中資源。”那麼,企業家靠什麼抓住和開發機會呢?靠資源,或者更一般地說,靠管理能力。管理能力回答了爲什麼同樣的機會,許多企業都發現了,但只有個別企業真正抓住了,藉此發展起來了的問題。
彭羅斯將企業定義爲基於管理框架下的資源集合體(a collection ofresources)。針對爲什麼企業的成長存在着一個限度這個問題,她認爲存在三種解釋:管理能力、產品或要素市場、不確定性和風險。她重點討論了管理能力。
她說:“隨着時間的推移,從企業的運營中獲得的經驗導致了知識的增加,這一過程也產生了許多生產性服務,但如果企業無法擴張,就無法利用這些服務。這些服務就爲擴張提供了一個內部誘因,同時也爲擴張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顯然,企業現存的人力資源既刺激了擴張也限制了擴張的速度。
而在企業的管理能力中,“有經驗的‘內生管理者’的可獲得性便成爲企業在任何時期計劃並實施擴張的制約因素。按定義,這類管理者原本是不可能從市場上獲得的,但一定是企業擴張的一個必要投入”。
實踐表明,相比資本和技術等其他資源,有經驗的內生管理者是最難獲得的。從外部人才市場引入的管理者,往往會因爲文化和價值觀的差異,很難融入企業的創業團隊,而要讓下屬認可和接受需要較長時間的磨合。
所以,對於企業成長最重要的是從內部選拔和培養勝任新業務挑戰的管理者,這是成長的最大促進因素也是最大的制約因素。如果企業的成長速度快於必要經驗和勝任的內部管理者的獲得速度,則企業的成長就會受到影響,企業會爲此付出成長的代價。欲速則不達。
華爲公司在信息與通信技術的國內與國際市場上持續快速成長了30多年,就是因爲企業家始終具有識別機會的前瞻性和敏銳性,且重視管理能力和幹部隊伍建設,較好地處理了機會牽引與資源驅動這對矛盾。我們這裏不妨摘幾段任正非的講話,說明他對這對矛盾的看法。任正非指出:
人類社會正處在一個轉折時期,未來二三十年內將變成智能社會,智能社會就是信息大爆炸的社會。這個時期充滿了巨大的機會,沒有方向、沒有實力的奮鬥是不能產生價值的。沒有正確的假設,就沒有正確的方向;沒有正確的方向,就沒有正確的思想;沒有正確的思想,就沒有正確的理論;沒有正確的理論,就不會有正確的戰略。
眼前最重要的不是成本高低問題,而是能否抓住戰略機會的問題。抓住了戰略機會,花多少錢都是勝利;抓不住戰略機會,不花錢也是死亡。節約是節約不出華爲公司的。
華爲大學能不能把“將軍的搖籃”這句口號公開喊出來?當然,這將給教學極大壓力,給學生極大壓力。我們執行830計劃,最大的困難是缺少帶兵的人,缺少優秀的擁有成功實踐經驗的幹部。
這些人在學習與實踐中,會逐步成長爲各級管理骨幹,我們稱之爲“將軍”。華爲大學在這個歷史時期應負有很大的使命。要研究一下,黃埔軍校、抗日軍政大學、西點軍校爲什麼出了這麼多將軍。爲什麼我們擔負不起這個歷史使命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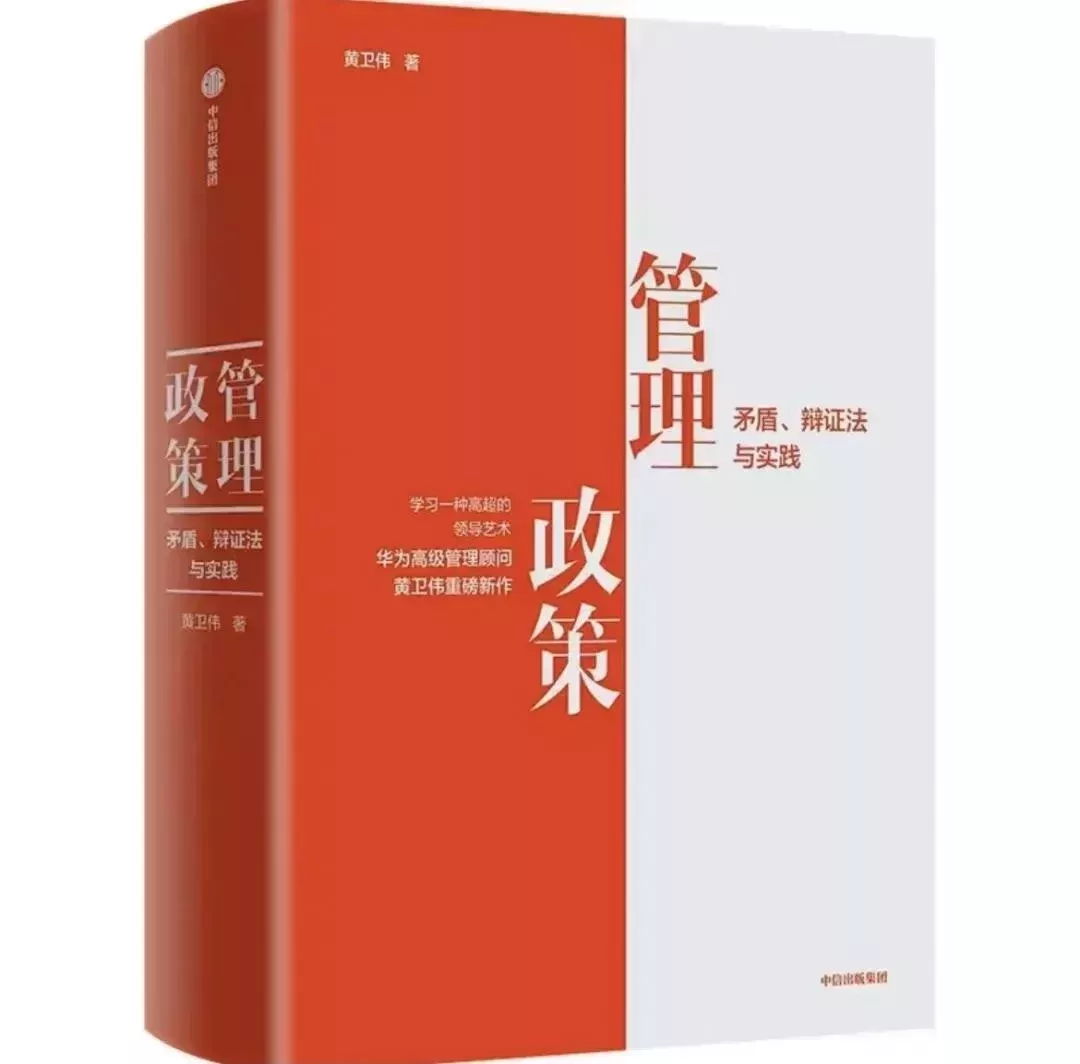
彌補制約整體競爭力的能力短板
企業經理人和各級管理者需要一套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方法,而約束理論(constrain theory)不失爲一個很好的方法。它是《目標》一書的作者埃利亞胡·M.高德拉特(Eliyahu M. Goldratt)發展出的一種方法,應用效果非常顯著。
這種方法是從端到端的角度看業務流程和整個系統的能力短板,該短板被稱爲“瓶頸”,即能力等於或小於需求的任何環節,然後發展出一套識別瓶頸、發揮瓶頸最大產能和消除瓶頸的方法。約束理論類似於經濟學的“木桶原理”,即木桶能盛多少水,取決於最短的那塊木板。
高德拉特運用工廠運營中的大量實踐生動地闡述了約束理論的核心觀點:
系統的產能等於瓶頸環節的產能,在瓶頸環節上損失一個小時的產能,就意味着整個系統損失了一個小時的產出。在瓶頸環節損失的產能是不能靠增加非瓶頸環節的產能來補充的。
瓶頸環節的每小時成本是系統的總支出除以瓶頸環節的生產小時數,而不是瓶頸環節的支出除以瓶頸環節的生產小時數。這樣的成本視角有助於提高管理者對瓶頸環節產能利用率的重視。然而瓶頸概念並非旨在降低運營成本,而是聚焦於提高產出。
如何提高瓶頸環節的利用率呢?首先,確保不浪費瓶頸時間,也就是不要使瓶頸環節閒置,以及不要用瓶頸環節加工有缺陷的零件。其次,是使其不要加工當前市場不需要的零件,這樣只會生產庫存,佔用現金,是犧牲現在的錢換取未來的錢。
絕不能尋求最大化系統中的每個資源。局部最優系統絕不是整體最優系統,而是一個效率很低的系統。
存在瓶頸和非瓶頸的事實並不是因爲我們對系統的設計很差。它是必然存在的。如果上游資源沒有剩餘能力,那麼我們將無法最大程度地利用瓶頸資源,因此,瓶頸環節的閒置將不可避免。
我們不是在處理技術,而是在思考過程。①我們要改變什麼?②要改成什麼樣?③如何改變?如果管理者不知道如何回答這三個問題,他或她有資格被稱爲管理者嗎?
改善瓶頸的管理,提高瓶頸的利用率,必須明確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目標不明確,就無法搞清什麼在約束着目標的實現。高德拉特在《目標》一書中指出,人們通常把一些看似重要但並非根本的度量當作目標,比如把質量當作目標,但如果質量是真正的目標,那麼像勞斯萊斯這樣的公司爲什麼曾一度瀕臨破產?又如把技術當作目標,但爲什麼在我們見過的每個組織結構圖中,研發部門總是處於與其他業務部門並列的位置上?可見技術很重要,但不是最終目標。再如把市場份額當作目標,一家企業可以佔有很大的市場份額,但如果不賺錢,誰在乎它呢?
高德拉特的結論是:企業的目標是賺錢。所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必須落實到企業的賺錢目標上,不賺錢的競爭力不是真正的競爭力。賺錢的標準是有利潤的收入,有現金流的利潤,長期的可持續的現金流是企業價值的本質。
約束理論實際上提出了一種取捨的標準,即無論是爲賺錢目標直接做貢獻的部門,還是爲賺錢提供服務和支持的部門,只要在分工和協作的體系下,該部門的能力低於加在該部門的工作負荷,這樣的部門就可能成爲整個系統的瓶頸,就會約束企業的產出。
因此,要增加系統的產出,也就是增加系統創造的利潤和淨現金流,就必須增加該部門的能力。這與我們的經驗是一致的。如果認爲要增加系統的產出就要增加直接對產出做貢獻的部門的能力,加大對該部門的激勵,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銷售訂單是增加了,但交付週期可能更長了,或是製造的質量開始下降,或是逾期應收賬款上升,或新產品上市時間延長,等等,最終銷售增長的勢頭開始放緩甚至下降。
所以,高德拉特指出,我們必須改變對產能的思考方式:我們不能孤立地衡量資源的能力,其真正的生產能力取決於它在系統中的位置,我們不應該只看每個局部區域並嘗試對其進行修剪;我們應該嘗試優化整個系統;重要的是平滑業務流而不是能力,是思考過程而不是處理技術。這些結論富有啓發性。
雖然高德拉特用的是工廠管理的實踐論證約束理論,但約束理論的應用領域絕不限於工廠管理,約束理論同樣適用於核心能力戰略框架。約束理論給出了戰略取捨的原則:根據目標和約束條件的鬆緊進行取捨或確定優先級。由於核心能力是約束企業競爭力的最緊的要素,所以它經常是企業競爭力的瓶頸。
錯開相位發展
戰略受到資源的約束,這意味着戰略的實施要有節奏,張弛有度,梯次推進。
構建核心能力是爲了實現成爲全球行業領導者的目標。核心能力的構建是競爭對手密切關注的動向,競爭對手隨時可能進行相應的操作。那麼,什麼時候是核心能力發展的最佳時期呢?用華爲公司總裁任正非的話來說,就是“彎道超車”,“錯開相位發展”。任正非指出:
錯開相位發展,加大對機會的投入。研發與市場要相差兩年左右的時間,現在如果不加大投入,等到春天來了我們種什麼?不加大投入怎麼能產生機會?研發體系要和市場體系錯開相位發展,在市場下滑時,要加大研發投入,纔有可能在市場重新恢復到正常狀態的時候有所發展。爲了迎接這種到來,我們在研發體系投入問題上是不能動搖的。
最近,我們確定了要“在彎道里超車”。我們要在世界競爭格局處於拐點的時候敢於超車。大家看F1比賽,賽車在直線跑道從來沒有超車的,因爲超不了。在直線上大家都是拼命加速,你怎麼超得了呢?西方同行有幾十年的管理積累、品牌積累、客戶的信任積累。在發展形勢一片大好時,他們一加速就跑得遠遠的,我們超不了。
而在彎道的時候,一個判斷失誤,可能它就掉到後面去了。因爲彎道多迷惑、多猶豫。我們只要把握了我們的優勢,敢於在彎道上加大投入,就有可能在某方面超越它們。
發展是一個趨向平衡和打破平衡的過程,弗蘭克·H·奈特認爲:“滾滾紅塵的每—種運動,都是也可以被視爲趨向平衡的發展。水流趨向於同水平面,氣流趨向於同氣壓,電流趨向於同電壓,輻射趨向於同溫度。每一種變化是對導致該項變化的力量的平衡,該項變化趨向於帶來這樣的條件,在此條件下該變化不再發生。”在經濟系統中,這種趨向平衡的過程就是產業的週期性調整。嚴重的是經濟危機,其次是經濟蕭條,一般的是需求飽和迫使供給端進行調整。
在產業的低谷時期,那些在產業繁榮時期盲目擴張的企業往往會陷入困境,現金流出現枯竭。而對於具有遠大目標的企業,這恰恰是後來居上的時機。有的是通過併購增強自身的實力和市場地位,而像華爲這樣的企業,則是通過錯開相位發展的戰略加速核心能力的構建。
錯開相位發展要承受企業效益暫時下降的壓力,尤其是在產業低谷時期,這種壓力更大,所以,錯開相位發展是在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之間的一種取捨。這是要考驗企業家的勇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