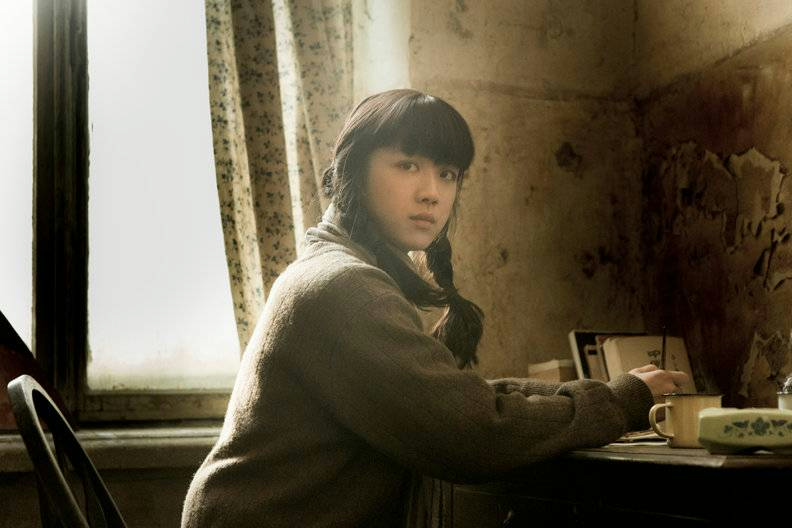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在外界翻天覆地的戰爭炮火中,經歷了一年的戰爭、疾病和貧窮交替折磨的蕭紅,給世界留下了最後一句話,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卻是因爲我是一個女人。”
隨即病逝在了香港瑪麗醫院,結束了自己短暫如流星般的作家人生。
與此同時,正在香港大學求學的張愛玲,在戰火中第一次歷經了生死考驗,領悟到了,
“想做什麼,立刻去做,也許一遲就來不及了。”
遂放棄了繼續追逐去英國進修的機會,回到上海,發表了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並藉此正式進入中國文壇視野之中。
魯迅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蕭紅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看來她有可能接替丁玲女士,正如丁玲接替了冰心女士。”
而就在家國破碎,山河動盪之時,蕭紅和張愛玲又命運般地,完成了這“中國女性文學”接力棒的交接,繼續努力探尋“中國女作家之路,究竟該何去何從”。
她們二人是極其相同的,童年時期都遭受了家庭的冷遇,經歷着母親的厭惡以及繼母和父親的雙重摺磨。成年後,逃脫原生家庭的她們,都靠着文學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但也都難逃被自己深愛的男人欺騙、拋棄的命運。
而她們二人又是截然不同的,蕭紅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所以她一開始創作,就把筆伸向了自己無比熟悉的,那些固守家園的農民和他們沉寂愚昧的生活,紮根鄉土,闡述着長期處於卑賤和無助狀態的女性。
“如何糊糊塗塗地生殖、亂七八糟地死亡。”
而張愛玲則是生長在滬港洋場,小說中,各色的遺老遺少、太太小姐,都在她身邊着真實的原型。這些女性個頂個的聰明厲害,都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不得不依附男人的困境,卻甘願把自己的精神和肉體待價而沽。利用男人對她們這種需求,千方百計地爲自己謀取好處。
究竟是更該尋求社會大環境的變革,努力改造國民性,消除讓男女不平等的制度,還是更該強調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努力尋求人格和經濟的真正獨立,她們二人所代表的,正是女性文學中關於“女性解放問題”兩種不同的路徑選擇。
01.逃離
“對於悲劇來說,引起我們快感的不是災難,而是反抗。”
蕭紅的一生,就是逃離父權的一生。
蕭紅於1911年,出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她的父親張廷舉,因投身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第一個帶頭砸爛了祖師爺的塑像,倡導新式教育,成了當地教育界的首腦人物。

可諷刺的是,雖然他在外提倡創辦女學,呼籲別人家都把女孩子送出來上學,但是他自己卻早早的阻斷了蕭紅的上學之路,與權貴之家達成了婚約。爲了繼續中學學業,蕭紅曾兩度離家出走去往北平求學,也因此被家人囚禁在老宅之中長達半年之久。
爲了逃離牢籠,蕭紅曾將自己的身心,都交給了未婚夫汪恩甲。結果等待她的就是欺騙、玩弄和拋棄,懷孕後被抵押在旅館做人質,還差點被賣到了窯子之中。
而後,她又將全部身心交予蕭軍,以期能獲得幸福。只可惜,蕭軍能將她從絕境中救出,能引她走上文學創作之路,卻不能給予她期望的安定美滿的婚姻生活。
共同生活的六年裏,蕭軍頻繁發生外遇,這邊暗戀着一個叫李瑪麗的文學沙龍主人,那邊追求着一個南方姑娘陳涓,對待蕭紅也是動輒家暴。
“往日的愛人,爲我遮蔽暴風雨,如今他變成暴風雨,我幼時有個暴虐的父親,他和我的父親一樣了。”
凡此種種,致使蕭紅心灰意冷,多次與蕭軍分手,可往往最終,又因生活的困難不得不再次低頭,直到後來與端木結合,纔算是徹底擺脫。

作爲一個追求愛情婚姻獨立自主的父權反叛者,蕭紅一生都在左衝右突、追求、逃離、掙扎,可又一次次被迫陷入男權中心的桎梏之中。
所以她的目光總是注視底層,注視着那些連基本的生存權都無法得到保障的女性。例如,她的代表作《生死場》中,農村女人像豬狗一樣的生產和死亡,“橫在血光中,用肉體來浸着血”,這種感受正是來源於自己兩次非常慘痛生產經歷。
在她看來,底層女性就如《生死場》中的金枝一樣,處於性角色的被動化和生育的動物化,人的生命活動和動物的自然繁殖一樣盲目而又氾濫。而女人比動物更不如的是,除了必須忍受生育之痛,還要承受丈夫的嫌惡和責難。
例如即使是在生孩子的緊要關頭,王姑姑的姐姐也要強忍疼痛,不敢大聲呻吟,她在土炕灰塵中哀嚎,丈夫卻用長煙袋砸她,用大盆涼水潑向血泊中即將死去的妻子。
當母親退化成了一個無自我意識的傳宗接代的工具,個體種種慾望、價值、情感也就逐步麻木和泯滅了,連同母愛也喪失了。
“生了就任其自然長大,長大就長大,長不大也就算了。”
“農家無論是一顆菜,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過人的價值。”
蕭紅在小說中重點突出了這種價值倒錯,《呼蘭河傳》中胡家大媳婦對自己家養的雞呵護備至,對踩死小雞的兒子卻痛下毒手,打了三天三夜,直到打出一場病才罷休。蕭紅越是宣揚人對動物,對財物的珍視,越體現他們對於人的價值的漠視。
“在鄉村,人和動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而張愛玲更進了一步,如果說蕭紅的悲劇在於,在五四文化的浪潮啓蒙下女性,還未有能支撐她們獨立生存的活路,那張愛玲的悲劇則是源自,過早的看到了新文明的陰暗面,對於人性,對於未來出路的徹底迷茫。

張愛玲因父親的打罵、囚禁,從封建舊家庭中逃出,來到母親和姑姑身邊,進入了一個完全西化的世界。在享受着新生活的同時,她也敏銳地察覺到了在先進觀念、新生活方式背後,物慾如何異化着人一步步走向毀滅和墮落。
在大部分中國精英知識分子還在熱切地呼喚現代文明降臨時,她已經洞悉到了中產階級的荒涼,察覺到了女性在傳統舊文化和資產階級物慾文明雙重壓迫下,會誕生出什麼樣的怪物。
在她的筆下,無論是豪門千金、望族閨秀、還是小家碧玉,都不似蕭紅那樣爲活着發愁,可她們的靈魂深處沒有一絲一毫的進步。依舊深深浸潤在依附男性意識中,成天尋思和盤算着,如何找一個有錢的丈夫。
爲了實現這一目的,年輕的曹七巧心甘情願嫁給癱瘓的姜家二少爺,只爲個“正頭奶奶”稱呼。書香門第的白流蘇和範柳原周旋,明知對方是個花花公子,依舊爲能與他結婚在心中歡呼,接受過新式教育的葛薇龍,寧肯賣身也要爲自己尋得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依靠。
在《傳奇》中,張愛玲將這樣的女性寫了又寫,只爲說出一句,男性的壓迫固然是存在的,但女性的悲劇根源更是在於,她們自身頑固而持久的“奴性思想”。
對於大多數的女人來說,並不渴求所謂的真正的平等,愛的意思就是“被愛”,男性的愛與不愛,是女性生命價值的核心。女人一輩子講的是男人,唸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遠永遠。
因此就算實現了經濟的獨立,社會的解放,女性仍然無法擺脫人格的依附性,就算有一天“婚姻自由”,就算有一天“同工同酬”,就算有一天“禁止家暴”,這種千百年來積澱下來的女性精神創傷得不到重建,那真正的“男女平等”就始終是一種幻夢。
她們二人的文學都高度的與她們人生相關聯,對比來看,蕭紅的講述,更多的是站在一種人道主義角度,去控訴在封建傳統、父權社會裏底層女性生存的艱苦,是一種對女性的“哀其不幸”。
而張愛玲更多的是挖掘女性心理層面的陰影,試圖找到女性悲劇根源性癥結,是一種對女性的“怒其不爭”。
02.異類
蕭紅是在蕭軍、舒羣等左翼文學家的鼓勵下,開始進行文學創作的。
蕭紅前期的作品都有鮮明的左聯文學特徵,例如早期短篇《王阿嫂的死》《看風箏》《夜風》就都是講慘烈的階級壓迫,以自己曾經看到的父親,家族種種故事爲藍本,去寫農村大地主對於農民的肆意欺壓。

1934年10月,蕭紅帶着《生死場》的手稿,拜訪她一直崇敬的魯迅先生。在魯迅的幫助下,她的《生死場》,作爲《奴隸叢書》之一齣版,大受讚譽。由於其中對日本侵略者的譴責和控訴,激起了全國人民強烈的抗日情緒和喚起了民衆抗戰的決心,蕭紅也被納入了抗戰作家的行列。
不過,在和左翼文學家圈子的接觸中,她也時時感受到性別的精神歧視。她在《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一文中,就寫了這些進步青年私下聚會裏,是如何拿女性作家們開黃色玩笑。在《三個無聊的人》一文中,也諷刺過那些以高高在上的新式學者,以研究社會科學的名義去嫖娼。在《夏夜》中揶揄左翼文人嘴上罵着摩登女子是惡魔,但要是自己得到了這些小姐的紅脣,立馬就放棄了所謂的批判等等。
在這個過程中,她的文學觀念逐漸和左翼作家漸行漸遠。1938年在《七月》雜誌的一次座談會上,蕭紅稱:“作家不是屬於某個階級,作家是屬於全人類的,現在或者過去,作家寫作的出發點都是對着人類的愚昧!”,明確提出,文學不該是革命宣傳的工具。
這很顯然與大環境相背離。她與蕭軍分手,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端木結合就已經被看作是“投向奴隸的死所”般自甘墮落的行爲,等她與端木到達香港,接連創作了《呼蘭河傳》《馬伯樂》,更是遭遇曾經同仁的圍剿。
矛盾就曾說:“《呼蘭河傳》給人一種印象,除了因爲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而樂。”在一片“抗日救亡”的文學中,“這篇敘事詩,多彩的風土畫,悽婉的歌謠”顯得如此格格不入。那是否真的如他們所說,蕭紅在思想上退步了呢?
其實不然,如果我們仔細分析,《生死場》中,不管是地主壓迫農民,丈夫欺辱妻子,還是日寇侵華,其實本質上講的都是一件事“弱肉強食”。
強勢羣體如何依靠自身力量去壓迫弱者,弱者如何把屠刀轉向更弱者,這是比階級鬥爭,民族矛盾,性別歧視等等更爲本質的問題,根植於人性之中的弱點。
《呼蘭河傳》中她以四五歲女童的眼光書寫世界,談的依舊是同樣的話題,小團圓媳婦和向日葵般的王大姐,在異化女性殘忍的肉體和精神折磨中悽慘的死去,金枝在城裏遭到強暴和蹂躪,不僅得不到同情,還被母親鼓動返城去掙犧牲尊嚴和人格換來的鈔票等等,依舊是男權體制下女性生存之艱難,弱者相互之傾軋的悲慘命運。
她一直以來聚焦的,都是精神導師魯迅的“國民劣根性”話題,只不過作爲一個女作家,沒有像《生死場》一樣加入宏大敘事,就難逃“無法超越女性狹窄作品”的刻板印象。
如果說蕭紅是與主流漸行漸遠,那張愛玲這是從一開始,就背道而馳。她的筆下從沒有緊跟時代潮流的思想宣傳,一直專注於描寫囚禁燬滅女性一生的“鐵閨閣”。她對於政治態度是淡漠的,爲了迎接新中國,她曾寫了《十八春》,這部小說和她之前的作品整體基調並無二致,唯一不同的是突兀的結局,幾個虐的死去活來的主角隨着新社會的到來,積極投入了東北的革命工作。
而等她到了海外後,立馬又把《十八春》刪改爲《半生緣》,又把劇情改回了她最爲擅長的悲劇收尾,人帶着千瘡百孔的靈魂,無可奈何地生活下去。
幼年時期毫無親情的生活,成年時期坎坷無果的愛情,這些傷痛讓張愛玲對婚姻,對愛情,對人生,形成了一種持之以恆的荒涼感觸。
所以,她和蕭紅還有所不同,蕭紅到死的那一刻都還在叫喊着“不甘!不甘!”,還在訴說着自己生而爲女的不甘心。可見雖然生活悲苦,但蕭紅心中還有着許多未完成的使命,還有着許多未寫完的文章,還有着生的渴求。
但張愛玲的作品沒有這種飛揚的生命力,有的只有說不盡的蒼涼,在對自我一遍遍重複中,無法爲筆下的主角尋覓哪怕一個好的出路。最終只剩下,湊活過吧,還能死咋地,的那種無奈和虛無。
張愛玲與主流意識形態的疏離,就源自於她的這種,對所有東西都感到絕望的態度,不管是哪種主義在她看來,都無法填補人性的缺失,所以她放棄了掙扎,晚年閉門謝客,在孤寂中走向了人生終點。
與兩個“異類”相對的是主流“丁玲”,蕭軍不止一次在蕭紅面前,讚譽丁玲像男人一樣自立自強。而她所代表的,也確實就是最被男性所認可的女作家形象“雄性化”女作家。
放棄自身所有女性化的特徵,像個男人一樣投身於時代,以男性化的筆調去構造,一個個新時代的女性人物。就像丁玲自己說過,“要拋棄原有階級堆積在身上的苦悶,把廣大人民的憂戚融合到我的生命中。”
但這種形象終歸是有時代性的,當解放了的新女性重新回到家的樊籠中,左邊是丈夫的妻子,右邊是孩子的媽,女性獨立自爲的權利,是否還沒真正獲得,就又悉數上交了呢,這是一個問題。
很多沒深入瞭解蕭紅,就給她打上左翼作家標籤的人,很容易把她和張愛玲對立起來,但其實仔細分析會發現,她們二人是殊途同歸的。
她們二人都觸及到了“如何纔是真正的女性視角”的問題。如何才能塑造一個地地道道的女人,如何寫女人的真實感受,而不是用宏大敘事邊緣化女性的悲痛,這是“女性言說”要去解決的。
蕭紅和張愛玲雖然她們的文學風格天差地別,但實際上都是在用自身痛苦經歷吶喊,去徹底地解構屬於女性的黑暗歷史。
她們都是主流男性文學的反叛者,也是主流女性文學的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