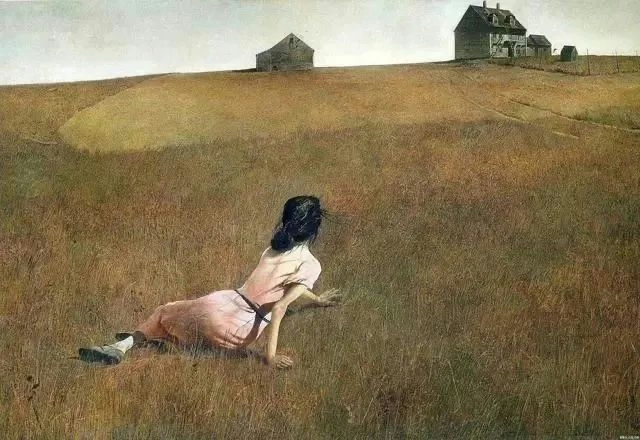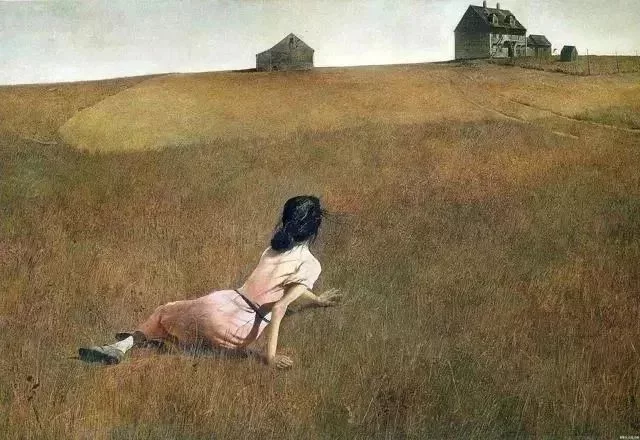
最近大家一直在互相說,出門對人客氣點。原因都懂的,每一張藍底白字都讓我更慫了一點。可是後來我想想,這不對啊。我本來就很慫了。我們這些慫人本來就不會鬧事傷人,你看通報措辭:
“當日13時許,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男,35歲)駕駛電動二輪車行駛至惠王陵東路路段時,因行車糾紛與小型轎車駕駛員賈某某(女,34歲)及同乘人員伍某(賈某某丈夫,35歲)、賈某(賈某某哥哥,38歲)發生口角,雙方相互推搡,後朱某某用隨身攜帶的刀具將伍某刺傷。伍某經送醫搶救無效死亡。”
正常人誰隨身帶刀啊?這類事情如果發生在我身上,都進行不到“互相推搡”的步驟,只要不是對方太過分,甚至都不會“發生口角”,頂多是挨兩句罵,我默默走人。
戾氣瀰漫,很多人都說要加大震懾力度。可是震懾的結果會是什麼呢?我們這些溫和的“慫人”本就不需要震懾,而那些戾氣瀰漫的“狠人”,似乎只會越震懾越亢奮。
爲什麼我這麼慫,現在網上開始傳播一個“幸福者退讓法則”,我覺得可以拿過來用,顯得比較優雅。但其實就是性格里帶的,不願意爲雞毛蒜皮的事跟人發生衝突。在有的時代有的社會,這挺丟人的,但在現代社會,不妨視爲一種優點,我們可以把勇氣用在其他地方,何必非把街頭當作舞臺呢。
我還有一些更加雄壯的理由,蘇東坡在《留侯論》裏寫過的:“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當然,把一個東西加個“大”字,就很容易變成語言污染。“拔劍而起,挺身而鬥”,就一定“不足爲勇”嗎,如果是見義勇爲,當然是勇。“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就一定是有“大勇”嗎,也不一定,有可能是真窩囊。人生是複雜的,判斷一個人是否有勇氣,需要做一個綜合的分析,而且要看關鍵節點。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勇氣應該是一個有縱深的概念,不應該只有“好勇鬥狠”這一種勇。讀過《史記·刺客列傳》的人都知道,那些留名青史的勇士,都不是隨隨便便跟人搏命的,通常要等一個知己出來,再把命託付給對方,還要等自己的老母親去世了,再去執行任務。
像這種街頭鬥毆弄出人命或把自己命丟掉的,司馬遷一個字的版面都不會給。可是現在網上卻頗有一種輿論,爲那些六親不認、無知殘忍的莽夫叫好。怎麼說呢,只能說是文化的墮落。但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爲什麼在信息發達,生活方式更加豐富的今天,很多人對勇氣的理解反而變得狹隘了?
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我前幾天刷到一個視頻,兩撥小孩在打架,兩撥成年人在圍觀,一開始成年人很淡定,但是打着打着,成年人陸續加入戰鬥。場面十分醜陋。關鍵是,這些成年人一開始在幹嘛呢?據合理推測,他們應該是聽信了某些流行觀點,“小孩子要學會保護自己的正當權益”“誰打你你就要打回去”,所以決定實踐一回,擇日不如撞日,棋逢對手將遇良才,演練起來吧。可是打着打着,發現自己家孩子喫虧了,所以按捺不住進入戰場……
這算哪門子的武德教育啊,這就是典型的巨嬰對武德的錯誤理解。如果你決定讓孩子“打回去”,就得接受孩子“打不過”的結果,即便打不過,事後跟孩子好好講一講,也不失爲一次生動的課堂。亂鬥一氣,只能說明這兩堆裏一個成年人都沒有。
非對稱攻擊不是武德,欺凌弱小不是武德。即便不談法律的紅線,這也是人類普遍認同的最起碼的底線。現在的那些報復社會事件,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絕對是懦夫的表現。在社會管理上,如何減少戾氣是一回事。在文化上,我們也有義務將這類行爲與“勇氣”這個美好的詞進行徹底切割。
蒙田講過一個故事,說有一個士兵作戰特別勇猛,國王賞賜給他很多禮物,女人,田地,金銀珠寶。後來又發生戰爭,這個士兵卻變得畏畏縮縮。國王問他怎麼回事,他說我從前一無所有,所以不知道害怕。
這個故事對我們今天是有啓發的。首先,一個社會要趨於文明發達,就要不斷減少赤貧人口,要讓大家真有“一頭牛”害怕失去。不僅是物質意義上的赤貧,還有精神意義、情感意義的赤貧。繁榮的經濟與繁榮的文化是相互支撐的。如果一羣人除了宏大敘事,再也找不到自己和世界的聯繫方式,那麼是很容易走上極端的。把文化搞得活潑起來,讓人的內心可以安放,可以抒發,絕不是一件小事。
然後,一個蓬勃多元的社會,纔可以培養出對於勇氣和英雄的多樣化理解。假如一個社會的小孩只知道把網紅當偶像,而網紅也只會引導他們把世界區分爲“家人”和“外人”,那這個社會是很危險的。這句話的意思絕不是說網紅不好,而是說除了網紅,還應該有更豐富的文化形態。無論身體還是精神,都需要更多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