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切特尼克首領塑像形成對比的是,今天的伊萬尼察似乎已經見不到鐵託時代的人物紀念設施了。當然我們只是走馬觀花路過此地,有沒有我們沒看見的?後來我還在網上查了一番此地的紀念建築,只發現鎮後山上有座南共時期留下的“革命紀念碑”,別無其他。革命紀念碑現在叫做二戰紀念碑,是大型馬賽克鑲嵌作品,裏面的人物羣像倒是南共的風格,但沒有人名,只刻有“1941-1945”字樣。

然而這裏是出過鐵託派大人物的,而且是叔侄雙雄,曾先後統治塞爾維亞十多年。兩人中的叔叔是鐵託打天下的股肱元勳,侄兒則是最終失去鐵託派江山(還連帶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的末代總統,叔侄兩人的人生歷程堪稱“鐵託主義”興亡史的縮影。只是對如今的伊萬尼察人來說,他們似乎都已經隱入了歷史的深處,令人浩嘆。
其中的叔叔皮塔•斯坦鮑利奇(以下稱爲老斯坦鮑利奇)1912年生於伊萬尼察鎮轄屬的佈雷佐瓦村,畢業於貝爾格萊德大學農學院。他戰前就參加南共,作爲鐵託的老戰友,戰時曾任塞爾維亞人民解放軍司令員,率部和同鄉兼死敵米哈伊洛維奇的切特尼克軍打得血流成河。

南共掌權後他一直躋身最高層,1948-1953年間任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兼總理,後來更成爲聯邦領導人,曾兩次接掌鐵託留下的交椅:1963年他繼鐵託之後出任聯邦總理,鐵託死後作爲塞族代表在鐵託生前安排的“輪流坐莊”體制下曾於1982年繼任南聯邦主席團主席(即聯邦總統)。

老斯坦鮑利奇無疑屬於鐵託時代最有權勢者之列,而且經歷鐵託幾次清洗塞爾維亞高層(尤其是1966年清洗蘭科維奇“中央集權主義”和1972年清洗尼克基奇“無政府自由主義”)的折騰而不倒,堪稱樹大根深。他退休後,侄子繼之而起在塞爾維亞掌權,並精心培養了米洛舍維奇。然而,在他垂暮之年風雲突變,他眼睜睜看着侄子被其一手栽培的米洛舍維奇推翻乃至慘遭暗殺,已經徒喚奈何了。
老斯坦鮑利奇壽逾耄耋而望期頤,在侄子遇害後又活了7年,才於2007年以95歲高齡悄然去世。他如果那時思維還清醒,會認爲自己長壽的暮年是幸福的嗎?
老斯坦鮑利奇之侄伊萬•斯坦鮑利奇(以下稱小斯坦鮑利奇)1936年也生於伊萬尼察的佈雷佐瓦村,畢業於貝爾格萊德大學法學院。作爲“紅二代”他很早就追隨叔父從政,仕途可謂一帆風順,1978年已經官至塞爾維亞共和國執行委員會主席(即總理),後來又做過塞爾維亞共盟主席和共和國總統,也就是黨政幾套班子的“老大”都做遍了。

而小斯坦鮑利奇的全部政治生涯幾乎都和一個人聯繫在一起,這個人就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

與“紅二代”小斯坦鮑利奇相反,米洛舍維奇的出身堪稱不幸。他的父親是一位東正教僧侶,1945年南共軍隊進入貝爾格萊德不久,他就拋下年僅4歲的小米洛舍維奇和自己在首都郊區的家庭,獨自隱居到黑山,1962年在那裏自殺身亡,種種跡象顯示他應該是個牴觸南共的切特尼克支持者。12年後,米氏的母親也於1974年自殺身死。米洛舍維奇曾提到:家庭的不幸對他的人生道路有重大影響。
在講究人事背景的黨國政治中,米洛舍維奇這樣的出身本來是極大的劣勢。但他上大學時結識的妻子米拉•馬爾科維奇卻又是個“紅二代”,其叔父德拉戈斯拉夫•馬爾科維奇在鐵託死後每年一換的“輪流坐莊”時代輪做過聯邦議會主席和南共盟中央主席團主席,幾乎與輪做過聯邦總統的老斯坦鮑利奇資歷一樣。兩家也很熟悉。靠着兩家位高權重的叔叔,這家侄女婿和那家的侄子成了鐵哥們。

小斯坦鮑利奇只比米洛舍維奇長5歲,但由於“根正苗紅”,政治上絕對是後者的教父,而仕途上則是後者的“前任”。你要問是什麼職位的前任?答曰:幾乎米洛舍維奇幹過的一切職位都是接斯坦鮑利奇的班。在長達20多年間,兩人關係都是這種模式:斯坦鮑利奇每任一職,就會把米洛舍維奇調到身邊當自己的助手。自己升遷了,原來的位子就交給米洛舍維奇接任。
1960年代斯坦鮑利奇擔任察爾石油化工公司黨委書記,他把米洛舍維奇召到該公司;斯坦鮑利奇升任塞爾維亞共和國計劃與經濟委員會主席時,米洛舍維奇便接掌察爾公司;斯坦鮑利奇調任南斯拉夫最大的國家銀行行長時,米洛舍維奇再次來到他身邊;斯坦鮑利奇當了貝爾格萊德市委書記,便推薦米洛舍維奇當銀行聯合會主席;1984年斯坦鮑利奇再升塞爾維亞共盟中央主席,他又薦舉米洛舍維奇接替他那首都市委書記的大位。
1986年5月,斯坦鮑利奇改任塞爾維亞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即共和國總統)——他一生最後一個高位時,又把塞爾維亞共盟主席的交椅交給了米洛舍維奇。最後,他的塞爾維亞總統位置也由米洛舍維奇接任了。
——但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次不再是他引薦米洛舍維奇,而是米洛舍維奇藉助街頭的“大民主”把他趕下了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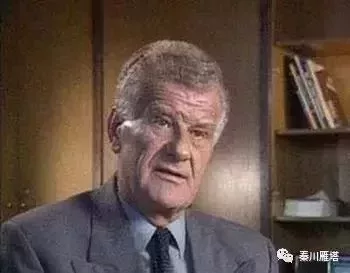
米洛舍維奇的紅二代妻子地位並不高,他的仕途可以說全靠斯坦鮑利奇這位“太子黨”,我們可以想象這20多年裏米洛舍維奇這位“太子跟班”是如何表現的。但是斯坦鮑利奇器重米洛舍維奇倒也不全因爲後者會巴結而又能幹,他們的思想也應該有些一致之處。
斯坦鮑利奇對鐵託時代打壓塞爾維亞的做法也有不滿,也曾努力維護塞爾維亞利益。早在鐵託去世不久的1982年,他就提出要保護科索沃塞族與黑山族居民的合法權利,並表示不害怕爲此被對手扣上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帽子。此後他又在1986年南共聯盟十三大上率先提出修改聯邦憲法以控制自治省權力的建議。他扶植米洛舍維奇,當然也是欣賞他爲塞爾維亞說話。
但作爲米氏後來抨擊的鐵託時代“機關權勢分子中的遺老”,斯坦鮑利奇希望在鐵託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改革,而不打算搞他斥之爲“再版的切特尼克政策”的大塞爾維亞極端主義。也是在1986年,斯坦鮑利奇嚴厲譴責了一些塞族民族主義者攻擊聯邦與其他民族的《塞爾維亞科學藝術院備忘錄》,而米洛舍維奇卻沒有表態。
按照斯坦鮑利奇的想法,“科索沃自治權過大”的問題可以在協商的基礎上先在塞爾維亞議會形成決議,提請聯邦議會修改憲法的有關條款,即通過合乎法理的漸進改革方式來解決。但他反對拋開聯邦、由塞爾維亞擅自取消科索沃自治,尤其反對把當時正在興起的民主化潮流引向極端民族主義的羣衆性歇斯底里,以免導致鐵託遺產的徹底喪失。
米洛舍維奇早先或許也是這樣想。但後來翅膀硬了,又適逢民主大潮,就有了“雄心壯志”。他從來不是“民主派”,但借塞族人對鐵託民族政策的不滿發動一場大規模羣衆運動卻成了他的如意算盤。他認爲這種“反官僚革命”不但可以徹底壓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和(伏伊伏丁納的)匈牙利人,還可以順勢搞掉共和國高層那些“因循守舊的老官僚”和“軟弱的機關權勢分子”,以塞族鷹派來個政治大換血。

勢不如人,老斯坦鮑利奇只能(左一)眼看着自己的侄子被米洛舍維奇(中)所害,進而發動塞族“改造”聯邦,清除“袒護”非塞族的領導層,從而使塞爾維亞不但對下可以擺平科索沃,對上可以控制聯邦,在全南斯拉夫“當家作主”,徹底出出鐵託時代所受的鳥氣。而且憑藉如此功勞,他也可以贏得塞族人的喝彩,從而在即將到來的民主化大潮中擊敗自由派。
這種“一石兩鳥”、把民主化引向極右民族主義的想法,在當時的東歐不是他一人獨有。俄羅斯的日里諾夫斯基就是一例,但沒有體制內地位的他一事無成,直到普京時代纔有了苗頭。而米洛舍維奇就不同了。
事實上米洛舍維奇雖然能幹,但因作風粗暴也樹敵很多,到了1980年代,他在民族問題上日益激進的言論屢屢使鐵託傳統下的黨國震驚,因此他最後幾次體制內升遷的阻力很大。尤其是1986年米洛舍維奇當選塞爾維亞共盟主席的大會上,米氏曾遭到多數代表的反對。是斯坦鮑利奇以前任主席身份“連續三天作了筋疲力盡的說服工作”,才使米洛舍維奇在這次據說是“塞爾維亞共產黨歷史上最緊張的選舉”中以微弱多數勉強過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