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十年浩劫的結束, 中斷了十年的高考與研究生考試陸續恢復招生,對一個國家來說,這是從失序回到正軌,從反智迴歸理性的開端, 而對於那些曾經被強行改變命運軌跡的知識青年來說,這場考試,是一個浴火重生的機會。
高考之後又考研
1977年的高考與1978年的研究生考試作爲“黃埔一期”都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觀。
如所周知,1977年高考因爲文革後“思想解放”的過程幾經討論,10月才定下規則,12月才考試,所謂77級大學生實際上是在1978年1-2月才進校的。但是幾乎在高考規則確定的同時,1977年10月高層就已決定恢復研究生招生,最初只是想讓中國科學院招,但很快更加“解放”的設想出來,到1978年1月10日教育部就決定把研究生招生擴大到經批准的一大批高校,報考資格更擴大到沒有讀過大學的“同等學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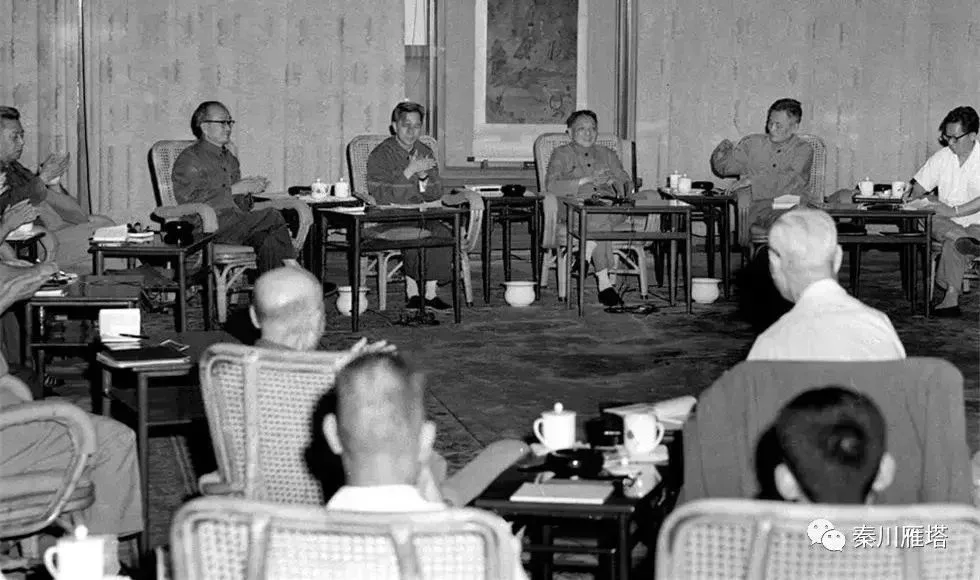
報考資格放得如此之寬,錄取名額卻非常少,研究生與本科生錄取名額之比只有如今的幾十分之一,從而在嚴格錄取的前提下爲“自學成才”者打開了一扇參與公平競爭之門。
決定做出後,招生安排落實很快,2月完成報名,3月發放準考證,5月15日全國統一考試。而這時77級大學生進校才3個月,離1977年高考也只有5個月。所以,當時有些人是連續參加了這兩場考試的。我者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1977年12月參加了文革後首屆高考,結果不甚理想。雖然據說在我們那個小縣算是文科總分第二名,但是各科成績卻是數學最高,語文不怎麼樣,這對文科考生很不利。加上我的志願填得太高,體檢更是“硬傷”。眼疾是我在農村待了9年多,多次招工招生招幹均被打回的重要原因,這次考研也幾乎因此折戟,由於導師力保才得過關,我曾在回憶趙儷生先生的文章中敘述過此一殊恩。
到了1978年2月間有過一次補錄,後來知道是一些地方舊習未除,“政審”卡掉了不少人才,鄧小平得知後認爲不對,遂決定在高分未錄生中再選遺珠,這也是那屆高考的又一特殊之處。我雖非因政審被卡,但也獲得補錄。不過這次補錄的學校都屬低檔,而且多在考生志願外,屬於多給一次機會,不去也不勉強。我因爲當時已經報考了研究生,補錄學校又很不理想,權衡再三就放棄了這次補錄。
“同等學力”者

我當時是上山下鄉插隊九年多的“知青”,廣西田林縣潞城公社營盤大隊平宜生產隊掙工分的“社員”。15歲下鄉時是年齡最小的知青,9年多來辭舊迎新,此時已經是我們公社南寧知青中僅剩的一個,在大批後來的本縣知青中儼然成爲元老,有人按當時習語送雅號曰“苦大仇深的老貧農”。
我號稱初中畢業,實際上1966-1969年的“初中”期間“一進校就停課,離校前(文革內戰)剛停火”,在學校裏我們那一派組織中,由於此後再無人入校,我們也沒上過課,於是一直被別人叫做“新生”,槍炮聲一停,我們忽然就成了“畢業生”了。儘管在九年多的“早稻田大學”中我也學到很多東西,在當地算小有名氣,但剛參加的高考就沒成正果,卻放棄補錄又去考研究生,在有的人看來未免太“冒進”。
那年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學生”,少部分是當時在讀的“黃埔一期”大學生和文革中的“工農兵學員”,少量沒讀過任何大學的“同等學力”者基本上也都是城裏的幹部、教師等“得風氣之先”的羣體,而且大多起碼還是讀過中學的。而我基本上只是文革前讀過六年小學,在當年的考研者中着實罕見。
當時我縣23個考研者中沒讀過大學的就我一人(考上了的也只我一人),我們系那屆錄取的11個研究生中,8個是老大學生,兩個是工農兵學員,“同等學力者”也只有我一個。全校錄取的“同等學力者”倒是還有若干,但本人身爲農民的,至少我還不知道有第二個。
我雖然比較自信,但也不至於狂妄,當時這樣做是有原因的:我自認論“表現”在當地幹部羣衆中還是有口碑的,論文化也不怕考試,但過去無論改革前重政治的“推薦”,還是重分數的前不久首次高考,我都被打了回來,主要是體檢過不去。有人說只看體檢表,給人的印象你就是個半瞎,應該走殘疾人就業這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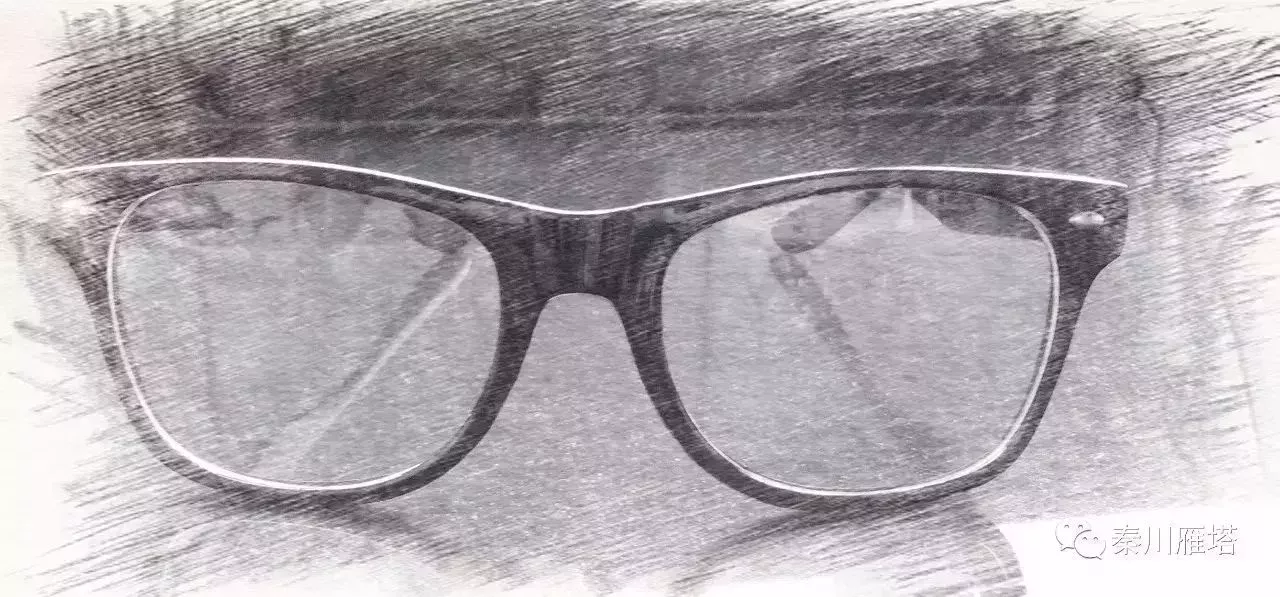
我當然不服氣,可是尋思要突破體檢關,恐怕得有得力的“伯樂”力薦。但是普通高考,考生幾百萬,統一命題,集體改卷,除非是“狀元”,不可能引起注意。這時候看到研究生招生消息,我就有了想法。那時培養研究生是一個導師帶幾個弟子,猶如師徒相傳,師傅選徒弟應該是比較有可能體現個性化的。
趙先生的知遇之恩
於是乘在文化局搞鄉土文藝的機會,我在縣裏查了全國招生導師目錄,覺得有兩位先生可能給我機會,一位是華東師大研究國際關係史問題的某學者。我給他寄了篇“習作”,是1973年石油危機和美元危機導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我寫的一篇筆記“金元帝國的崩潰”。此文根據當時流行的左派觀點,把美國無力維持美元兌金承諾導致的國際貨幣動盪說成是美元、甚至“美帝國主義”快要完蛋了。今天看來這是一篇毫無可取的“憤青”作品。
不過有趣的是,現在左派的說法已經完全相反,他們如今認爲美國發行不能兌金的貨幣體現了“美元霸權”的膨脹。2008年金融危機時,我曾在一篇論文中提到這件往事,因爲當年這篇筆記並不僅僅是我的想法,當時全球的反美輿論和我國的意識形態都對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幸災樂禍,沒人說這不是對美國的打擊、反倒是美國對世界施展霸權。
事實上,說美元不能兌換黃金就意味着美國行將崩潰,當然不對,但是美國維持不住由它自己倡導建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無疑顯示它在從戰後霸權頂峯走下坡路,至少不能說它比以前更強大吧?如果說美元不能兌金就意味着美國“不受制約”,豈不等於說此前更強大的美國在自己找“制約”?此後不那麼強大了它反倒“不受制約”了?所以,不是說美國沒有霸權或不追求霸權,但用美國霸權或美國陰謀來解釋危機,顯然是不合邏輯的。
這當然是現在的看法了。話說回來,當時寄出這篇文章後沒有得到回信,但華東師大還是寄來了準考證。不過那年考研的時間是全國統一的,一人不能分考兩頭,所以我只能放棄。現在想來,沒有導師的力薦幫助我克服體檢障礙,加上國際關係史需要的外文優勢我並不具備,考上的希望幾乎是沒有的。
另一位就是我後來的恩師、蘭州大學的趙儷生先生,他在1950年代被打成“右派”發配西北之前活躍於史壇,所著(包括與師母高昭一先生合著)的幾本書我們家裏都有。
家父1949年前在大學就是讀歷史系,以後也一直有這方面的興趣,家裏這方面的書不少,趙先生當年在山東大學與幾位同仁創辦的《文史哲》雜誌,從開始徵訂到文革一度停刊我們家也一期不缺。這些我原來都讀過,在導師目錄中看到這一熟悉名字後又讓家裏把這些書和文章都寄來細讀,對先生的研究有了較多瞭解。

先生這些著述多數是關於農民戰爭史和史學理論的。在“反右”中蒙難後,先生的精力轉向土地制度史研究,但是卻被剝奪了發表著述的權利,他這方面的成果大都是在改革時代發表的,我當時不可能知道。不過土地制度史本身是文革前中國史學的“五朵金花”(五個討論集中的重大問題)之一,我對相關討論也有了解,加上在農村九年也有些直感吧。因此就給先生致信請教,除表達投師之意外,還寄去一些我關於農民戰爭和土地制度史相關問題妄加議論的“習作”——現在看來只能叫讀書筆記。
寄出這些當然意在投石問路,希望得到先生的回信。但先生回信的熱情和嘉許還是出乎我的期望。他不僅對我這個素不相識又毫無資歷的自學者大加獎掖,鼓勵我認真備考,還給我寄來一包參考書。我後來又告訴他我可能遇到體檢問題。先生說:只要你初試複試都表現突出,體檢問題我會盡力爭取解決。後來他果然這樣做了。說實話我真是非常感動。“我本非良驥,愧對伯樂期;駑馬自加鞭,不負恩師意。”我放棄補錄而一心考研,也就不算是狂妄了。
在“早稻田大學”學外語
我們現在知道1977、1978年高考的一個結果就是致命地打擊了當時已是很不得人心的知青上山下鄉政策。尤其是“插隊”知青,本來紀律約束就沒有“兵團知青”那樣嚴,平時就有部分人滯留城裏而“不在隊”。1977年宣佈恢復高考、而且實行按分數錄取後,大量知青都紛紛回城複習備考,連一些樣板知青點都幾乎走空了。一些地方爲了穩住這些樣板,曾經私下許諾會給表現好的模範安排上大學的“捷徑”,結果卻鮮能兌現。
更有甚者,從1978年開始,很多地方招工也開始用考試的辦法選擇文化水平相對高的新工人,使得“文化低無出路”的危機感在知青中更加蔓延。於是這一年不但回城備考之風更盛,就是本來沒打算考大學的人,包括不少模範知青,也看出留在村裏已無前途,紛紛另謀回城之路。因此儘管當時知青政策宣示尚未明顯變化,但是知青運動顯然已氣數將盡了。
而我無論1977年高考還是1978年考研都是在村裏備考的。當時20多人的知青點經常就只有我還在“堅持”,這曾使當地一些幹部大爲讚許。我們平宜知青小組是縣知青辦的“點”,雖然不像鄰近的央務知青小組作爲自治區知青辦樹的典型那樣大名鼎鼎,但通常還是受好評的。而到了這時,連央務典型都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我卻還能在村裏待得住,令他們刮目相看,認爲我平時儘管“表現不錯”但並不大紅大紫,而到了這時卻只有我“經得住考驗”。
但其實我留在村裏,只是因爲我父母那些年裏也被放逐到一個窮鄉僻壤的山區縣,那裏的條件並不比田林好。而在南寧我已“無家可歸”,不留在村裏我能上哪裏去呢?
77年考試前後我還是間歇出工的,考完的第二天還上了龍車水庫工地。但是進入1978年後就不然了。春節時我曾回父母所在的鳳山縣過年,在家裏找了一些書,並向鳳山中學的英語老師請教了一些問題。但是那時我尚未報名考研。而返回田林報名已在年後,剛剛探過家也不好再走了。不過,我留在村裏並不是要與那些模範一比高下,經受什麼“考驗”,其實從2月間報名到5月間考試我都很少出工了,基本上也是在備考。
回想起來,那時我花在專業上的時間還不算最多。當時除體檢外,外語是另一個障礙。記得1977年高考時,除外語專業外一般考生的外語成績是僅供參考,不計入總分的。但研究生考試外語就是個硬槓。當時文革剛過,國人的外語水平普遍低,“黃埔一期”也不例外。尤其是中文、中醫、中國史這類帶有“國學”色彩的專業,導師大都主張重專業,而不過分要求外語。但總分數仍是一道坎。

而趙先生當年是清華外文系出身,他還是重視外語的。我當時只讀過先生的著述,對他的早年一無所知,但我自知與一般考研者不同,由於有體檢的障礙和資歷的缺失,我必須在其他方面樣樣都讓人無話可說,先生纔好爲我爭取。
我雖然在農村自學過英語,但此前並沒有重視。臨考需要提高。而在農村別的都可以看書自學,唯有外語,在當時全無視聽工具的情況下又沒有老師,起碼聽、說都是沒法自學的。我於是完全不管聽、說,連教科書都不怎麼看,只死啃幾本不同的語法書,力求掌握語法,而在語法書的例句範文中熟悉詞彙的同時,還直接閱讀大學外語專業高年級教材中的長篇課文以增加詞彙量。
由於完全不管發音,我讀單詞都是按漢語拼音來讀的,比如home就被我讀成“霍麼”。我的記憶力還可以,很快積累了一定的詞彙量,掌握語法後就形成了一定的閱讀能力。考研時是蘭州大學外語系出題,我考了48分,在中國史考研者中名列第二。但是這樣學的英語是既不能聽也不能說的“聾啞英語”,以至於後來進校後聽研究生外語課都困難。
當時學校認爲研究生水平應該比本科生高,所以研外的老師常常就直接用英語講課。當然我可以去聽用漢語講授的本科外語,但我覺得那太花時間,而且也浪費我的閱讀能力。於是我索性就“路徑依賴”了,沿襲故技,自己就着詞典和語法書看外文原著,閱讀中理解不了的疑點記下來。上外語課時老師講的我似懂非懂,下課時就拿原著追着老師請教與課堂內容不相干的一大堆問題。
這樣很短時間內我居然先在分班考試中由初級班升入高級班,接着在全校研究生一外(英語)、二外(日語)的第一次“過關”考試中成爲蘭大第一批外語“過關”的研究生,而且英語成績並列第二,日語甚至是第一。
不過說實話,我也就能夠應付那時的考試而已。那時的外語考試都不考聽、說,否則我就露餡了。而且由於過關後我就全力搞專業,不再上外語課,雖然專業中的外文資料我還是在看,但總的閱讀能力並無提高。到了國外也依然是“聾啞人”。
沒有聽、說配合,就沒法真正進入語言環境,形成外語思維,隨着年齡增大,機械記憶力減退,閱讀能力還會下降。我常對孩子說我的外語學習其實是不足法的。但在“早稻田大學”的環境下,不這樣我還真的很難過考研的外語關。
就這樣,我在5月間作爲唯一的“同等學力者”到縣城參加了研究生考試。6月間我拿到了初試通過、去蘭大複試的通知書。後來得知,在蘭大同專業考生的初試中,我的兩門專業課分數都是第一,外語第二,政治較差,總分也是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