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士坦丁七世寫作DAI的時代,這些“白色”族羣已經逐步基督教化,並且向不同方向遷徙:塞爾維亞人如前所述,先後遷到愛琴海邊、多瑙河畔,大概與當地人(這兩個地方當時都已是久經開發的有主之地)不能相容,最後又轉徙進入了今天斯圖代尼查所在的拉什城一帶山區定居下來,並在這裏接受了拜占庭一系的基督教(東正教)。
拉什(又譯拉斯)被視爲塞爾維亞最早的“首都”,周圍地區“拉什卡”因而有了“受洗的塞爾維亞”之稱。在奧斯曼征服前的幾個世紀,“拉什奇亞”(拉什卡人)甚至已經成爲塞爾維亞人的同義詞和代稱。
克羅地亞人則走向另一個方向,在8世紀前他們已經遷徙到達爾馬提亞海岸,接受了羅馬天主教,並形成一系列小公爵(Ban)。到了925年,其中的一個有爲之主托米斯拉伕力克羣雄,成爲第一個克羅地亞國王,並從克寧城堡出兵,與拜占庭結盟打敗了保加利亞。把統治版圖從海邊一直擴張到德拉瓦河與德里納河畔,疆域幾乎相當於今天克羅地亞與波斯尼亞的總和。


這就是第一個克羅地亞人的統一國家;也被認爲是前南地區第一個由延續到今天的民族建立的較大國家。1925年後,在“第一南斯拉夫”時期,當時的各民族“聯合王國”爲托米斯拉夫立國一千年曾經對此大加宣傳,今天薩格勒布火車站前的托米斯拉夫廣場就是那時命名的。

而波斯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則是在大約兩百年後才創造了類似成就。在DAI裏也提到Bosona,即波斯尼亞人,當時就是住在波斯尼亞河流域的斯拉夫族羣。他們名義上是匈牙利的藩屬,實際上在這片山區自立。在宗教上,那時他們已經被東西基督教會都視爲異端——當然不是因爲幾個世紀後才由奧斯曼征服者傳入的伊斯蘭,而是因爲他們獨特的“波斯尼亞教會”,這是一種從保加利亞傳入的基督教波戈米勒派異端,具有早期基督教諾斯替派和新摩尼教的二元論特點,雖然崇拜上帝和耶穌,但不承認三位一體,也不視十字架爲神聖,這也成爲那時波斯尼亞人的一個特徵。
如今還有些民族學者主張他們在體質遺傳上乃至語言上也有特點,如保留更多的前斯拉夫時代山區土著的基因等等。我不是專家也無力做這方面的判斷,但僅從當時留下的一些波斯尼亞王公名,如庫林、圖爾特克等來看,似乎也與今天波斯尼亞人名有明顯的不同,不太像斯拉夫人名。
當時,正如塞爾維亞人在拉什卡地區形成了許多茹潘(王公)一樣,波斯尼亞人與克羅地亞人也形成了許多“巴恩”(Ban,一般認爲來自突厥語的“伯顏”,蒙元時代這個稱呼也常見於中國,意爲總督或頭人)。1180年波斯尼亞大巴恩庫林恃強自立,以後代有強人,各領風騷,如此綿延百餘年。到圖爾特克一世(1353-1391)時統一波斯尼亞諸部,並對外不斷擴地,加冕稱王。於是繼塞爾維亞人的杜尚帝國解體後,波斯尼亞王國成爲巴爾幹又一強國,最盛時不僅據有今波黑全境,還據有今克羅地亞的達爾馬提亞海岸和塞爾維亞、黑山的部分地區。

塞爾維亞人的建國晚於克羅地亞,而略早於波斯尼亞。從8世紀開始,在愛琴海岸和多瑙河畔生活得不如意的斯拉夫族羣陸續進入拉什卡山區,780年這裏出現了見於記載的第一個茹潘,名叫維舍斯拉夫。以後小茹潘林立,中間在969年拜占庭一度出兵此地,在拉什設置政權直接統治,而此前茹潘們也從拜占庭接受了東正教。屬地化的“拉什奇亞”和宗教性的“受洗的塞爾維亞”遂成爲同義詞。
拜占庭的直接統治沒有持續多久,拉什卡又恢復了茹潘林立狀態,在傾軋與兼併中出現了弗拉斯蒂米爾洛維奇、沃伊斯拉夫列維奇和武卡諾維奇等“王朝”,實際上就是各個茹潘間通過聯姻和分封形成的一些聯繫。12世紀中葉,原來控制拉什卡的沃伊斯拉夫列維奇家族因反抗拜占庭而被廢黜,原來僻居澤塔(今黑山境內)的武卡諾維奇“王朝”茹潘扎維達被拜占庭扶植爲拉什卡的統治者。扎維達死後,他的長子蒂霍米爾繼立,並與兩個弟弟分治了拉什卡。
扎維達的小兒子斯特凡•奈馬尼亞沒有得到封地,但卻不知通過什麼途徑得到了拜占庭的支持。這奈馬尼亞據說道行很是了得。他在澤塔出生時受的是天主教洗禮(澤塔因與克羅地亞和威尼斯人接壤,受到天主教影響),但到拉什卡後即按東正教禮儀重新受洗,而且很快成爲狂熱的東正教信徒,一生以討伐異教徒、大興東正教、最後捨棄王位入山爲僧而著名。他得到拜占庭的支持大概也與宗教有關。

他的興起本身就是個帶有“靈異”色彩的故事:據說他到拉什卡後建了許多東正教堂,而統治者大哥蒂霍米爾從澤塔受到天主教影響,視他爲威脅,把他關進一個洞穴中。然而這時聖喬治(就是基督教造型藝術中經常出現的那位屠龍英雄)顯靈,把他從洞穴中救出。於是他起兵討伐三個哥哥,拜占庭給他提供了一支由希臘人、法蘭克人和突厥人組成的僱傭軍,幫助他終於在1168年殺了大哥,流放了二哥三哥,統一了拉什卡,成爲整個“受洗的塞爾維亞”的大茹潘。
奈馬尼亞隨即開始對外擴張。這種擴張也帶有明顯的宗教色彩。他先是聯合東正教會成立了個討伐波戈米勒異端的委員會,以宗教名義攻打波斯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焚燒異端經典,摧毀異端教堂,花了十年時間“根除了異端邪說”。晚年他又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紅鬍子腓特烈在尼什結盟,大力支持十字軍東徵。

當然,大茹潘的信仰也有很實用的一面,信仰東正教並不妨礙1171年他與威尼斯、匈牙利和神聖羅馬帝國(都是天主教勢力)結盟對東正教的拜占庭作戰,企圖徹底擺脫與拜占庭的藩屬關係並奪取拜占庭的土地。但這個聯盟很快瓦解,拜占庭捲土重來。奈馬尼亞很識時務地又主動向拜占庭皇帝曼努伊爾一世負荊請罪,乃至被押解回君士坦丁堡,在凱旋門下作爲“蠻族俘虜”在拜占庭的凱旋儀式上示衆。但不可思議的是:據說又是他對宗教的虔誠感動了皇帝,以致皇帝又恢復了對他的信任,並重新封他爲拉什卡的世襲大茹潘。
然而,幾年後曼努伊爾一世去世,奈馬尼亞又興兵反對拜占庭,從後者手中奪取了科索沃。至此,經過30年的努力,奈馬尼亞統一了塞爾維亞諸部,建立了奈馬尼亞王朝。
不過歐洲所謂的“王朝(dynasty)”與我國秦以後所謂的王朝完全不是一回事。奈馬尼亞自己就是前一個“王朝”武卡諾維奇王朝的“王子”,“武卡諾維奇王朝”與之前的茹潘也是類似的關係。“王朝更替”未必意味着易姓奪權、天下大亂,而“王朝統一”也是短暫的,茹潘林立的“封建”狀態並未根本改變。但是在奈馬尼亞之後,這個王朝在時聚時分的狀態下確實還輝煌了一陣。特別是到他的五世孫斯特凡•杜尚(1331-1346稱王,1346-1355稱帝)時,一度建立了一個“塞爾維亞帝國”。

在拜占庭帝國內亂、衰敗,而奧斯曼帝國還沒有打上門來的這個空檔裏,杜尚打下了一片“從愛琴海到多瑙河”的江山,包括今天的塞爾維亞、黑山、科索沃、馬其頓、大半個希臘和波黑的一小部分。這是近代多民族南斯拉夫出現之前,這片土地上的民族所建立的版圖最大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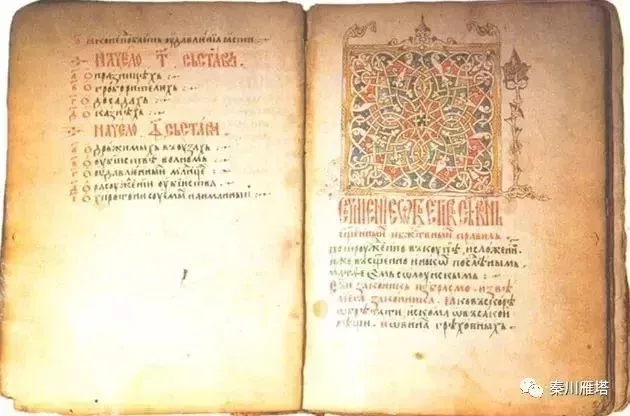
但是,號稱“塞爾維亞人和希臘人的皇帝”的這位“杜尚大帝”的功業也是曇花一現,他死後塞爾維亞又陷入茹潘林立的狀態。
總之,10世紀中期到14世紀中期,即在從DAI到科索沃大戰的這四百年裏,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這幾個民族都已經形成,並且先後建立過托米斯拉夫的克羅地亞國、奈馬尼亞-杜尚的塞爾維亞國和圖爾特克的波斯尼亞國這幾個比較大的“民族統一”政治實體。它們與今天存在的三族國家在地理上有相當高的重合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