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時巴爾幹這三族的差異似乎比現在更大,起碼不是現在這樣幾乎“三族共語”。它們的交往也並不密切,尤其不比各自與其相鄰的其他民族密切。
特別是克羅地亞人與塞爾維亞人,如果說地理上位於這兩者之間的波斯尼亞人和這兩者都還有交往的話,被波斯尼亞隔開的克羅地亞與塞爾維亞在這幾個世紀中的歷史很少有交集,當時也並沒有出現諸如羅馬帝國、鼎盛時期拜占庭帝國、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那樣能夠把這三個族羣、至少其中兩個族羣囊括進來使其密切接觸的宏觀地緣政治格局。
另一方面,當時這幾個民族都還處在諸侯林立的“封建”狀態,各自內部整合程度並不高。無論托米斯拉夫、奈馬尼亞-杜尚還是圖爾特克,他們的“統一”功業都是曇花一現。而在這個時期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三族都是茹潘、巴恩林立,無論哪兩個民族關係整體上的好壞其實也是談不上的。
例如杜尚大帝死後塞爾維亞就分裂了,奈馬尼亞的子孫互相攻伐,各引外援,拉扎爾聯合波斯尼亞國攻打阿爾託曼諾維奇。你不能以拉扎爾的立場說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友好,也不能以阿爾託曼諾維奇的立場說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有仇,不是嗎?
其實,這也是歐洲“前民族國家”時期的歷史常態。這段歷史給人的啓示,就是文化上的相近與否與政治上的友好乃至認同與否是兩回事(其實我們周邊的中日關係等等也是類似例子),而交往的密切化也可能同時導致兩個似乎矛盾的結果,即“文化”似乎是接近了,但政治仇恨卻加深了。民族認同這個“想象的共同體”有時就是要靠歷史機緣和具體的互動實踐,不是從文化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的“宏大敘事”就可以推論的。
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本來不太可能會有三族合一的“南斯拉夫”國家。而二戰後無論是王國流亡政府還是鐵託掌權,南斯拉夫都是戰勝國,這本來是有利於戰前就不太穩定的這個多民族國家增加凝聚力的。但鐵託在建立“專政”的同時又搞了個法律上可以自由退出的“列寧式聯邦”,他死後聯邦遭遇轉型危機,舊體制下形成的怨恨已經來不及通過建立新體制發展新的國家凝聚力來化解,聯邦要延續下去確實很困難。但沒有米洛舍維奇亂來的話,前南即便分家也不太可能搞成屍山血海的大悲劇。
當然,那時的塞克波三族是不是現在的塞克波三族,或許不易分清。曾經有人從遺傳學上研究,說波斯尼亞人不僅是信伊斯蘭的問題,他們的基因組合也有與古波斯尼亞人一脈相承的特徵。但是現在基因分析得出的驚人結論已經不少,有的說現在被視爲同一民族的人其實來源各不相同,有的說現在好像差別很大的“異族”其實基因高度一致。這都是不能直接用來解釋現狀的。就以中國北方而論,所謂“五胡亂華”時代居民血緣其實變化很大,但這並不決定民族認同的走向。
至於中世紀並非穆斯林的波斯尼亞人與塞爾維亞人是什麼關係,這種關係與今天的兩族關係有無聯繫?這裏我想到一箇中國曆史上類似的例子:我國古代的“回回”、“回部”原來並不是指今天的漢語穆斯林羣體,而是指從古代的回紇、回鶻、畏兀兒到近代維吾爾一脈傳下來的西北突厥語系民族。

這些民族並不講漢語,原來也不是穆斯林,那時的漢“回”交往與矛盾也就相當於中原漢族與塞外突厥等民族關係的水平。可是後來“回部”伊斯蘭化了,於是有了“回教”之說。
再後來在元朝隨着西域回教“色目人”大量進入內地,語言、宗教乃至血緣的交流就逐漸產生了講漢語的“回民”,1949年以後更進一步被正式確定爲“回族”。這時的回族幾乎遍居內地各省,漢回交往之密切和文化的互滲就已經遠遠超過了古代漢人與突厥諸部交往的水平,而近代漢回沖突的頻繁與烈度也不是當年漢族與回紇回鶻之間矛盾可比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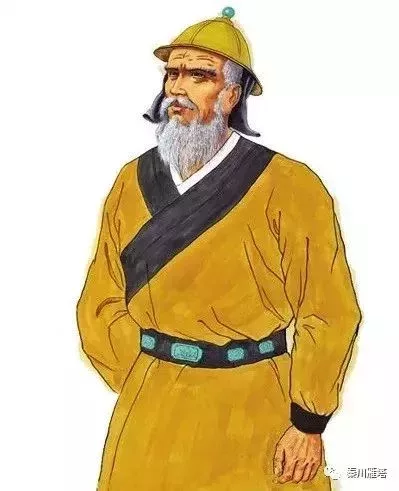
所以,今天的漢回並不是古代的“漢”“回”,可是兩者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歷史聯繫,而今天的關係也不能從歷史關係中簡單推論的。
類似地,中古波斯尼亞人不像今天那樣與塞族“同語”,也不是穆斯林,但在奧斯曼時代他們與塞族同受土耳其統治,語言趨同,而宗教卻趨異,血緣應該也有相當程度的融合。關係密切了,而怨恨也積下了。
因此他們與塞族的關係也並非自古就確定的。許多跡象表明,鐵託時代波斯尼亞人中不信伊斯蘭教卻保留波斯尼亞認同的情況也是存在的。鐵託劃分出“穆斯林族”固然削弱了塞族,卻並未使這些波斯尼亞人滿意。
當時的波黑共盟主席波茲德拉克(一個不信伊斯蘭教的波斯尼亞共產黨人)曾對鐵託表示:“他們(塞族)不允許有波斯尼亞民族,卻提議叫我們‘穆斯林’。我們接受這個提議,雖然族名錯了,但隨後我們將開始波斯尼亞認同的過程。”在兩人談話的1970年代誰也沒想到這個過程會走向後來那個方向。
但今天我們無法確定:假如當初鐵託答應了他的要求,他們會因換了個族名就不產生別的問題了嗎?反過來想,假如這兩個同樣不信教的無神論共產黨人共同忙於應付別樣“主義者”的合法競爭,就像希拉里與奧巴馬共同應付共和黨的競爭一樣,他們還會爲那個“族名”問題耿耿於懷嗎?
好啦,現在讓我們回到中世紀吧。進入“受洗的塞爾維亞”,第一個要看的就是斯圖代尼查修道院。
走出冷水河峽谷,地形稍顯開闊。路邊出現了一座又似城堡又似莊園的建築羣,這就是著名的斯圖代尼查修道院。在踏着深秋的落葉走進大門時我有兩個印象,一是這裏遊客稀少,與我想象中這麼個名播遐邇的人類文化遺產應有的訪客雲集之狀完全不同。

後南斯拉夫時代人們爲“民族矛盾”打了那麼慘烈的仗,而印象中他們的“民族”又基本是以宗教劃分的,我以爲他們對宗教聖地會有高度的熱情,現在看來也不過爾爾?

二是這裏同樣是自由參觀不賣門票。當然歐洲各地的教堂大都如此,只是高塔、珍寶館和墓穴之類非禮拜場所如果開放的話通常需要遊覽門票。前南地區的不同在於:除克羅地亞外,其他各國不僅教堂,包括城堡、歷史遺址在內的名勝也不收票。但是教堂的開放程度則相對保守,高塔、珍寶館之類地方通常不開放。

斯圖代尼查,不僅古蹟可觀,背後的故事也很精彩。這個修道院的開創者就是中世紀唯一曾經統一塞爾維亞的奈馬尼亞王朝的開創者斯特凡•奈馬尼亞。這個君王的經歷上節已經講過,總之此公從一個沒有封地的落魄小王子,先是被長兄囚於石窟而得聖喬治顯靈拯救,繼之藉助拜占庭一舉打敗了三個有封地的哥哥,統一拉什卡後反過來又向拜占庭擴地。
他兒時受天主教之洗,成年後改弦更張,成爲東正教的衛道士,力闢波戈米勒異端,襄贊十字軍之大舉。既與天主教列強結盟反拜占庭失敗,卻又得以東正教之虔誠感動拜占庭君主赦其反罪而讓其復位。這些作爲已經讓人嘖嘖稱奇。
而他奮鬥30年、以鐵血手段終於統一了塞爾維亞之後,卻做出了更驚人的決定:1196年3月25日,斯特凡•奈馬尼亞在首都老拉斯城召集貴族委員會,宣佈把王權讓給他的次子“第一加冕王”斯特凡,而他則與王后一起拋下剛建立的王國,在拉斯城下的聖彼得和保羅修道院立誓出家爲僧了!

從此奈馬尼亞國王變成了修士西麥昂,安娜王后變成了阿納斯塔西婭修女。不久西麥昂進入他做君主時修建的斯圖代尼查修道院,他原先的王后則跑到另一小城庫爾茹姆利亞的基督之母修道院,兩人分開修行。但是即便清心寡慾如此,西麥昂還嫌這裏不是淨土,一年多後他開始雲遊四海,最後跑到愛琴海上希臘東正教聖山阿索斯的希蘭達爾修道院,在那裏隱居起來。

這期間,由於他不立嫡長,長子烏堪不服氣弟弟繼位,兩兄弟打起了內戰。但西麥昂既入空門,心如古井,居然聽任他建立的王朝陷入混亂而不加理會。而他的三兒子拉斯特克可能是確蒙神召捨棄了人間富貴,也可能是被兩個哥哥的爭位弄得心灰意冷,也跑到希臘加入了父親所在的修道院,從拉斯特克王子變成了薩瓦修士。

父子二人捐出大量財產,把希蘭達爾修道院打造得十分興旺,至今仍是塞爾維亞東正教會的境外聖地。而這對父子後來也被東正教會宣佈爲聖徒,這就是著名的聖西麥昂和聖薩瓦。

1199年,聖西麥昂以86歲高齡在希蘭達爾修道院去世,1206年,聖薩瓦遵從父親遺願,把他的遺體遷回拉什卡,葬在了斯圖代尼查修道院。據說正在打內戰的兩兄弟被父親的聖徒精神感召,終於握手言和。後來聖西麥昂的遺體據說也出現了種種神祕的聖蹟(異香、異光等),引來衆多的朝聖者。

繼承父志的聖薩瓦後來也多有作爲,他寫了一本《斯圖代尼查的典範》,以父親的一生爲例宣傳東正教的神學思想、教會傳統和聖徒志向。這本書至今傳世,成爲塞爾維亞東正教最著名的神學典籍。他也成爲自己創立的塞爾維亞東正教大主教區的首任大主教,後來杜尚大帝建立佩奇大總主教區,聖薩瓦又被追尊爲首任大總主教。他死後也葬在這裏,斯圖代尼查於是從奈馬尼亞王朝的王家修道院,進一步升級爲塞爾維亞東正教的一處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