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出生的利亞伊奇畢業於薩拉熱窩大學醫藥系,學生時代就參與波斯尼亞運動,回到桑扎克後他在1990年成爲民主行動黨創始人之一。後來他不滿該黨的波斯尼亞民族主義太“意識形態”,於1993年退出,並另建了桑扎克民主黨。
該黨主張“歐洲化”並與塞爾維亞的中左派合作,同時積極參加反對米洛舍維奇暴政的塞爾維亞反對派陣營。米氏垮臺後,利亞伊奇加入親歐洲的科斯圖尼察政府並擔任人權與少數民族權利部長,而他建立的黨也改組爲“歐洲的新帕扎爾-桑扎克民主黨(SDP)”,進一步強化了與其他民族誌同道合者的合作。
2008年他加入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SDPS),並仿效德國聯邦政黨與巴伐利亞政黨的關係(有自治傳統的巴伐利亞左中右派都有與聯邦不同的叫法,如基督教民主聯盟在巴伐利亞的同道叫基督教社會聯盟,在聯邦選舉時他們實際上是一起的,就叫基民盟-基社盟),使自己建立的SDP與SDPS共同以SDPS-SDP的名義參加全塞競選,最後在2013年實現兩黨合併。
利亞伊奇本人則作爲SDPS的新黨首,在中左聯盟競選獲勝後出任塞爾維亞政府副總理和國際國內貿易及電信部長,成爲有史以來桑扎克波斯尼亞人在塞爾維亞執政的最成功者。而“歐洲的新帕扎爾-桑扎克民主黨”也成爲新帕扎爾地區選舉中勝出的執政黨。

就這樣,利亞伊奇不僅以“歐洲的新帕扎爾”口號超越於塞族和波斯尼亞族兩種民族主義的對立,並用“歐洲化”取代了要麼分離自立要麼波斯尼亞人接受塞族統治這種二擇一的目標困境,而且與伏伊伏丁那匈牙利族、塞爾維亞本部塞族中的普世主義者一起,倡導族際寬容、合作和共贏。同時更與國際社會積極配合,利亞伊奇本人曾兼任塞爾維亞與海牙國際法庭合作全國委員會主席,爲追緝戰犯、實現轉型正義基礎上的民族和解做出了貢獻。
全國政治民主化條件下桑扎克民族主義的淡化,當然不僅僅體現爲一個利亞伊奇。與穆斯林居多的塞爾維亞桑扎克有別,在桑扎克的黑山部分,波斯尼亞人僅居少數,在黑山全國就更是很少數的族羣了。但按照現在的體制,波斯尼亞人不僅在黑山桑扎克地方政壇舉足輕重,他們的政治家還在黑山國家層級上參與執政。如黑山共和國本屆政府,就有副總理拉菲特. 胡索維奇等3名波斯尼亞族閣員。他們都是黑山“波斯尼亞黨”(BS)政治家,通過全國競選作爲政黨聯盟“歐洲的黑山必勝”的成員執政的。
我們知道,少數民族擔任民選政治家與皇上欽點“蕃官”的含義是完全不同的。皇上任用蕃人,充其量只能說皇上本人在用人上很開明,與整個主體民族是否開明,是否消除了“夷夏之辨”的歧視,在邏輯上完全是兩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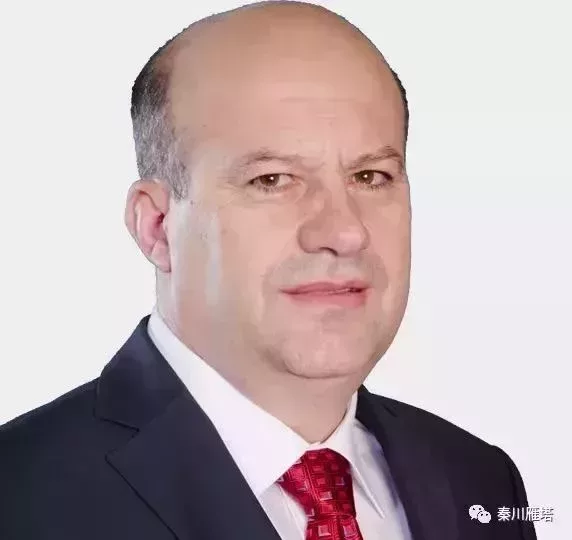
這樣的蕃官並非土司,更不是蕃人的“代議士”;作爲朝廷命官他是給皇上、而不是給蕃人辦事,蕃官對蕃人甚至都未必比漢官更友好。所以這種事或許也是好事(皇上開明總比愚頑好),但扯不上“漢蕃”關係平等。
民主國家其實也有類似邏輯。美國黑人學者威廉. 威爾遜曾指出:美國黑人當高官早已有之,但像黑人四星上將鮑威爾這樣的高官儘管貴爲美國最高軍職參聯會主席,與黑人議員、州長和奧巴馬總統這類人出現的意義還是大不一樣。
像鮑威爾這種任命制的高官只能說明任命者沒有種族偏見,不能說明一般白人的態度。但奧巴馬當選就不同——倒不在於總統這“官”更大,而在於他與議員、州長一樣,不是某個開明者任命的。授權給他的是選民。如果多數白人選民投了黑總統的票,那就意味着白人的態度確實與過去不一樣了。
前南的情況也是如此,鐵託安排“八族輪流坐莊”並不能使各民族真正感到平等,各民族也不認爲被安排者代表了他們。但是利亞伊奇、胡索維奇這類波斯尼亞族政治家的出現就不同了,因爲他們是選舉出來的。當然,利亞伊奇等人不像奧巴馬是全民直選,他們的小黨是加入政黨聯盟後整體出線的。但這種間接體現的選民意志還是與鐵託時代任命各族官員有本質的不同,它意味着桑扎克的民族對立的確是實質性地緩和了。
同時,這些民族性小黨如果單獨競選絕無勝算,但加入或左或右的政黨聯盟後就有了執政可能。不過這時他們已經不僅是所在民族的代表(當地選舉證明瞭這一點),而且首先是全國性左派或右派的代表,他們追求的也是在全國實現左派或右派的“主義”,而不會是一個民族的分離了。
像在黑山桑扎克,波斯尼亞人本來就不佔多數,即便獨立也未必有利於他們,可是“波斯尼亞黨”加盟後,不僅在地方選舉中能夠得到跨族盟友的支持,而且聯盟勝出也使他們可以影響全國政壇。

當然,這些小黨在執政聯盟中一般只是配角,通常這些國家還做不到像美國多數白人選出黑總統、南非西開普多數黑人選出白省長那樣的事。不過配角不等於“花瓶黨”,因爲在民主格局中他們至少可以自主選擇加盟對象。而且在兩大聯盟旗鼓相當時,他們的選擇往往成爲決定性的“黑馬”。這時他們對國家政治的影響會大大高於其選票的比重。
而更基本的是:在“多數決”機制下少數民族整體上雖不可能有大民族那麼多的選票,但作爲個人,每個少數民族成員與大民族成員的權利完全是平等的,這不比他們分離出來做“本族皇上的臣僕”合算嗎?所謂民族平等,本質上難道不就是要表現爲不分民族的每個公民的權利平等嗎?
黑山現在的執政聯盟叫“歐洲的黑山必勝”,由社會主義民主黨牽頭,包括了BS和“阿族民主聯盟”、“克族公民倡議”等少數民族小黨。而反對派聯盟也同樣擁有跨族陣營。這樣就把族羣的對立變成了左右的分野。可以設想,這種狀態如果穩定下來,兩大聯盟會逐漸變成兩大黨。小黨會按“主義”而非按族羣合併成大黨,就像桑扎克民主黨最終加入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那樣。如此,族羣政治就徹底轉化爲“左右”政治。而跨族的民主國家認同就在“左右”競爭中穩定了。
總之,一個“歐洲化”方向,一個民主憲政,是前南和巴爾幹地區解決民族衝突、實現民族關係正常化的兩大要件。桑扎克的考察也證明瞭這一點。但願“歐洲危機”不要愈演愈烈毀了這一切。
今天的新帕扎爾是座忙碌而又充滿古趣的城市。在塞爾維亞經濟不發達的南部山區,該城應該說是很繁榮了。

據資料介紹,這裏的穆斯林頗有商業頭腦。前南時代這裏建了一些紡織廠,聯邦解體時期這些國營廠相繼倒閉,私營紡織-製衣業卻盛極一時。甚至在聯合國對塞爾維亞實行制裁期間,儘管全國經濟凋敝,新帕扎爾卻曾經一枝獨秀,由於紡織工業的強大私營主動性推動,這裏生產的牛仔褲就以新潮而且能夠緊跟時髦而銷路大增。與中國的晉江、溫州當初一樣,新帕扎爾的紡織業者先僞造名牌商標,後來就自創品牌,使整個地區的紡織業名聲大振,各種服裝暢銷國內外。
然而2000年後,米洛舍維奇垮臺,國際社會解除了制裁,塞爾維亞的經濟出現復甦和繁榮,新帕扎爾的紡織製衣業卻因來自亞洲的廉價紡織品大量進口而趨於衰落。現在這裏的人們還在爲開發替代產業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而傷腦筋。

同時,在經濟趨冷、民族矛盾緩和後,原來被經濟繁榮和民族矛盾掩蓋的紡織廠私有化中的下崗問題等等,又作爲轉型公正問題浮出水面。類似於前面提到的圖茲拉事件,這裏近年來也出現了階級博弈增多的現象。但正如我們前面討論過的,這其實是一種早該出現的正常現象,而且對穩定民族關係是有利的。
我們來這裏是要尋找世界遺產老拉斯,本無意遊覽現在的市區。但這個小城並無繞城公路,而且城區沿拉什卡河呈東西向長條狀,我們恰恰是溯河而上從東北向西去老拉斯,又順河而下從西向東南迴來並轉去科索沃,一來一回,經由不同路線兩度穿過市中心區,也算把她走馬觀花看了個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