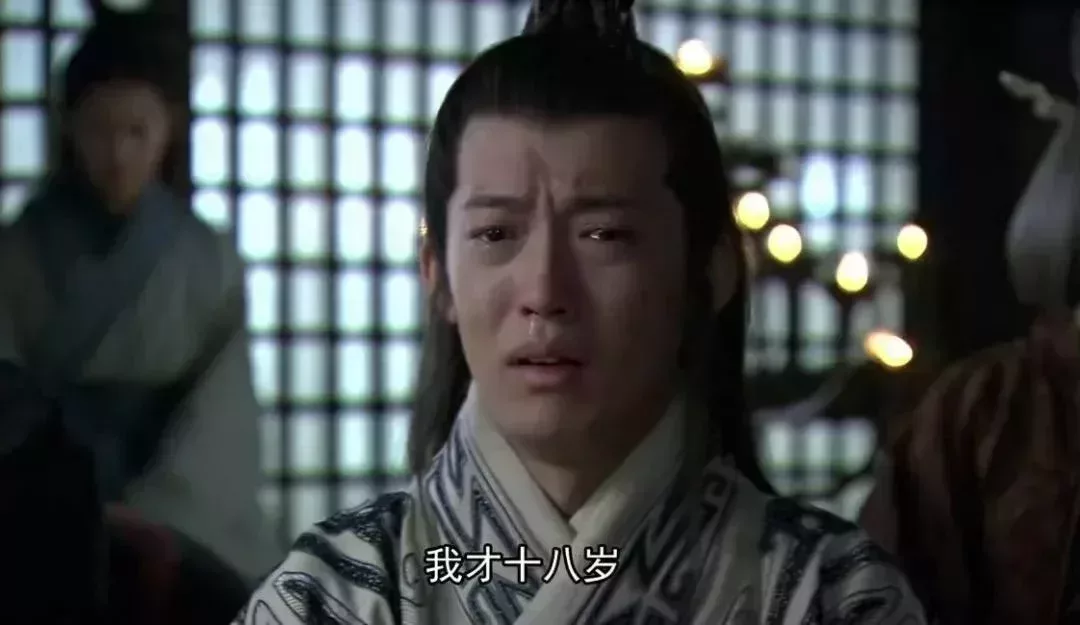
中國古代的大學生是怎麼樣的?他們學些什麼?又考些什麼?古人上了大學後,是不是直接去朝廷打工了?
西周辟雍、宋朝書院、明朝國子監……中國古代的學校是如何建立、發展的?這些學校和當時的朝廷又有着怎樣的關係?
這些問題,我們均可以在史學大家錢穆的經典著作《國史新論》中找到答案。
我們會成爲什麼樣的人,和我們受到的教育關係密切。我們能接受什麼樣的教育,和國家的歷史、政治相勾連。而一代人接受教育的總體境況,又將影響政治與歷史的發展。
錢穆在《國史新論》中寫道:“全部中國思想史,亦可謂即是一部教育思想史。至少一切思想之主腦,或重心,或其出發點與歸宿點,則必然在教育。中國一切教育思想,又可一言蔽之,曰:‘在教人如何做人。’”
今天,我們摘選了書中“中國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一章,呈現中國古代教育的興衰與特色,“就新時代之需要,探討舊歷史之真相,給時人以借鑑”。
01 西漢
西漢的教育制度和選舉制度是相結合的。要想成爲政府官員,需要進入太學學習一年並參加考試。
西漢教育制度之重要性,乃以“育才”與“選賢”雙軌並進。換言之,乃是教育制度與選舉制度之配合行使。由地方學即郡國學申送十八歲以上青年入太學,受業一年,經考試,以甲乙等分發。甲等得在宮廷充皇帝侍衛,乙等迴歸本鄉作吏。
爲吏有成績,重得選舉入充皇宮侍衛,再由侍衛分派到中央及地方政府擔任各職。
此一制度,形成了此下漢代政府,較之以前歷史上所有之舊政府,展現了一獨特之新面相。凡屬政府成員,皆須太學出身,或是由太學生服務地方政府爲吏之雙重資格爲出身。此等人,皆經政府之教育與選擇。每一成員,既通經術,亦長文學,又擅吏事,漢人謂之“通經致用”。縱位極丞相,亦不例外,必備此資歷。故漢代自武帝以下之政府,乃備受後世之崇重。後代政府,亦莫能自外於漢代之規模,而別創一新格。總之是受教育的始能任官職。教育地位乃顯在政治之上了。
博士於五經,有兼通,有專精。但雖兼通,亦必以專經任教。惟一經亦可有幾派說法,經太學博士與朝廷公卿會合審查決定。所以到宣帝以後,五經共設有十四博士,即太學中共有十四個講座,此外不再添列。
所難者則在考試,須定一客觀標準。故每一太學生,必申明其自己乃依據某一講座之說法而作答。漢人謂之“家法”。五經共分十四家,每一經之章句訓詁,必遵從某一師之家法,以爲考試之答案,乃能及格。其實所謂師傳家法,皆爲便於考試;在學術上,其高下是非則仍待討論,非有定案。
但太學在此後已成爲利祿之途,來者日衆。其先博士弟子只五十人,漸增至一百人、兩百人、一千人。有人說孔子弟子三千,太學生名額遂亦增至三千人。此已在西漢之末年。下及東漢晚期,太學生乃增至三萬人。試問十四位講座,如何能教三萬名學生?太學至此,逐漸變質,失卻了開始重視教育之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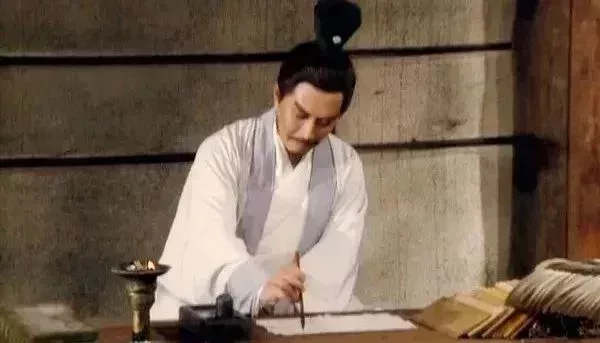
02 東漢
漢朝考試需要遵循“家法”,但有這種墨守成規的標準答案的存在,創新活力受到抑制,民間私學因故興盛。
既定家法,則重墨守,陳陳相因,無發明,無創闢。私人聰明反而窒塞了。於是官學遂又不受人重視。真心求學的,重又轉歸到社會私學去。私學即是排拒在博士講座之外的;或是在博士家派之外,自有講法的;或是在博士家法之中,有所融會貫通的。既非十四家法,即爲太學所不容,於是隻在民間設教,當時謂之“開門授徒”。
太學博士所講,以其爲當時所通行,稱爲“今文經學”。民間所授,以其非爲當時所通行,乃稱爲“古文經學”。古文經學無家法,可兼通,可博採。此亦都在東漢之世。私學乃又代官學而崛起。
其間最值一述者有鄭玄,山東高密人,曾造太學,又自向私學從師,遊學遍全國。以東方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介紹,投馬融門下。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受業者五十餘生。玄在門下,僅得高業弟子轉授。三年,不獲見融一面。某日,融會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召見於樓上。玄因得備問所疑。既畢,辭歸。融喟然曰:“鄭生去,吾道東矣。”玄不仕在鄉,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曾途遇黃巾數萬人,見者皆拜,並相約不敢入縣境。孔融、袁紹亦對玄備致敬禮。
就歷史言,無數百年不敗之政治,亦無數百年不壞之制度。西周以下辟雍、泮宮等制度,今已無可詳說。秦漢兩代博士制度之演變,經學上今古文雙方之異同得失,餘已有專書詳述。惟鄭玄以在野學者之身,當朝廷提倡數百年經學達於墮地將盡之際,玄之爲學,不專治一經,更不專師一家,能囊括匯通,成一大結集。此下十四博士家法師傳盡歸散失,惟鄭玄最晚出,而使經學傳統不墜重光。其功績實爲兩漢經生四百年來所未有。
可見教育事業,主要在“師道”。師道所貴,主要在爲師者之“人格”與“學問”。振衰起弊,承先啓後,其能發揮絕大功能者,則多在師不在學校,又每在野不在朝,抑且在亂不在治。如鄭玄之在兩漢,即可爲一例。故其人在中國教育史上,尤爲後代所重視。
鄭玄稍前,有一郭泰亦當附說。郭泰亦當時一太學生。其時太學生數萬人麇集京都,博士倚席不講,又值朝政黑暗,激起太學清議,成爲當時政治上一難對付之力量。而郭泰是太學生中之翹楚。同時又有苻融,亦太學生,師事少府李膺。膺乃當時名公卿,但見融,必絕他賓客,聽其言論,爲之捧手嘆息。郭泰家貧,從其姊夫借五千錢,遠出從師。並日而食,衣不蔽形。及來太學,時人莫識。融介之於膺,時膺爲河南尹,待以師友之禮。後泰歸鄉裏,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泰惟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視若神仙。時漢政已污濁不堪,太學亦有名無實。但公卿中有賢如李膺,太學生中有英特奇偉如苻融、郭泰。其故事著之史籍,長供後人玩賞。雖無救於漢室之覆滅,但中國文化之內蘊,與夫其社會精力之充盛,可知此下尚有無窮生命,決不隨一時朝政而俱熸。

03 唐朝
唐朝國力強盛,公立教育再度興起,但和漢代不同的是,唐代的教育與考試不再捆綁發展。唐代以考試選拔人才,考試內容看重詩賦創作。
隋唐統一盛運再興,於是漢代公立教育制度亦隨之復起。唐初太宗時,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都派留學生來中國,太學生多至八千餘人。又有書、算、律各門專科,學制似較漢代更爲進步。
但漢制須先進太學,再經選舉;而唐代則教育、考試分途發展。太學出身與進士之公開競選屬於兩事,把考試來代替了漢代之選舉。學校出身其事易,公開競選其事難。社會羣情,都看重進士,不看重太學生。當時中央政府地位雖高,而國家公立教育則未有大振作。抑且唐代還有門第教育與寺院教育之存在。就教育言,則未見有大勝於魏晉南北朝之世。
唐代考試重詩賦,其事亦未可厚非。考試本是一種智力測驗,短短一首詩,其中有學問,有抱負,有寄託,有感想;不僅智力高下,即其學問人品,亦可於此窺見。若作策問或經義,題材內容,先已有了限制,未易出奇制勝。而且陳陳相因,易於揣摩抄襲。不如詩題,層出不窮,無可準備。而應考者卻得借題發揮,各盡其趣,於拘束中見才思。
唐代終於把進士考試來漸漸替代了門第勢力。社會孤寒之士,亦得平地拔起,廁身仕宦,使仕途不再爲門第所壟斷。而寒士應考前,則常赴寺院中讀書。乃有如王播“飯後鐘”故事。相傳播客揚州某寺,隨僧齋餐。僧加厭怠,乃齋罷擊鐘。播作詩有“慚愧闍黎飯後鐘”之句。後播顯達,出鎮揚州,訪舊遊,其所題詩,已受碧紗籠之。或傳段文昌事與此相類。其他此等事,亦復屢見。
故可謂唐代僅有考試取才,而無學校養才。養才仍賴於寺院與門第。寺院所養不爲世用,門第出身比數漸不如進士之多。而進士又僅尚詩賦,不免實學漸衰,流於輕薄。唐晚季,昭宗時,鄭綮以爲“歇後詩”得相位。彼自謂縱使天下人皆不識字,相位亦不及於我。制詔既下,曰:“笑殺天下人。”又曰:“歇後鄭五作相,事可知矣。”或問綮,相國近有詩否?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此處那得之?”此亦可謂有自知之明。
然國家豈得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人來掌理治平。其時則已若政府社會舉世無才,有才則只在寺院中作禪宗祖師去。
唐末有書院教育,此事乃門第教育之殘波餘影。門第沒落,子弟向學無共學之人。乃於宅旁建書院,藏書其中,延納俊秀之來者,可爲子弟作師友。又爲避世亂,常擇名山勝地建書院,則受寺院影響。而書院之盛,則待宋代。故言中國教育史,有唐一代,實有腰虛中弱之象。此亦不可不知。

04 明朝
明朝廣泛立學,學校教育與考試製度再次融合,學生想要進入國子監,須先參加科舉考試,進入國子監後,需要學習十幾年,方能出任官職。
明太祖未定天下,即在婺州開郡學。及即帝位,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府設教授一,訓導四。州設學正一,訓導三。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自二十人至四十人。據一時統計,全國府、州、衛、所,共得教官四千一百餘員。較之北宋元豐時學官,幾多近百倍。則明初注意興學不可謂不力。
地方生員升至國學,初稱“國子學”,後稱“國子監”。監生分赴諸司先習吏事,稱“歷事監生”。亦有遣外任者。在學十餘年,始得出身。洪武二十六年,曾盡擢國子生六十四人爲佈政、按察兩使及其他高級官職,出身遠優於漢之太學。又必生員入學始得應舉,則學校與考試兩制度亦復融合爲一。此皆明制之優於前代者。
即在此後,明代南、北監,常簡大學士、尚書、侍郎爲司成。一時名儒爲國立大學校長者,項背相望。晝則與學員會饌同堂,夜則燈火徹旦。不乏成材之士出於其間。明代國力,與漢唐相抗衡,人才輩出,亦與政府重視教育之意有關係。
然由政府辦學,學校興衰,終視政治之隆污而判。故明代之教育制度,雖可稱道,而教育功效則終有限。此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又明代政府中,擁有大批學人,可以不負實際行政之職位。此亦兼寓有一種教育意義在內。進士及第,一甲得入翰林,二甲、三甲得選爲庶吉士。因其未更事,俾先觀政,同時進學。此一制度,論其淵源,實頗似於秦漢時代之有博士官。翰林猶如博士,庶吉士近似博士弟子。迴翔政府,儲才養望。此製爲清代所沿襲。論其制度,有張有弛;論其作用,有顯有晦;論其意義,在政治集團之內而別有一種養賢儲才之機構與組織,此則大值重視。
漢代政府之此項措施,乃受戰國諸子在野講學之影響。明代政府此項措施,則受宋元儒在野講學之影響。唐、宋兩代之政府中,亦有與漢、明大同小異相類似之措施。此見中國政治重視學術與教育之傳統精神,乃無時或已。此乃中國政治史上一大特點,所當大書特書,以供後人作參考。
惟由政府來提倡學術,培植教育,其最高意義總不免偏重於政治。此已不能滿足在野學術界之理想要求。而且中國傳統政治,學校、選舉兩途並重。學校在造賢,選舉在拔賢。而學校與選舉之兩者,均不免要以考試爲標準。考試製度之在中國,遞有變遷,而終於不勝其流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弊已如上述。明代以經義取士,其變爲八股,流弊更甚。於是民間講學,仍必與朝廷提倡相對立。
明代民間講學,雖遠承宋元,下至武宗時代王學特起而大盛。陽明政務在身,而兼亦從事講學。其所至,學徒羣集。唱爲“惜陰會”,欲使學者時自集會,講論研究。及其身後,流風益甚。各地社會,自有組織。其大弟子,年有定時,分赴各地。一面藉此集會,交換心得,討論新見;一面集合羣衆,公開演講。稱爲“講會”,亦稱“會講”。
此與朱陸書院講學有不同。一則講會近似一學會,學者同志藉以互相切磋。一則講會以宣傳普及爲務,更近一種社會教育。循而久之,以普及代替了提高與深入。故此種講會,雖曾一時風起雲湧,而亦滋流弊,終於不可久。
最後乃有東林書院出現。此一書院之規制,更近似一學會。學者常川集合,輪流主講,重在自相切磋。而所講亦涉及當時之政治。逮此一學會遍及全國,更復在京師有分會,乃引起政治大波。直至明室覆滅,黨禍始告結束。
下至清代,政府公立學校,無論在中央,在地方,其在傳統上均已名存實亡,無一定之宗旨以爲規則,以爲號召。在野學者,風氣亦變,無復宋、元、明三代講學之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