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這一年被視爲中華民族百年屈辱史的開端,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重大分野。同一年,美國民主共和黨正式改名爲民主黨,美國兩黨輪流執政的局面正是鼎立,這一年標誌着美國現代政黨制正式形成。
現代政黨制起源於民主革命之後,在君主專制時期,只存在朋黨,現代意義的政黨並不存在,也不具備孕育出來的基本條件。
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之後,英國議會掌握了實際權力。在處理現實問題時,因爲價值觀和代表利益的不同,議員們開始主動或被動的劃分成派系,並開始分裂融合,最終演化出輝格和託利兩個大黨,這便是最早的現代政黨。
在大洋彼岸,1787年美國憲法起草時,美國根本沒有政黨,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最初也不相信任何黨派。他們期望建立一個充滿和諧、沒有黨爭的國家。
比如華盛頓就十分反感黨派。他認爲,政黨維護的是派系利益,是少部分人的利益,不是國家利益。甚至在1796年的告別演講中,華盛頓還警告說,黨派是共和最危險的敵人,將帶來可怕的專制。
但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民主政治必須奉行多數決原則,也就是以多數人的意見爲準繩。而多數決原則,就決定了多數人會主動或被動的聯合,這就讓黨派的誕生無法避免。
通俗來講就是:因爲需要投票決定國家的政策,根據政治觀點的差異和代表利益的不同,議員們自然而然會形成不同的派系。

其實在美國製憲之初,美國就已經萌生了黨派。有一派人主張建立強大的聯邦政府,強調聯邦的權力,通過權力集中來維護北美的統一,建立一個自上而下的共和政體,代表人物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另一派則主張限制聯邦政府的權力,強調公民的權利,通過維護州權和地方自治,建立一個自下而上的共和政體,代表人物是託馬斯·傑斐遜。
在華盛頓卸任之後,兩派人馬開始支持不同的總統候選人,最終導致了兩黨制的初步形成。
1874年,美國著名畫家納斯特,分別以長耳朵的驢和長鼻子的象比擬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嘲諷他們一個愚蠢膽小、一個笨重守舊。沒想到兩黨竟然欣然接受,並以驢和象作爲黨徽。民主黨認爲,驢子既聰明又有勇氣。共和黨認爲,大象既威嚴又有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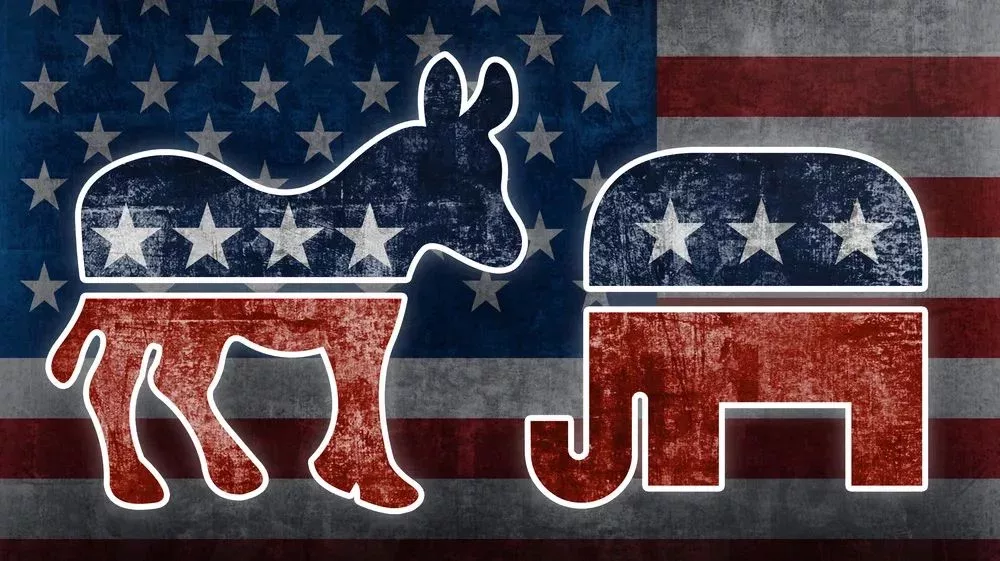
美國內戰結束後,美國驢象之爭的格局延續至今。如今美國的黨派活動十分繁榮,在冊的黨派竟然高達430多個,當然主要還是民主共和兩個大黨。
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曾經說過:公民權利與黨派活動,猶如空氣與火,去掉前者,後者就會消失。只要保護公民權利,就必然滋生黨派。如果爲了禁止黨爭,就扼殺公民權利,智者不爲也。
這便是大名鼎鼎的麥迪遜悖論。麥迪遜認爲,利益集團的出現來自於人的本性,來自人們對共同利益的維護,所以利益集團不可能消失,更不可能用強制的方法將其消滅。
麥迪遜認爲,政府的作用就在於兩個方面:一是緩衝。因爲利益之爭不可避免,所以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協調利益集團的關係。如果溫和的協調失效,那麼內戰就不可避免。二是控制。“多數利益集團”獲得“權力”後,就會損害“少數利益集團”的權利,因此國家的制度設計就要防止這種狀況的發生,比如橫向的三權分立、縱向的地方自治等等。
於是,麥迪遜提出了利益集團之間“遏制與平衡”的理念,也就是用利益集團的野心,去對抗和平衡利益集團的野心,這就是現代黨爭存在的必要性。
從這個理念出發,現代政治必須保護不同黨派的存在,目的就是爲了保障公民的權利,最關鍵之處在於不能讓任何黨派凌駕於國會之上。
也正如陳獨秀先生大徹大悟之後的名言: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1922年,蘇布歷經5年時間,徹底清理掉了其它黨派,然後宣佈其它黨派都是反革命集團。而且蘇布凌駕於一切之上,制憲會議更是被取消,國家的一切大事都由蘇布內部一個小利益集團來做決定。隨着權力的更替,這就導致蘇布的小利益集團及其附庸,會遭到下一代小利益集團的無情打擊。
蘇布這樣的治理模式,弊端顯而易見,體制僵化、官僚腐敗、經濟崩潰等等,都如跗骨之蛆。所以蘇聯解體之時,就是蘇布垮臺之日。
以“文明衝突論”而享譽世界的亨廷頓認爲,民主的第一個標準,就是政黨之間對民衆手中的選票進行公平公開的競爭。
亨廷頓認爲,黨派競爭執政的好處有兩點:一是國家體制可以不依賴政績的合法性,因爲糟糕的政績只會歸咎於現任政府,而不會歸咎於體制本身。二是對現任政府的罷免與取代,可以讓這一體制不斷的更新和進化。因爲不存在體制和歷史的包袱,所以就可以大刀闊斧的改革與創新,從而盡最大可能避免體制的僵化。
比如臺灣地區和韓國,曾經都是一黨壟斷,執政的合法性極度依賴於政績。雖然他們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都取得了大小不等的經濟成就,但當經濟不再有8%的增長速度,失業、通脹等等經濟危機都會帶來社會的劇烈衝突。如果唯一的執政黨繼續抱殘守缺,那麼後果可想而知。
所以1986年,面對社會空前高漲的變革呼聲,小蔣說出了亞洲民主進程三句箴言的第二句: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語氣輕微,卻有如雷霆萬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