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皇帝,必然是憋屈、不快意的”
(一)
1054年,宋仁宗化身爲“純愛戰士”,決定爲自己摯愛的女人爭一份名譽。
這一年正月初八,年僅31歲的張貴妃不幸玉碎珠沉,她是仁宗皇帝一生最愛的女人,白居易那句“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用來形容張貴妃生前所獲的恩寵,恰如其分。
與莊重、嚴肅、不苟言笑的曹皇后相比,張貴妃溫柔、懂事、乖巧得多。面對皇后時,性格軟弱的仁宗常感壓抑,而在張貴妃的溫柔鄉中,給予仁宗皇帝的只有香溫玉軟、小鳥依人。

“巧慧,善迎人主意”的張貴妃,按今天的解釋,大概率是屬於“討好型人格”,這與她坎坷的人生經歷有關:
她幼年喪父,母親無力撫養姐弟三人,不得已只能將她賣掉。不料幾經輾轉,她被大長公主買下來做了舞女。所以張貴妃其實自幼便在宮中長大,長期寄人籬下的生活,使她年紀輕輕便已識透人間冷暖,心思之細膩自然遠勝那些望門閨秀。
自康定元年仁宗皇帝在一次宮廷宴飲中,無意間瞥見張姑娘跳舞之後,到慶曆三年這短短四年時間,張貴妃一共生育了三名公主(可惜都沒能活過5歲)。
妃嬪的生育頻次,是受寵與否的重要指標。考慮到女性的生育間隔和皇帝后宮數百名爭寵的女子,仁宗對張貴妃的確稱得上榮寵備至。

所以,當這樣一位摯愛突然離世,仁宗皇帝內心的悲傷可想而知。隨後,這份悲痛理所當然地控制了皇帝的理性,它很快化作超越常規和現成禮法的種種恩寵,與守文持正、恪守規矩的文官系統產生了衝撞:
仁宗皇帝希望以皇后的喪儀,爲心愛的張貴妃在皇儀殿治喪——這件事遭到了時任副宰相梁適的實名反對。
仁宗皇帝又下詔表示,將爲張貴妃之喪輟朝七日——御史呂景初大聲抗議,他說幾年前荊王趙元儼(宋太宗的第八子,按輩分是仁宗皇帝的叔祖)去世時,朝廷不過才輟朝五天,張氏只是一個一品貴妃而已,怎可“恩禮過荊王”?
按祖宗禮法,貴妃之喪,只當輟朝三日。
我都想替仁宗皇帝罵一句:老子最愛的女人薨了,你他媽的怎麼還想着多上幾天班啊?你身上的班味兒都把人味兒淹沒了。

正月十二,仁宗皇帝又下詔,表示將追封張氏爲皇后,賜諡溫成——然而正宮曹皇后健在,皇帝追封死去的貴妃爲後,在當時也是不符禮法的。
這封詔書遭到了樞密副使孫沔的強烈反對,這哥們數次上書,最開始只是勸阻皇帝不要追冊張氏爲皇后,後來連宰相也一併罵起來,意思是說,皇帝種種越禮行爲,都是當朝宰相這個佞臣鼓舞的。
面對仁宗皇帝逾越常規禮法的行爲,御史臺也沒閒着,以御史中丞孫抃爲代表的御史、諫官,輪番上疏,“奏請罷追冊”,甚至以集體辭職的決心“要挾”皇帝。
雖然御史臺羣臣激憤,但極悲之下的仁宗皇帝心意已決,他表現出個人帝王生涯中少有的“一意孤行”的任性,執意以皇后喪儀送別此生最心愛的女人。
可關於此事的鬧心事還沒有停止,在爲溫成皇后發喪的儀式上,原本預定流程是孫沔讀哀冊。誰也沒想到,事到臨頭,孫沔站在皇帝和滿朝大臣之前,寧死不爲溫成讀哀冊。
孫沔倒不是和溫成皇后有什麼私人恩怨,他的理由仍是“不合禮法”,因爲按規矩,皇后發喪歷來由翰林學士讀哀冊,“今召臣承之,臣實恥之”。
然後,這哥們竟然在溫成皇后的喪禮上,在衆目睽睽之下,將哀冊放下,自行告退了,玩了一手無組織無紀律。
時任宰相陳執中爲避免皇帝尷尬,趕緊撿起哀冊讀了起來,這才讓溫成皇后的喪禮得以繼續。
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爲溫成皇后撰寫碑文的環節,翰林學士擬好碑文後,仁宗皇帝希望請知制誥蔡襄手書碑文,因爲蔡襄是大名鼎鼎的書法家。
但皇帝的這一請求,卻被蔡襄明確拒絕了,他說這不是我負責的事,“此待詔職也”,這個理由簡直令千年後996的牛馬淚流滿面。
蔡襄面對帝王之悲,如此“不近人情”,仁宗也無可奈何,不能勉強他。
因爲仁宗皇帝不喜奢靡,所以溫成皇后生前的起居用器也很樸素。仁宗望着愛人生前所用簡單舊物,不禁悲從中來,一口氣賞賜了許許多多的珠翠金玉給溫成陪葬。

按當時習俗,這其中的許多陪葬品要焚燒掉。看到皇帝如此大手筆的爲溫成準備陪葬品,諫官範鎮上疏說,此舉“於死無益,而於生有損”,請求罷焚錦繡珠玉等陪葬品。
仁宗皇帝不佔理,只能答應範鎮的請求。
除此之外,仁宗皇帝爲溫成皇后立忌、建陵、立廟時,均遭遇御史諫官不同程度的反對,直到溫成皇后已經去世多年,還有言官上疏“乞毀溫成廟”。
(二)
講溫成皇后的故事,意在呈現中國帝王鮮爲人知的另一面。
溫成之歿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個側面:
一則這只是皇帝的“家事”,即便皇帝在悲痛之下有稍許任性,也談不上涉及帝國的存亡興衰;
二則事由特殊,中國文化歷來尊重逝者,面對皇帝最心愛的貴妃病逝,即便基於最樸素的倫理人情,臺諫百官似乎也不該對皇帝的“不當行爲”過於苛責。
但是並沒有。自溫成皇后病逝後,面對仁宗皇帝任何哪怕細微的“越禮”行爲,御史臺諫的繩愆糾謬都會接踵而至,沒有任何含糊與遷就。
影視爽文看久了,現代人往往以爲,所謂皇帝,貴爲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可以傲睨萬物,任性妄爲。
實際上,皇帝是一件風險很高,鬧心無限,卻歡暢有限、自由有限、權力亦有限的職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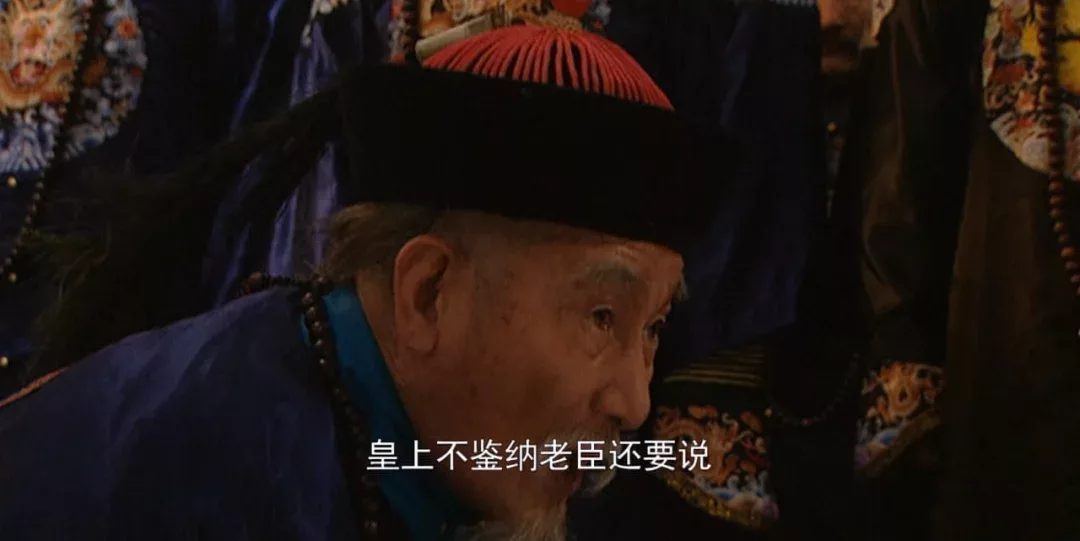
以北宋的皇帝爲例,雖然名義上皇權至高無上,但二府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在現實層面擁有參與最高決策的權力,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皇權,還擁有規諫皇帝的職責。
有宋一代,自宋太祖趙匡胤始,便立下“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者”的規矩,由此逐漸形成了寬仁民主、優假士人的政治風氣。
臺諫是大宋王朝中“分權與制衡”皇權的重要一環,北宋的御史諫官批評起皇帝來,那真是不留情面,毫不顧忌,他們對皇帝、宰相的一舉一動,可謂是虎視眈眈,任何細微的過錯都會遭到臺諫官激烈的彈劾。

面對貴妃之死,皇帝尚且有這許許多多的不自由,不暢快,那些事關國家改革和財政軍事的社稷大事,皇帝所面臨的種種掣肘與束縛,更可想而知。
(三)
仁宗時代被後來者譽爲治世的楷模,可你若站在皇帝的視角,回溯審視仁宗帝的種種工作,只會覺得各種鬧心:
朝堂上面對的永遠都是爭吵不休的羣臣,國家的內憂外患如江河般連綿不休,種種事情都等着你的指示和裁決,可偏偏你的決定,總會有人站出來表示反對,他們不僅抗議,還罵人,還PUA你。

國事羈絆重重,皇帝的私事也不得暢快,連和女朋友上牀這樣的事情,都會被諫官指着鼻子罵荒淫無道。
明道二年,垂簾聽政十一年之久的劉太后去世。仁宗皇帝終於迎來了真正意義上的親政。
沒了劉太后的監督,繼位以來“不近聲色”的仁宗皇帝,開始沉溺於美色之中,最令仁宗不能自拔的,是楊氏、尚氏兩位美人,這倆美女幾乎每天晚上都要侍寢,以至於讓仁宗這個正值壯年的小夥子,一度因縱慾過度,上朝都睏倦無神。

其實這事也好理解,和所謂的荒淫無道沾不上邊。宋仁宗當時只有25歲,這個年紀的小夥子,遇到傾國傾城的絕世佳人,那基本上就是四個字:如狼似虎。
可如此“男之常情”的帝王私事,御史臺諫表示也要管上一管,上疏規勸者衆多,也有不留情面直接開罵的。
比如滕子京(就是范仲淹千古名篇《嶽陽樓記》中提到的那位)就上疏,罵仁宗“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倦色”。
臺諫官的批評令仁宗不堪其擾,無奈之下,不得不忍痛割愛,答應將楊、尚兩位美人遣出皇宮。
聖旨下達後,尚美人哭哭啼啼地不肯走,嚷着要見皇帝,一個叫閻文應的太監上去就是一個嘴巴,如扔垃圾般將兩美人逐出了皇宮。
你瞧,堂堂天子,連自己心愛的美人都保護不了,欲留而不能。
(四)
所以後來宋神宗曾對臣子感嘆:
“朕平生未嘗作快意事。”
瞭解了這些做皇帝的“苦衷”,或許就能夠理解,爲何宋神宗當年會如此放任王安石率領“變法派”在朝堂上肆意妄爲,以種種手段排斥異己,驅逐反對派了。
因爲皇帝的手腳被千萬條無形的繩索束縛着,他太渴望“鬆綁”了。
皇帝也有七情六慾,皇帝也渴望更自由、更放縱,也渴望及時行樂。
可一個運轉良好的社會機制,必然要求帝王是不暢快的,即作爲“人”的皇帝,必須有力量制衡其慾望——如果制衡帝國統治者的力量消失殆盡,那王朝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最終的崩潰。

譬如,和相對剋制的仁宗皇帝相比,北宋亡國之君宋徽宗,就是一個更任性,更自由,更放縱自我慾望的帝王。
徽宗這個皇帝,當得可比仁宗“快意”多了。
若論“好色”,如果金國翻譯官王成棣的記錄真實可信的話,那宋徽宗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好色的君王之一。
靖康之變後,金人俘虜了許許多多宋朝王室的女眷,這些女眷被押送到金國分賞給權貴們,王成棣是押運部隊的一名翻譯官,他將一路上的見聞記錄了下來。
王成棣一路聽這些皇室女眷講述了許多皇宮祕聞,其中就記錄到:
宋徽宗五到七天,必須用一位處女,這些女孩,他每臨幸一次會給她們進一階,徽宗退位時,服侍他的宮女達到了6000人之多。

不過對於古代君王而言,好色,應該是社會成本最低、邊際效用遞減最強,對民間盤剝打擾最輕的一項“愛好”了。
作爲帝王,多臨幸幾個美女,根本構不成對帝國的威脅。古往今來認爲帝王沉湎女色導致江山易主的人,在我看來都純屬腦子進屎邏輯不清的無菌級傻帽。
因爲相對於愛錢、愛功名、愛開疆拓土、愛大興土木這些更奢侈的事物,一個皇帝再好色,也很難造成民間哀鴻遍野、家破人亡、生靈塗炭的悲慘。

士大夫們當然也知道這一點,但必須防微杜漸。因爲真正危險的,必須提防和警醒的,是帝王放任自己慾望、野心和權力的徵兆。
仍以宋徽宗爲例,在花錢享樂方面,宋徽宗的窮奢極侈也居於宋代皇帝之首。
徽宗的一大愛好是大興土木,爲了建造出全世界最奢華奇豔的園林,他專門授權朱勔(北宋六賊之一)爲自己在東南搜刮珍稀方物。朱勔爲了討好皇帝,也是不辱使命,在他的勢力範圍內巧取豪奪,中產之家幾乎都被盤剝至破產邊緣。

方臘就是朱勔“奉旨搜刮”的受害者之一。方臘其實是個小富二代,因不堪忍受朝廷的盤剝才聚衆造反。當方家這樣的富庶之家都被皇權壓榨得無法過活了,可以想象那些處於社會更底層的百姓,該是何等的悽慘。
所以方臘起義的口號之一,就是誅殺朱勔。這場起義帶有明顯的復仇色彩,凡是被方臘起義軍抓到的宋朝官吏,全都被酷刑折磨至死。
古往今來,帝王慾壑難填的背後,往往是草芥小民悲慼的呼號和血與肉的獻祭,可人的慾望哪裏有止境呢?
(五)
中國男人心裏大抵都有一個當皇帝的美夢,很多人骨子裏還覺得自己真能做成爲一代聖君。
實際上,這樣想的人往往既不瞭解歷史,也不瞭解自己。
如果立志要做一個被萬世稱頌的聖君明主,那麼皇帝這份工作就不僅僅是枯燥無味,而簡直稱得上是心力交瘁、愁腸百結、寢食俱廢的一份“苦差事”了。
要我說,普通人所夢想當的皇帝,無一例外將是世人眼中的昏君、暴君,即終日嬉戲,縱情聲色,殺伐果斷,看到不爽的人就撂一句:“朕必誅你九族”的皇帝。
而一個好皇帝,必然是“憋屈、惆悵、不快意”的。
政治家其實沒有多少任性恣情的時刻。所謂政治,想象中是縱橫捭闔,睥睨天下,其實在現實中更多是平衡、取捨、隱忍乃至退步,是不得不爲,是隻能如此,是打碎了牙齒和血吞。
一個隨心所欲、快意恩仇的皇帝,則多半是一個昏聵、暴戾的帝王。
在君權體制下,所謂的內聖外王之道,首先需要依靠帝王自身對慾望和權力的剋製爲道德基石。
而皇帝作爲一個有七情六慾的普通人,其人性中的貪嗔癡,與成爲聖君明主所需具備的“神性”天然相悖。

在此之上,德政仁君的實現,需要以種種祖訓、禮法、制度、法規及臺諫糾察機制制衡約束皇權,而君主則需要以極高的道德自省和高度的自律意志,接納來自制度、法律及士大夫等文官集團的約束、平衡與規諫。
這是一個根本性的、無法調和的矛盾。
如何讓作爲人的皇帝,超越自身的“人性”,克己復禮,抵達和接近聖帝明王所具備的“神性”,即克服皇帝的“本我”,實現“超我”,是封建帝制最大的挑戰。
昏君佞臣,向來是帝制王朝最大的危機之一。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階層,窮盡各種辦法試圖解決這一問題,設置各種機制平衡各方權力,束縛統治者的慾望和任性,皇位傳承儘可能謹慎地選擇“有德之人”……
然而歷史的演繹,卻遵循着近乎一致的劇本:
一個王朝無論曾經如何昌盛,帝制之下,它總會走向權力逐漸失衡,欲求逐漸膨脹,一切藩籬化作齏粉的那一天。

昏君,是帝制王朝必然會出現的結果。
畢竟,在至高無上的皇權加持下,一個有血有肉、有慾望、有雄心的皇帝,內心深處一個始終澎湃不息的衝動,就是打破一切藩籬,扭斷一切束縛,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任性地行使權力,貪婪地滿足個人慾望……
施行“王道”,固然可以名垂青史,但是作爲肉體凡胎的一個具體的人,作爲手握皇權的一代君主,沒有什麼比行“霸道”更爽的事情了,做一個所謂的“昏君”,實在是太舒服太肆意太暢快太有吸引力了。
生而爲人,誰不想簡簡單單地做個昏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