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官斷十條路。”,這句話被廣爲流傳,一句話能夠一直被大家記住,往往有兩個可能,一種是這句話是官方要求民衆知道的,比如“君權神授”、“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等,這些言論不管民衆是否認可,但是官方要求你只能記住。
另外一種是不需要官方強制,卻能讓大家記住的話,那隻能說明這句話有理,或者說他說出了社會現狀,並得到了民衆的一致認同,成爲了大家的共識。而“官斷十條路”能被大家熟知,也就是因爲他說出了古代社會的現實。
那爲什麼古代官員能斷十條路呢?就是因爲古代大量的法律條文都有模糊不清、語義含混的狀態。這種現象並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於古代社會的政治土壤之中。從本質上來說,這往往是統治者精心設計的結果,背後隱藏着複雜而深刻的政治權謀與考量。
比如,村民張三因偷了鄰居的一隻雞而被告到衙門。按照古代的律法條文,對於盜竊行爲的定罪是依據所盜財物的價值來判定的,處罰方式包括罰金、笞刑、流放等多種形式。然而,法律條文在此處卻存在關鍵的模糊點——沒有明確規定偷盜價值多少財物應對應何種具體刑罰。
法律僅僅寫了情節“較輕的”、“比較輕的”、“較重的”等字樣,可是偷多少錢財算是“較輕的”呢,又多少是“較重的”呢?這樣一來就出現了模糊空間,而這種模糊性就將裁決的大權交到了審訊官員的手中。官員在處理這起案件時擁有極大的自主操作空間。
如果張三是官員的親戚,或者官員收了張三的好處,那他完全可以從輕發落張三,將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許只是簡單地警告張三,或者象徵性地罰一點小錢,便草草結案。
可如果張三和官員有過嫌隙,那麼他也有權力對張三進行重判。他可以將張三的這一小小盜竊行爲的罪責無限放大。可以聲稱一隻雞雖然看似價值不大,但卻關乎民風,關乎道德倫理,用道德這個殺人不見血的利劍,將張三從重治罪。

在這種情況下,張三的命運完全被官員掌控,此時,百姓所畏懼的對象就不再是抽象的法律條文,而是執行法律的官員。他們深知,自己一旦觸犯了法律,哪怕是輕微的違法行爲,最終的結果都取決於官員的個人意志。
可如果法律條文是極其詳細的,情況則會截然不同。如果法律明確規定了偷盜財物價值的具體量刑標準,比如,偷盜價值在一兩銀子以下的財物,處以罰金若干;價值在一兩到三兩銀子之間的,處以笞刑多少下;價值超過三兩銀子的,判以流放某地。
那麼,當張三偷雞這一行爲發生後,無論是張三本人還是審訊的官員,都能清楚地知道應該適用何種刑罰。這樣一來,官員便失去了可以操作的模糊空間。他們無法再根據自己的意願隨意地對百姓從輕或從重處罰。
每一個判決都必須嚴格依據法律條文來執行,沒有了自由裁量權所帶來的灰色地帶。對於百姓而言,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行爲的後果,在犯法時能夠有法可依。這看似公平合理的狀態,卻觸動了古代統治階層的敏感神經。
因爲,對於統治者來說,他們都希望自己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權力的體現就在於掌握別人的生殺大權!有能力讓別人做他們不喜歡的事情,而詳細的法律條文恰恰束縛了統治者的權力,他們需要法律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但不需要完善的法律限制自己的權力!
統治者深知,官員權力的一部分來源於對法律執行的自由裁量權。這種權力讓官員在百姓面前擁有絕對的威嚴。當官員能夠決定百姓的生死榮辱時,百姓自然會對官員敬畏有加。而這種敬畏又會通過官員這一階層,最終傳遞到統治者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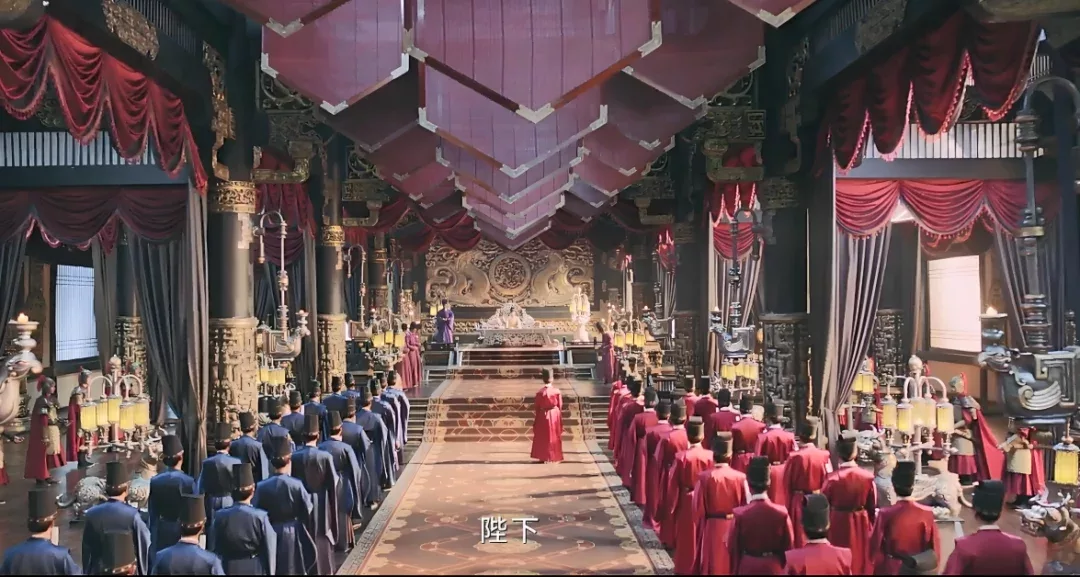
於是,通過故意製造法律的模糊性,讓法律條文存在模糊空間,統治者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官員和百姓。官員因爲擁有較大的權力而對統治者感恩戴德,同時也會更加忠誠地爲統治者服務。而百姓則因爲對法律執行的不確定性而心生畏懼,不敢輕易觸犯法律,更不敢挑戰統治者的權威。
可以說,古代法律條文的模糊不清,從根本上增加了人治的權力。在很多情況下,人治的力量遠遠大於法律的力量。官員在處理案件時,往往不是依據法律條文的明確規定,而是根據自己的主觀判斷、個人利益或者上級的暗示。這種人治的現象在古代社會屢見不鮮。
當人治大於法治時,老百姓會更加畏懼執行法律的人。他們知道,在法律面前,自己的命運更多地掌握在官員手中。這種畏懼心理會讓百姓在行爲上更加謹慎,但同時也讓他們處於一種極度不安的狀態。
而對於統治者來說,這種讓百姓恐懼、不安的狀態正是他們所期望的。百姓的畏懼心理會轉化爲對統治者的順從,這樣他們就可以更好地拿捏百姓,讓百姓乖乖地成爲自己燃料的同時,還要歌頌統治者的偉大!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皇帝用來統治臣民的一種專制工具。中國古代社會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專制與人治”的社會。在這種社會形態下,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是爲了維護皇帝的統治。
皇帝或統治階層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隨時制定、修改或廢除法律。法律沒有獨立性,它完全從屬於統治者的政治目的。比如在明朝時,江南百姓懷念張士誠的輕徭薄賦,朱元璋知道後大怒,直接對該地區徵收高達20%的田賦,作爲懲罰性措施!

在古代那種畸形的社會環境中,法律的存在形式和功能都發生了扭曲。它不再是公平正義的象徵,而是權力的附庸。法律條文的模糊性是這種畸形狀態的外在表現,人治和專制則是其內在的核心本質。這樣一來,百姓就成爲了法律模糊性的最大受害者,他們只能在專制與人治的陰影下艱難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