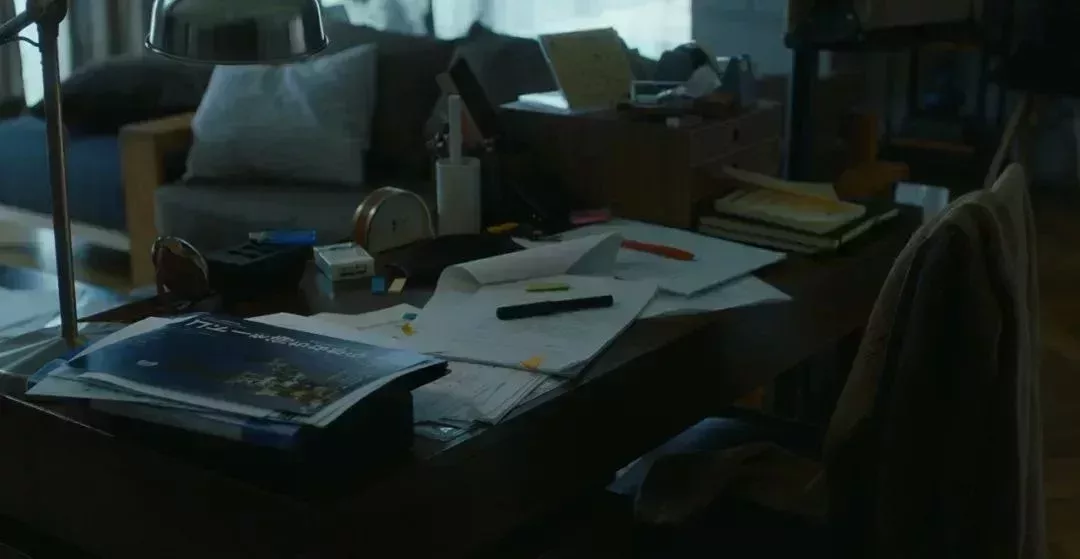
當下生活處於激烈的變化中,既往的確定性不斷受到侵蝕,爲在流變中尋找生活的自主感,人類學家項飆和哲學學者王小偉進行了一次線上對談。
項飈因“附近性”的概念爲大衆所熟知。王小偉則於近期出版了隨筆集《日常的深處》,以技術哲學爲基底,討論人與物品與生活的關係。他們試圖從哲學與人類學的交叉中尋找思想資源,來應對劇變的挑戰。
德國馬普所的段志鵬主持了本次對談,蔣文丹對錄音進行了文字整理。牛津大學的陳志峯參與了對談。篇幅所限,文字資料整理自部分座談內容。
01. 宏大敘事
“有些宏大敘事的結構是固定的,僵化的,你自己的經驗是沒辦法回視它的,而要受到它的擺佈。”
王小偉:項老師一直願意朝向公衆說話,關注年輕人的遭遇、年輕人的焦慮和無意義感等生命力萎縮的情況。您談論“附近”比較多,給人感覺排斥宏大敘事,也和宏大的理論本身保持了距離。似乎年輕人要擺脫焦慮,重獲生命感不太需要大的哲學和人類學理論,而是要關注自己的“附近”。這起碼是第一步?
項飆:如果我們把宏大敘事理解爲一個穩定的象徵性結構,一系列的牢固觀念,一個是在你的經驗之上、經驗之外的意義的話,那當然要擺脫這個結構。這種結構是固定的,僵化的,你自己的經驗是沒辦法回視它的,而要受到它的擺佈。

第三種宏大敘事是更具反思性,其根本是要問我們究竟在幹什麼?像我們所要做“共同焦慮”的人類學研究。如果沒有宏大敘事,這個研究就不太成立。在這個點上,我特別希望向哲學界學習新東西。
比如李澤厚的工作,他是中國20世紀後半期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李澤厚是宏大的,抽象的,他從美學出發,將美感、情緒、體感,跟康德、馬克思等結合,提供了獨特的主體性理論。
李澤厚可能是80年代影響最大的一個學者。他的影響力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去看是有原因的,因爲李澤厚給大家提供了一個視角,這個視角有社會和政治含義。你必須有宏大敘事的視角才能理解李澤厚的思想爲什麼有那樣的影響力。
同樣的,理解整體性焦慮也需要宏大敘事。年輕人覺得不爽,我們要問是什麼東西讓ta感到不爽?怎麼理解ta的不爽,ta怎麼表達不爽。對不爽的不同表達方式分別體現了什麼樣的權力結構,自我認知等等。
你不斷追問,最終我們需要一個潛在的宏大敘事來幫助理解。我覺得必須有個宏大敘事才能知道我們今天在歷史中處於哪一刻,我們在幹什麼,這樣才能深刻理解年輕人具體的困惑。
比方說年輕人的“不配感”,你如果只做實證的話,講不清楚的。ta怎麼會覺得不配呢?有些東西明明是自己考上的,經過很多努力,ta反而覺得自己不配。這反映了對自我存在的一個認知。
這不僅是個心理過程,這是ta對自己長期的成長經驗的總結,很可能也包含了ta父母的成長經驗和心態。這需要通過哲學思考把這個現象轉變爲一個更大的議題。

王小偉:所以您排斥的是作爲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因爲我們沒法回望,對它無能爲力。第二種宏大敘事是瑣碎的,是一種日常講述習慣。第三種是反思性,歷史性地,要去問我們在歷史中處於什麼位置。這樣纔能有效回應現實中具體的問題。
李澤厚所處時代的宏大背景是一個開放的,試圖融入世界文明的中國。重新發現中國人的主體性是他在那樣一種宏大背景下的系統性嘗試。
趙汀陽是李澤厚的學生,他近來討論比較多“後人類”問題,其實就是科技時代人的主體性流變的問題。我們正在一起寫一組後人類的稿子。
他對於深度科技化時代每個人所遭遇的這種虛無感、無意義感,都感同身受。他似乎認爲科技的無處不在會造成道德的崩壞。他似乎也操持一種理性人文主義的態度,熱烈地希望通過弘揚理性來阻止墮落。
不過宏大敘事的哲學計劃今天不時興了,像黑格爾那樣的歷史哲學,包括李澤厚那樣的主體性哲學可能都很難引起興趣了。
02. 總體化焦慮
“年輕人今天的問題往往呈現爲一種‘總體化焦慮’,甚至渴望讓世界毀滅”
項飆:我們沒有雄心去給大衆提供一個宏大圖景,但是我們自己腦子裏是有個大的圖景,這是給自己用的,幫助我們去理解具體的社會問題。無論如何我們都需要一個總體性(totality)的視角。
比方說馬克思主義就通過商品的概念把所有社會關係連接在一起。盧卡奇也注重總體性的概念,認爲資產階級學說越分越細,每一個細節都是正確的,放在一起就錯了,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看到全局。
總體性和總體化不一樣。總體性是一種分析方式,看到多樣事物之間的聯繫。總體化是情緒性的,把所有事情看作一團。
年輕人今天的問題往往呈現爲一種“總體化焦慮”,甚至渴望讓世界毀滅,覺得整個世界就是這樣的不堪,就是很不公平。這種焦慮的表現很絕對化。
最後這個總體化的焦慮又變成一個既定的象徵結構、象徵秩序了。你也沒辦法回望它了,總體化焦慮還是帶來了無力感,焦慮完你什麼也沒有幹。

王小偉:您似乎有兩個企圖。一是朝向實踐,渴望年輕人找到某種整全感,這種整全感能夠導致具體的行動,提高人的生命力。另外一個可能是哲學的,是一個本體論工作。
歐陸和分析哲學家都有自己一套本體論方案。在深度科技化時代,像大衛·查莫斯這些人也會提出一些新的方案(例如比特本體論)。我不確定哲學本體論是否能幫助我們緩解焦慮,應對虛無。在本體論層面,我不知道人類學究竟要走多深,它要變成哲學嗎?
項飆:總體性不是我要對世界做出一個判斷,它不是一個斷言(assertion),主要不是一個哲學本體論的描繪。
在人類學裏,總體性是我的一個實證觀察:年輕人自己在生活裏面有着關於總體化的想法和說法,例如渴望世界毀滅。我覺得要對抗總體化焦慮,不是說要回到歲月靜好,關注自己一畝三分就能解決的。
我想從實證角度來考察一種總體性的世界觀,也就是觀察年輕人他們怎麼看世界的。比方說,通過對年輕人的生活經驗和他們的生活意識進行民族誌書寫,讓他看到具體的事物,並非獨立存在,截然分割的,它有各種各樣的豐富的聯繫。
比如說教育對生命力的影響。你可以把教育理解爲學習知識,理解爲社會馴化,理解爲阿爾都塞所說的意識形態裝置,理解爲社會關係的再生產,理解爲人的工具化,都可以。
如果把教育理解爲對生命力的一種運用,問爲什麼今天的教育讓年輕人覺得沒生命力,要深挖這個問題,就會進入一種潛在的“總體性”的分析方式。
在學校裏我們不僅是在學知識,老師看我的眼神是怎樣的,同桌怎麼對我說話,考試前的緊張,考試後的釋然等等都是聯繫在一起的。這個聯繫在一起不是本體論意義上的,它指的是教育制度和環境的設置。
教育作爲一個生存活動如何對我們生命力造成影響,這是我們感興趣的。一個學生感受到的生命的萎靡包括兩部分。一個是最直接的反應,比如ta們覺得累了、麻木了,這是經驗基礎,第二要看ta怎麼處理自己的經驗,這會需要用到語言、概念。

王小偉:比如說年輕人覺得痛苦來自內卷,“內卷”就是一個去解讀自己生命經驗的概念。內卷、焦慮,包括抑鬱現在都變成了泛在概念。二十年前這些概念並不用來解讀人的生命經驗,內卷聞所未聞,焦慮和抑鬱還是精神診斷詞彙。日常生活裏我們會說競爭激烈、有點緊張、有點不開心。
你覺得普遍性的,總體化焦慮和這些詞彙的發明和使用,甚至是誤用有關係嗎?
項飆:顯然是有關係的,有一種說法認爲這些詞彙強化了抑鬱。但這些語詞在這個時候出現,它本身是有意識地實踐的結果。李澤厚也講過究竟是“語言說我”還是“我說語言”。其實兩邊都說得通。但在當下中國語境裏,我覺得要更加強調“我說語言”,強調語詞的形成是人們行動和選擇的結果。
王小偉:我認同這個取捨。回到我們之前的討論,您認爲有沒有一種宏大的敘事作爲背景,導致了年輕人選擇這些詞彙來去解讀自己的生命體驗?
項飆:任何事情都有背景,問題是怎麼樣去處理這個背景?
李澤厚後期有歷史沉澱說,提示要在個體的主體性裏面看到歷史的沉澱。比方說焦慮,我們知道青年人的焦慮跟這兩年的經濟下行有關,但這個是短期的,焦慮也跟他的小時候成長經歷有關,這是中期的,但同時也跟一些創傷通過代際無意識地傳遞也有關,這是長期的。
孩子那麼焦慮是因爲父母焦慮,父母焦慮是因爲父母小時候的經歷,這會無意識地傳遞給孩子。比如父母小時候資源缺乏,現在看到孩子的一步走錯,就認爲是災難性的。
一個20歲的人自殺可能跟中國近100年的歷史有關,跟昨天考試失敗有關,也可能跟20年的成長經歷有關。關鍵是我們用什麼方式把這樣多層、多面的背景講出來。
王老師,你現在是以思想隨筆的形式來表達,也通過公共媒體對日常生活和自己的生命經驗進行總結。我感到一到生活經驗,好像我們的思考就會被生活經驗本身淹沒,很難作爲思想主體對生活經驗進行重新整理。
你個人感覺到現在走出一種以生活經驗爲底子,但又超出它,回頭能再照亮生活的思考方式嗎?
王小偉:觀察日常經驗肯定滲透着某種哲學視角。它不是寫日記,不是對自己的生活的詳盡記錄。它是通過特定的視角來裁切生活,然後把裁切成果再映射到自己的生命體驗當中去。我一直在試圖尋找自己的人格和工作統一起來的辦法,傑出的工作可能都是給生命寫注。
項飆:你覺得自己和身邊朋友處在一個什麼樣的階段?覺得找到一個這樣的理想模式了嗎?
王小偉:沒有。青年學者一個重要主題是在學院體制內儘快錨定資源,通過職稱晉升獲得穩定的生活,這基本上是擺脫屈辱感的活動,很少有人能從生命體驗出發做研究。
03. 奪回日常,喚起感受
“日常生活在當下生活當中被擠壓、邊緣化,被認爲是無關緊要的……”
王小偉:在交談中,我注意到人類學和哲學研究方法差距還是很大的。哲學不太需要實證研究,更多在嘗試建構敘事。但人類學似乎很不一樣,要做很多田野。我更多的是做技術現象學的工作,試圖去澄清當下生活困境的宏大背景。
當代生活的宏大背景是無處不在的技術裝置和伴生的技術狂信。不少人相信科技會一直進步,物質會極大豐富,幸福將不期而至。哲學家對此很謹慎。海德格爾認爲技術是科學的前提,我們必須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可以數學化、力學化的東西,才能把世界表徵成爲科學研究的對象。
他已經預見未來世界是以計算(強控制)、快速(不等待)和巨量(無個性)爲突出特徵的時代。所有的意義都會被剝奪掉。人和一切存在者都變成“持存”,被任意擺弄。
科技會帶來一種徹底的遮蔽,人們無法想象另外的存在方式。正像孫周興解讀的那樣,真正的虛無主義只有一種,那就是技術虛無主義。
在這個宏大圖景裏觀察當下的生活,我們幾乎沒有辦法再去理解什麼是神聖的、超越的、模糊的,我們只有一種定量的、計算的、控制的生活方式,這是造成總體化焦慮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切都是權力意志,工具理性的彰顯。
當代社會中,人在家庭、公司、社交生活中都感到被“挪用”,要被用來做那些ta沒有熱情事。而愛、親密關係,以及藝術這種無法計劃、擺弄、榨取的東西變得稀缺,或者乾脆不值一提。

項飆:你有沒有想過在中國當下的情況下,怎麼繼續發展海德格爾的想法。
王小偉:受到海德格爾哲學和項老師有關“附近”討論的啓發,我現在特別關注生活的日常性,寫了《日常的深處》。
日常生活本來是生活世界基質性的東西,它對應的是工作性的活動,當代工作已經完全被現代技術邏輯籠罩,都是高度目的化,工具化的。日常生活卻是沒有目的性的,不需要考慮投入產出,不需要量化管控的。它粗糙、模糊,並且帶有很強的隨機性和任意性。
日常生活在當下生活當中被擠壓、邊緣化,被認爲是無關緊要的,但其中包含緩解技術獨裁的解藥。我想做的工作是奪回日常生活,通過日常生活把生命力充實起來。
有些事很容易操作,比如花五分鐘去樹林裏面枯坐,養一條魚、種一盆薄荷等等。這些在海德格爾看來可能是一種非本真的“常人”狀態,但今天格外重要。
項飆:那你需要引用很多腦科學或者心理學的研究來說明你的觀點嗎?比如看看神經科學對在森林裏無目的地坐一下會不會產生某種心理效果?你怎麼去論述日常生活跟生命意義的關係?
王小偉:這是要尤其警惕的。一旦使用腦科學去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你就把日常生活技術化、工具化了,日常也就變成了工作,要在其中謀求效益。奪回日常是要提高人的感受性,而不是理性。
項飆:所以奪回日常的作用不是勸說,是喚起。
王小偉:是的,是要喚起人們對存在的感受,保持一種在技術性生存之外維度,獲得一種適度的意義感,不至於陷入一種“消極的虛無”。
尼采經常談論虛無,他區分了需要強意義的弱者和需要弱意義的強者。需要很強意義感的人,ta要把自己的生命工具化。
尼采說基督徒把此生看作是走向天國的步驟,這是把生命工具化了,索要一個強意義,他們都是弱者。強者有不一樣的時空感,它不關注外部,不把自己的生命當作工具,強者肯定生命本身,所以只需要一個弱意義——日常或許就是一種弱意義。承認自己不卓越,接受並擁抱日常,從中找到價值感,這反倒需要更強悍的生命力。
當然我們也沒法提供一個幸福人生的操作手冊,一旦手冊化它就又會變成一種技術——焦慮去除術。
項老師的工作其實看起來也很像一個行爲藝術。比方說《把自己作爲方法》,這絕對不是一本幸福生活操作手冊。書裏並沒有直接的訓誡指導,和操作步驟。它更多的是在對話構造一種指引。這本書的寫作方式很像海德格爾的《鄉間路上的談話》。

項飆:這個太有意思了,在中國傳統裏有這種做法嗎?
王小偉:我的閱讀非常有限,但似乎前現代的東西多少都保留一些神聖性、超越性,不可言說的神祕性。比方說“道”這個概念就保持着一種不可說性,因此具有詩性。
它沒有辦法通過說明文來澄清,只能通過誦讀來體會。回到日常生活,我有個感受,似乎八九十年代中國的大學裏麪人們都愛談論詩歌,演奏民謠。
今天的大學裏你幾乎看不見詩歌,每個人都在想着發論文。現在詩歌喪失了召集的能力。詩歌就是一種邀請性和指引性的語言,詩歌天然地拒絕清晰。
項飆:學生不寫詩歌了,都在想考研這件事,在一個層面上我們可能認爲ta們被工具理性佔據了。但ta心裏是不高興的,是覺得壓抑的,所以ta的自覺意識是有的。我們去觀察這個意識,從一個啓蒙理性的角度來看,這個意識活動是非理性的,所以ta沒有完全被工具理性所征服。
年輕人感到的其實是生活不可測,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技術沒有給ta們帶來確定性。ta覺得自己的一切都是很不可測,個人處於一種不但非理性而且不合理(irrational and unreasonable)的境遇中。
這種非理性指的是從制度設計角度上是不合乎邏輯、沒有效率的(irrational),比如內卷;不合理是指在倫理上是無理由的(unreasonable)。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大家感到的不確定性就與政治經濟學相關,不僅僅是因爲技術造成的。它是一個社會結構造成的問題,是可以言說且必須言說的,不言說就走不出困境。
生活不可預測,如何能在不可預測的生活之流裏面來做總體性分析呢?這個時候,每一刻又需要清晰語言,否則的話,難道遇到問題我們就去寫一首詩嗎?當然那也可能是一種辦法,但我們的進路還是非常理性主義的進路。
王小偉:所以您對海德格爾式講的迴歸藝術,或者我提到的迴歸日常這套解決方案並不完全滿意。
項飆:當有人把槍拿出來的時候,你該怎麼回應?在黑森林裏面行走,在林中枯坐是不能回答槍口下的逼問的。你要有一種古典意義上的理性,加之再回到人本主義,這個人本主義就是早期馬克思人本主義,這樣或許才能解決問題。
王小偉:項老師,我隱約看到了一種世界圖景的根本差異。在理性和感性之間,我們似乎有不同的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