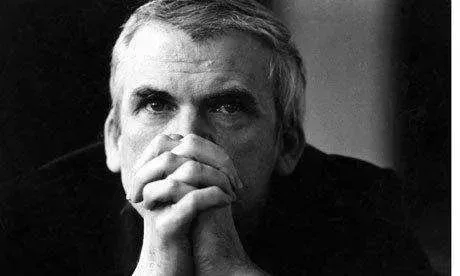
選自《巴黎評論·作家訪談》,美國《巴黎評論》編輯部
《巴黎評論》:
你在《新觀察家》雜誌發表的一篇長文讓法國人再次發現了布洛赫。你高度稱讚他,可你同時也是批判的。在文章結尾,你寫道:“所有偉大的作品(正因爲它們是偉大的)都部分地不完整。”
昆德拉:
布洛赫對我們是一個啓發,不僅因爲他已實現的,還因爲所有那些他打算實現卻無法達到的。正是他作品的不完整能幫助我們明白對新藝術形式的需求,包括:第一,徹底地去除非本質(爲了捕捉到現代世界的複雜性而不用喪失結構上的清晰);第二,“小說的旋律配合”(爲了將哲學、敘事、理想譜進同一支曲);第三,尤其小說體的隨筆(換言之,保留假想、戲謔或反諷,而不是傳達絕對真實的信息)。
《巴黎評論》:
這三點似乎充斥了你的整個藝術規劃。
昆德拉:
要將小說變爲一個存在的博學觀照,必須掌握省略的技巧,不然就掉進了深不見底的陷阱。穆齊爾的《沒有個性的人》是我最愛的兩三本書之一。但別指望我會喜歡它巨大的未完成的部分!當你完成了閱讀,應仍能記得開頭。如果不,小說便失去了它的形,它“結構上的清晰”變得含糊。
《巴黎評論》:
《笑忘錄》由七個部分組成。如果你處理它們時用的不是一種這麼省略的方式,你可能會寫七部不同的、完整的小說。
昆德拉:
可如果寫了七部獨立的小說,我會失去最重要的東西:我將無法在一本單獨的書裏,捕捉到現代世界人類存在的複雜性。省略的藝術絕對必不可少。它要求一個人總是直奔主題。我的目的是:摒棄機械的小說技巧,摒棄冗長誇張的小說文字。
《巴黎評論》:
你提到的旋律配合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沒有這麼明顯。
昆德拉:
那是我的目標。那兒,我想要夢、敘述和思考以一條看不見、完全自然的水流匯聚成河。但小說復調的特點在第六部分很明顯:斯大林兒子的故事、神學的思考、亞洲的一起政治事件、弗蘭茲在曼谷的死、託馬斯在波西米亞的葬禮,都通過同一個永恆的問題聯繫起來——“媚俗是什麼? ”這個復調的段落是支撐整個小說結構的支柱,是解開小說結構之祕密的關鍵。
《巴黎評論》:
通過召喚“一篇尤其小說體的散文”,對《夢遊者》中出現的有關價值觀墮落的散文,你表達了幾種保留態度。
昆德拉:
那是一篇非常漂亮的散文!
《巴黎評論》:
你對它成爲小說一部分的這種方式有過懷疑。布洛赫沒放棄他任何的科學語言,他以一種直白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而不是藏在他的某個角色之後——像曼或穆齊爾會做的那樣。那不正是布洛赫真正的貢獻、他的新挑戰嗎?
昆德拉:
確實如此,他對自己的膽識很瞭解。但也有一個風險:他的散文會被看成、被理解成小說意識形態的關鍵,理解成它的“真理”,那會將小說的剩餘部分變成一種思想的純粹說明。那麼小說的平衡被打亂;散文的真理變得過於沉重,小說微妙的結構便有被摧毀的危險。一部沒有意圖要論述一種哲學論題的小說(布洛赫憎恨那一類的小說!)可能最後會被以同樣的方式解讀。一個人如何將一篇散文並人小說裏?有一條基本原則在心很重要:思考一旦囊括進小說的身體,本質就會起變化。小說之外,一個人便置身於一個振振有詞的王國:每個人的哲學家、政治家、看門人,都確信自己的言論。可小說,是一塊地盤,在這兒,沒有人下斷言;它是娛樂和假想的國度。小說中的思考是假定的,這由它的本質所決定。
《巴黎評論》:
你曾將《笑忘錄》描述爲一部“變奏曲式小說”,但它還是一部小說嗎?
昆德拉:
沒有情節的統一,這就是爲什麼它看上去不像一部小說的原因。人們無法想象一部小說沒有那種統一。就連“新小說”的實驗也是建立在情節(或非情節)的統一上。斯特恩和狄德羅樂於將統一變得極其脆弱。雅克和他主人的旅程在《宿命論者雅克》中佔較少的篇幅;它不過是一個喜劇的託詞,中間可以融人趣聞、故事、思考。儘管如此,要讓小說有小說的感覺,這一託詞、這一“框架”是必需的。《笑忘錄》中不再有任何這樣的託詞,是主題的統一和它們的變化給整體以連貫性。它是一部小說嗎?是的。一部小說是通過虛構的角色,對存在進行的一種思考。形式是無限的自由。縱觀小說的整個歷史,它從不知如何利用自己無盡的可能;它已錯失良機。
《巴黎評論》:
但除了《笑忘錄》,你的小說同樣建立在情節的統一上,儘管《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確是更鬆散的一類。
昆德拉:
是的,但別的更重要的統一方式完整了它們:相同形而上問題的統一、相同中心思想的統一,還有變化(比如,《告別圓舞曲》中父權的中心思想)的統一。但我尤其要強調,小說首先是建立在許多基本詞語之上的,就像勳伯格的十二音列。在《笑忘錄》中,詞列如下:遺忘、笑聲、天使、“力脫思特”、邊界。在小說的推進過程中,這五個關鍵詞被分析、研究、定義、再定義,因而轉變爲存在的類別。小說建立在這幾種類別之上,如同一座房子建立在它的橫樑之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橫樑是:重、輕、靈、肉、偉大的進軍、狗屎、媚俗、熱情、眩暈、力量和軟弱。因爲它們明確的特徵,這些詞不能被同義詞取代。這總是得一遍又一遍地解釋給譯者聽,他們——出於對“優美文體”的考慮——企圖避免重複。
《巴黎評論》:
關於結構上的明晰,所有你的小說,除了一部之外,都分爲七章,這給我很深的印象。
昆德拉:
當我完成我的第一部小說《玩笑》時,它有七個章節,這沒什麼好驚訝的。接着我寫了《生活在別處》。小說就快要完成時有六章,我覺得不滿足,突然有了一個想法,要將一個發生在男主人公死後三年的故事包括進來——也就是說,在小說的時間框架之外。現在這是小說七章中的第六章,叫《中年男人》。小說的結構一下子變得完美了。後來,我意識到這第六章,奇怪地與《玩笑》的第六章(《科斯特卡》)相似。
《巴黎評論》:
但爲什麼你在完全不爲了娛樂的情況下,爲小說選擇了鬧劇的形式?
昆德拉:
但它是一種娛樂!我不理解法國人對娛樂的輕蔑,爲什麼他們對“消遣”這個詞感到如此羞愧。有趣比無聊冒的風險少。它們要冒陷入媚俗的危險,那些對事物甜美的、謊話連篇的裝飾,浸泡着玫瑰色的光暈,就作品,如艾呂雅的詩,或伊託·斯高拉最近的電影《舞會》(它的副標題可以是“法國媚俗的歷史”)也如此。是的,媚俗,而非娛樂,是真正美學的災難!偉大的歐洲小說從娛樂起家,每一個真正的小說家都懷念它。事實上,那些了不起的娛樂的主題,都非常嚴肅——想想塞萬提斯!在《告別圓舞曲》中,這個問題是,人類值得在這個地球上生存嗎?不應該有個人“幫助地球逃脫人類的魔爪”嗎?我這輩子的渴望是統一問題的極端嚴肅與形式的極端輕薄。這不是一個純粹藝術上的渴望。一種輕浮的形式,和一種嚴肅的主題,兩者的結合立刻使我們的戲劇——那些發生在我們牀笫間,也發生在歷史偉大舞臺之上的,和它們可怕的無意義露出真相。我們經歷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巴黎評論》:
因此你也可以用你最近一部小說的名字命名《告別圓舞曲》?
昆德拉:
每一部我的小說都可以叫做《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或《玩笑》 或《好笑的愛》;名字是可以互換的,它們反映了困擾我、界定我,同時也限制我的一小部分主題。在這些主題之外,我沒什麼可說,也沒什麼可寫的。
《巴黎評論》:
你的小說中有兩種寫作的典型:第一,復調,將異類元素統一進建築於數字七的結構中;第二,鬧劇,同類的、戲劇的,避開不可能性。在這兩種典型之外,還會有另一個昆德拉嗎?
昆德拉:
我總是夢想某些美好的意外的不忠,但我還未能從自己重婚的狀態中逃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