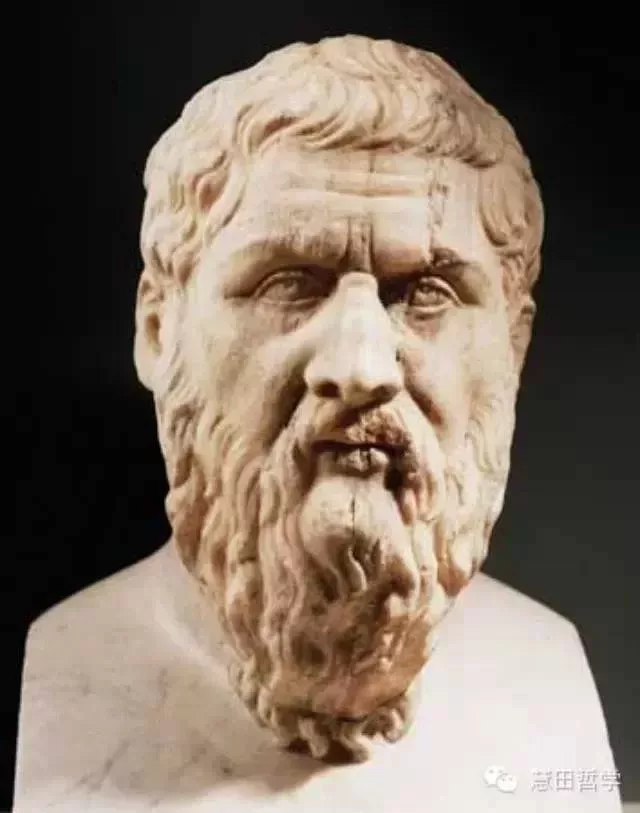
黑格爾在其哲學史中,出於自己體繫上的需要,曾顛倒地將後起的埃利亞派放在赫拉克利特之前來講述,理由是:
埃利亞派的“一”或存在的原則是哲學思維邏輯上的開端,赫拉克利特則代表“變”這一更高的思維階段;這一次序也與邏輯學開端的次序(有-無-變)相吻合。但事實上,“變”的思想在人類思維發生史上遠遠早於“存在”和“非存在”、“有”和“無”的思想。
早期希臘哲學之所以要爲世界尋求一個不變的始基,無非是爲了要把握自然萬物的變。當赫拉克利特說“萬物皆變”的時候,他實際上並沒有超出、而只是明確表達了米利都派所早已知道的思想:
所謂“無定形”的東西,無非是變化的東西,水、氣等等都是善變的東西。在赫拉克利特之前,全部哲學努力都是要對變化的東西加以規定,把它固定和把握在語言、概念之中。
儘管在黑格爾的時代,“一切皆變”是一個極其大膽的思想,因爲當時統治着人們頭腦的是機械論物理學和傳統神學的世界觀;但在古代人心目中,這卻是一個樸素的真理,它在各民族最早期思想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其生動的表述。因此,將“變”置於有、無範疇之後,認爲這是一個無條件地更高級的思維階段,這種做法似乎顯出黑格爾的某種針對性。
但赫拉克利特的確有其偉大的貢獻,這種貢獻不在於他提出了一個單純的“變”作爲哲學術語(當然這也不是毫無意義),更重要的是他對這個“變”的具體闡述和理解真正達到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
初看起來,赫拉克利特把變作爲萬物始基“火”的原則,這與過去將“無定形”作爲水、氣的原則沒有什麼兩樣,仍然是用感性自然來說明感性自然;然而更仔細的考察可以發現,他與米利都派已有了本質的差異,他不再去尋找一個“無定形的東西”充作世界的本原(在這方面,阿那克西米尼的“氣”已經走到頭了),他要找的是一個既是無定形、又能自己給自己定形並能給他物定形的東西,以克服米利都學派無法解釋萬物變化的成因這一缺陷。
這個東西在自然界只能是火。火就是有定形和無定形的內在的統一。因此,與米利都派的“無定形”相比,赫拉克利特對“變”的理解已不是盲目、被動的可塑性,要靠外來的力量來給它定形,而是能動的塑造或創造本身,它具有自身的規律、尺度或分寸:
“這個世界對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創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創造的,它過去、現在和未來永遠是一團永恆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燒,在一定的分寸上熄滅”。
火的特點就在於它是自己運動(並因而推動萬物)的,它可以視爲“作爲變的變”,因此它比“氣”更類似於人的靈魂和能動的精神;而它之所以能自己運動,就在於它具有自身的規律和尺度,自己的自我定形的“分寸”,這就是所謂“邏各斯”。
從哲學語言的層次上看,邏各斯的提出是一個比火、比“變”的表述更爲重大的事件。邏各斯就是規律,是變化的尺度,是變中之不變;它顯然是一種關係,但已不是抽象的數或量的關係,是質的關係,是兩個在性質上不同或相對立的東西統一成一種新質,它不像兩個數相加成一個數那樣在同一個質的層次上平靜地延伸,而是顯現爲整個世界豐富多彩、充滿矛盾鬥爭的流變不息的生動圖景;
而在一切對立面的統一關係中,最基本、最普遍的就是存在和非存在的統一:“我們走下而又不走下同一條河,我們存在而又不存在”。
似乎可以認爲,是赫拉克利特,而不是埃利亞派,才第一次將存在和非存在引入哲學思維,將它們看作是變本身的兩個環節,將它們的關係看作是變化的規律、尺度和邏各斯。從歷史上看,存在和非存在在古希臘是從變的概念中分析出來的,而不是通過對存在和非存在的綜合得出了變的概念。
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概念,正是在這種尺度、規律的含義上,最後演變成了“理性”的意義。這一演變過程是很使人感到興趣的。這首先涉及到 λόγος 這個詞的詞源。現代的研究者對此有各種不同的解釋。
基爾克認爲,λόγος 的詞根是 λɛγ,原有挑選、選擇之義,由此引申出計算、尺度、比例和規律的意思。這種解釋當然有利於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追溯到畢達哥拉斯的數學原則,也頗符合當代哲學中科學主義的思路,從某方面說,也不是沒有道理。
但這種解釋遭到了海德格爾的強烈反駁,指出這些侷限於“科學的語言用法範圍之內”的解釋是自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以來對於 λόγος 本來含義的“掩蔽”。
海德格爾則認爲必須將 λόγος 與 λɛγɛlv(說、展示)聯繫起來,它表示“說出”或“展示出”,同時還表示“被展示者”,只有在這種意義的基礎上,λόγος 才能被理解爲理性、根據、關係等等。範明先生在《希臘哲學史》中搜集了《希英大辭典》和格思裏《希臘哲學史》關於邏各斯一詞的各大的十種含義。
初看起來,這些含義使邏各斯一詞顯得撲朔迷離,但仔細分析一下,還是可以看出這些含義所共有的某種特點,要言之,不外兩點:1.它是人類的一種精神活動;2.它不是純主觀的活動,而是有客觀效準的活動,是展示給人看並能得到別人同意的活動。
赫拉克利特多次明確強調,邏各斯不是個人的東西,而是每個人都具有的人人共同的東西,邏各斯是“一”。他甚至要求人們:“不要聽我的話,而要聽從邏各斯,承認一切是一纔是智慧的”。
那麼,這種“既有主觀意義也有客觀意義”的東西是什麼呢?是語言,或話語。語言本質上是這樣一種東西:
它既是主觀意謂的表達、展示,又是展示出來的客觀的東西,即人人接受的尺度、規律。語言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只存在於每個人的普遍傾聽和承認之中。語言是人的東西,同時又是自然的東西,它是對象化了的人的東西和人化了的對象的東西。
“人的第一個對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思維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現的要素,即語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語言既是人與人相互理解的媒介,也是人與自然的媒介,是人理解、把握自然規律的媒介。
當然,這裏指的應當是一種理想的語言,而且不是現代分析哲學家所構想的那種科學的人工理想語言,而更接近海德格爾所推崇的那種充滿暗示性的、具有豐富底蘊和“言外之意”的語言。這並不排除語言的邏輯規範、理性和規律,因爲即使是暗示,也是需要規範、至少需要別人會意和承認的,最“詩化”的語言也是將不可言說的東西說出來、展示出來的媒介。
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也正是將不可固定(定形)因而不可追隨的和不可言說的變本身固定在語言的暗示中從而表達出來的手段。變本身,作爲變的變,是不可固定的,正當你要固定它進,它又變了,你規定的只是所變成的東西,而不是變本身。
這正是米利都派和畢達哥拉斯派失敗的原因。赫拉克利特則說:“那位在德爾斐發神讖的大神不說話,也不掩飾,只是暗示”,邏各斯在赫拉克利特這裏的作用,主要就是暗示,在古代哲學家中,他所使用的語言是最富暗示性魔力的。
而且一般說來,語詞的“魔力”(如原始時代的巫咒)是建立在它的豐富的暗示性意謂之上的。沒有一個語詞是本來就“空洞”的。語詞之所以成爲空洞無物,是因爲人們遺忘了其中所包含的不可言說的意謂,或是故意將語詞和它的意謂割裂開來的結果。
由此可見,如果說,赫拉克利特提出邏各斯思想是當時所能達到的頂峯,那麼,這恰好是由於對哲學語言的追尋最終在他這裏回到了語言本身。
當人們正在爭論用一個什麼樣的語詞來表達和規定世界的本原時,赫拉克利特站出來說:就用“語詞”這個語詞吧!他把語言的本性賦予了世界的本原(火),使它能夠規定那不可言說的“變”本身。這是語言的自覺(自我意識)或語言的覺醒:“不可以像睡着的人那樣行事和說話”。邏各斯的上述作用在黑格爾哲學中得到了最明確的體現。
前面說過,畢達哥拉斯派的數中之“一”的原則在埃利亞派那裏轉化爲存在的“一”,即存在的不可分性與統一性原則。但這種轉化看來與赫拉克利特也並不是毫無關係。我們曾看到,赫拉克利特首先強調了邏各斯的同一性,要求人們“承認一切是一纔是智慧”;另一方面,埃利亞派的巴門尼德提出“存在是一”命題時,其根據既不是米利都派的觀察假設,也不是畢達哥拉斯派的數學證明,而是邏各斯。
在現有的殘篇中,巴門尼德開頭引用女神的告誡說:“要用你的邏各斯去解決我告訴你的這些紛爭”;而在他論證和闡述了關於存在的整個學說之後,總結性的一句話是:“現在結束我關於真理的可靠的邏各斯和思想”。這裏顯然有一種前後呼應關係。那麼,巴門尼德的邏各斯與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是不是一個意思呢?
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從邏各斯所表述的內容來看,兩者是完全對立的。巴門尼德顯然認爲,像赫拉克利特那樣將存在與非存在看作一回事,這並不能表達真正的真理;伊奧尼亞學派想去把握“作爲變的變”,這隻能是純粹的幻想,得出的只能是意見,而非真理;因爲當你說“某物是什麼”時,等於說“某物爲什麼而存在”,當你這樣說,這樣想時,這個某物已經變了。
事實上也的確是這樣。赫拉克利特想表達作爲變的變,想把握這種變的邏各斯,但留在他手中的仍然是一個很有限的感性自然之物即“火”,或一個形象的比喻“流變”(即水,或“河流”)。
巴門尼德據此就認爲,要想把握變,就不能不陷入意見,侷限於感性自然,而達不到抽象的邏各斯。要想得到“關於真理的可靠的邏各斯”,必須拋棄“變”的思想,而考察那不變、不動、不可分的存在,並將它與“非存在”嚴格區分開來。
不過,從這裏也正可以看出,巴門尼德雖然在邏各斯的內容上與赫拉克利特持相反的看法,但在形式上,對於哲學最終要找到一種正確可靠的邏各斯(話、言辭、表述),他與赫拉克利特是完全一致的。
鑑於赫拉克利特首次將邏各斯的尋求提升爲哲學的最高任務,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就沒有巴門尼德的“存在”。
邏各斯是巴門尼德論證和得出其存在原理的手段,這一點從巴門尼德自己的論證過程中可以看得很明顯。例如他說:“能夠被表述、被思想的必定是存在”。這裏的“表述”或“說”一詞,正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海德格爾認爲應當用來理解邏各斯的那個詞。類似的說法還有:
“我不允許你說,也不允許你思想存在來自非存在,因爲非存在是既不能被表述,也不能被思想的”;“思想只能是關於存在的思想,因爲你找不到一個沒有它所表述的 存在的思想”;他反駁相反的(赫拉克利特等人的)道路說:“這條道路是什麼也學不到的,因爲你既不能認識非存在,也不能將它說出來”,或:“將那條途徑當 作不可思想的、不可言傳的途徑拋棄吧”。
巴門尼德的殘篇並不多,他如此強調錶述、說和言傳的作用,可見“邏各斯”的思想在他這裏所佔的分量。

陳村富先生說得對:“巴門尼德是將‘存在’、‘思想’、‘表述(說)’放在同一個系列”,可惜他沒有進一步從哲學上闡明這三者的關係,而只是簡單地歸之於古希臘人的說話習慣:希臘人認爲“能被表述的東西一定是能被思想的”。
其實,只要我們在這裏不把 λɛγɛlv 一詞僅僅理解爲日常意義上的表述,而是將它當作真正的與“思想”和“存在”平級的哲學範疇(邏各斯)看待,那麼我們就會看出,當巴門尼德提出其著名的命題“思維和存在是同一的”時,他的意思是指:
思維和存在同一於邏各斯。由於有了邏各斯,思維和存在纔是同一的,“因爲你找不到一個沒有它所表述的存在的思想”,思想就在於表述,而表述必定是表述一個存在,表述或邏各斯是思維和存在的中介。
黑格爾在其《哲學史講演錄》裏給予了巴門尼德極高的評價,認爲“真正的哲學思想從巴門尼德起始了”,因爲他提出了對有和無的分析並認爲思維和存在是同一的。
但黑格爾並沒有花很大篇幅來論證這一點。他對整個埃利亞學派的評價也是如此。他宣稱:“我們在這裏發現辯證法的起始,這就是說,思想在概念裏的純粹運動的起始;因而我們就發現思維與現象或感性存在的對立,自在物與這一自在物之爲他物而存在之間的對立,並且我們發現客觀存在本身所具有的矛盾(真正的辯證法)”,埃利亞派由以達到這種思維辯證法的前提和工具——邏各斯學說,在這裏卻隻字未提。
當然,如果提到這點,他的哲學史也許就得改寫,而不得不將赫拉克利特恢復到實際上先於巴門尼德的地位了;但不提這點,埃利亞派的思想確實顯得跨度大了一點:
怎麼從畢達哥拉斯的數,一下子就提出來一個存在和非存在的對立?爲什麼巴門尼德如此固執地反對把非存在當作存在?他反對的是誰?
總之,將赫拉克利特人爲地擺到巴門尼德之後,除了史學界給人以糟糕的印象之外,也增加了理解黑格爾辯證法的困難,使人失去了把握黑格爾邏輯學開端的線索,不能從語言本身的辯證內涵來理解開端的提出及其運動,並導致了邏輯範疇的動力源來自體系外部(如特倫德倫堡)這樣的誤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