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界泰斗曹禺說過:《茶館》的成就前無古人、蓋世無雙。
但在學生時代,我不喜歡看茶館,總感覺苦難屬於過去時。進入社會後,才逐漸看懂了《茶館》,而且是常看常新,甚至耳邊經常出現一個聲音:那麼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

老舍先生曾說過:一個大茶館就是一個小社會。
《茶館》是個三幕劇,歷經60年,掠過了三個時代。第一幕是大清尾聲,第二幕是民國初年,第三幕是抗戰勝利之後。
茶館要跨越這三個時代,當然無法迴避政治。但茶館的掌櫃王利發,無論在哪個時代,都要茶館“莫談國事”,他天真的以爲只要老實經營,就能勤勞致富。
但鄭板橋的“難得糊塗”,絕對不是生存的奧祕。你可以不去關心政治,但政治早晚要來關心你,不管你是什麼階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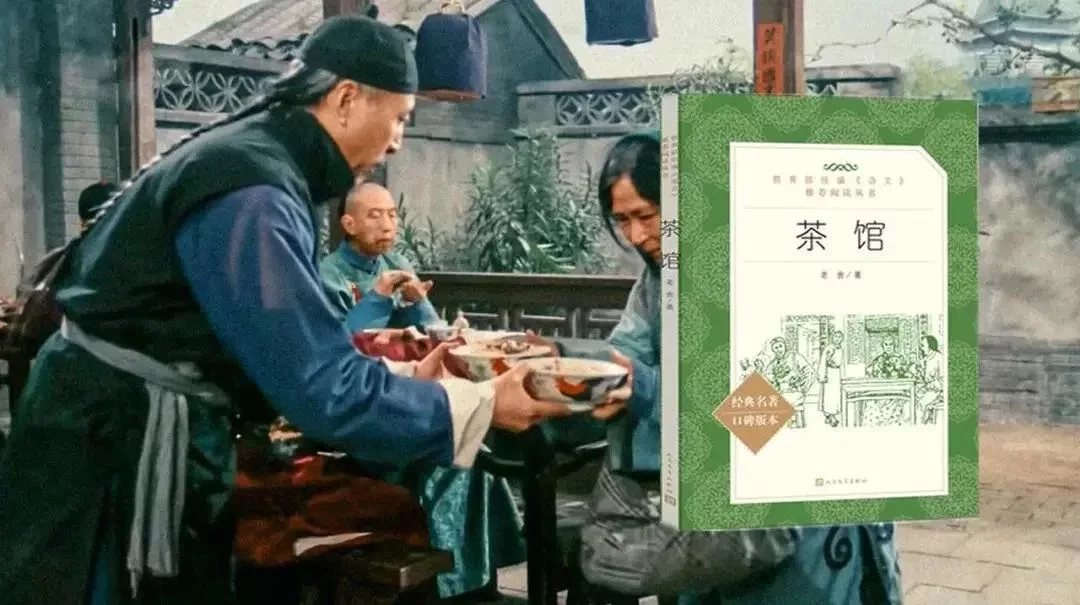
茶館裏的人,大體可以分成三個階層。
首先是食利階層。
茶館是一個大雜燴,真正的食利階層很少踏足,但他們纔是攪動茶館風雲的幕後大手。只有偶爾幾個食利階層的邊緣人物,纔會在茶館驚鴻一瞥。比如第三幕的沈處長,他的現身就意味着王掌櫃茶館的易手。
比如龐太監。他要給自己買個媳婦,要親自面試纔來的茶館,他花了200兩從皮條客劉麻子那裏買了一個農村姑娘。因爲老佛爺處斬了譚嗣同,龐太監似乎感覺自己可以雄起,自己的太監事業也可以傳承,於是又買了一個兒子。
不管是買媳婦兒子,還是謀奪資產,在大廈將傾之時,這些食利階層想的都是自己。至於國家危亡、社會公正、變法改革等等,食利階層並不關心。
其次是幫兇階層。
這個階層,無論在哪個時代,都能活的逍遙快活。
比如宋恩子和吳祥子,他們在大清當走狗,到了民國繼續當走狗,後來他們的兒子也承襲父業,不過他們的目的都很明確,那就是一心一意的撈錢。
他們沒有是非立場,只是鑽營投機。在大清,他們就當大清的幫兇,在民國,他們就當民國的爪牙。當權者的立場就是他們的立場,當權者的是非觀就是他們的是非觀,因爲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藉助特權撈錢。

吳祥子有一句常看常新的臺詞:誰要是恨我們,那就是恨大清,誰要是罵我們,那就是罵大清。
宋恩子也有一句常看常新的臺詞:我們就是大清,大清就是我們。大清 ,就沒有辦錯事的時候。
他們嘴裏的大清,當然可以隨時隨地的替換,他們身在何時就替換成何時,他們身處何地就替換成何地。
二德子、劉麻子,以及他們的後代和精神後代,都是這類人,用他們自己的話就是:誰給錢就給誰賣命。雖然缺德,但是他們掙得就是缺德的錢。
不過,秦二爺是個特例,雖然他作爲新生資產階級的一員,但不願意充當爪牙。他瞧不起腐朽的大清,甚至敢於面斥有權有勢的龐太監。
他堅信實業救國,可是開辦工廠的過程中,他要不停的面對敲詐勒索,最後經營了幾十年的工廠,還被充了公。
心如死灰的秦二爺,痛心疾首地悟出了一個道理:有錢就得喫喝嫖賭、胡作非爲,可就是,千萬別做好事!

最後就是牛馬階層。
三個時代的牛馬階層都很艱難,比如農民康六,被迫把自己的女兒康順子,以10兩銀子的價格賣給劉麻子,劉麻子轉手以200兩的價格又把康順子賣給了龐太監。
還比如茶館的掌櫃王利發,他苦心經營茶館,可是特務、巡警、兵痞接二連三的敲詐勒索,王利發不得不低頭哈腰,誰也不敢得罪。
王利發有一句臺詞,特別的有意思:現在山上哪還有土匪啊,都下山進城了。王利發最大的困惑就是:我是個順民啊,怎麼總倒黴呢?
王利發想要的從來不是大富大貴,而是老實本分的一生。所以當最終親人散盡,他唯一的精神依靠——茶館,也要被人奪走時,他選擇吊死在茶館裏,這是他對時代的最後控訴。
茶館的跑堂李三,同樣勤勤懇懇,他也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臺詞:改良!改良!越改越涼、冰涼冰涼,我還是留着我的小辮子,萬一把皇上改回來呢!
底層牛馬對變法改革不理解、不關心、不討論,甚至諷刺那些知識分子的胡鬧瞎折騰。
但也有特例,那就是常四爺,他對大清國憂心忡忡,他看不上假洋鬼子,也看不慣官差的爪牙二德子,他對着二德子說出了那句常看常新的臺詞:要抖威風跟洋人幹去。不過二德子也回了一句常看常新的反問:我打不了洋人,還打不了你嗎?
常四爺更看不得“鄉婦賣女”,一時口快說了句:我看這大清國是要完哪!結果被特務聽見,送進了衙門。
常四爺耿直了一輩子,可風燭殘年的他連一個棺材也沒有,黃泉路上唯一的陪伴,還是在別人出殯時撿的紙錢。他將死之時的那句臺詞,足以穿透歷史的迷霧,叩問無數人的良心:我愛咱們的國呀,誰愛我呀。

茶館的人來來去去,窮人賣兒賣女,惡霸良心喪盡,官差搶人搶錢。一邊是實業家們的報國熱情盡付風中,另一邊是酒囊飯袋借風持權。修橋補路無屍骸,殺人放火金腰帶。
話劇的結尾,幾位老爺子聚在一起給活着的自己撒紙錢,淒涼而熱鬧地喊上了一句:本家賞錢一百二十吊。這一幕,讓人唏噓萬分:生的無奈,走的也無奈。
1966年8月23日,老舍無奈的爲《茶館》做了最終的《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