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斯特拉·桑福德是倫敦金斯頓大學現代歐洲哲學研究中心的現代歐洲哲學教授。她的著作包括《植物的性別:植物哲學》(Vegetal Sex: Philosophy of Plants,2022)《柏拉圖與性》(Plato and Sex,2010)和《如何解讀波伏娃》(How to Read Beauvoir,2006)等。本文原載於aeon.cn網站,原標題爲:“重新認識植物——植物令人驚歎的複雜行爲引發了我們思考世界的新方式:植物哲學”(Seeing plants anew — The stunningly complex behaviour of plants has led to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our world: plant philosophy)。
文|斯特拉·桑福德(Stella Sandford)
譯|李斯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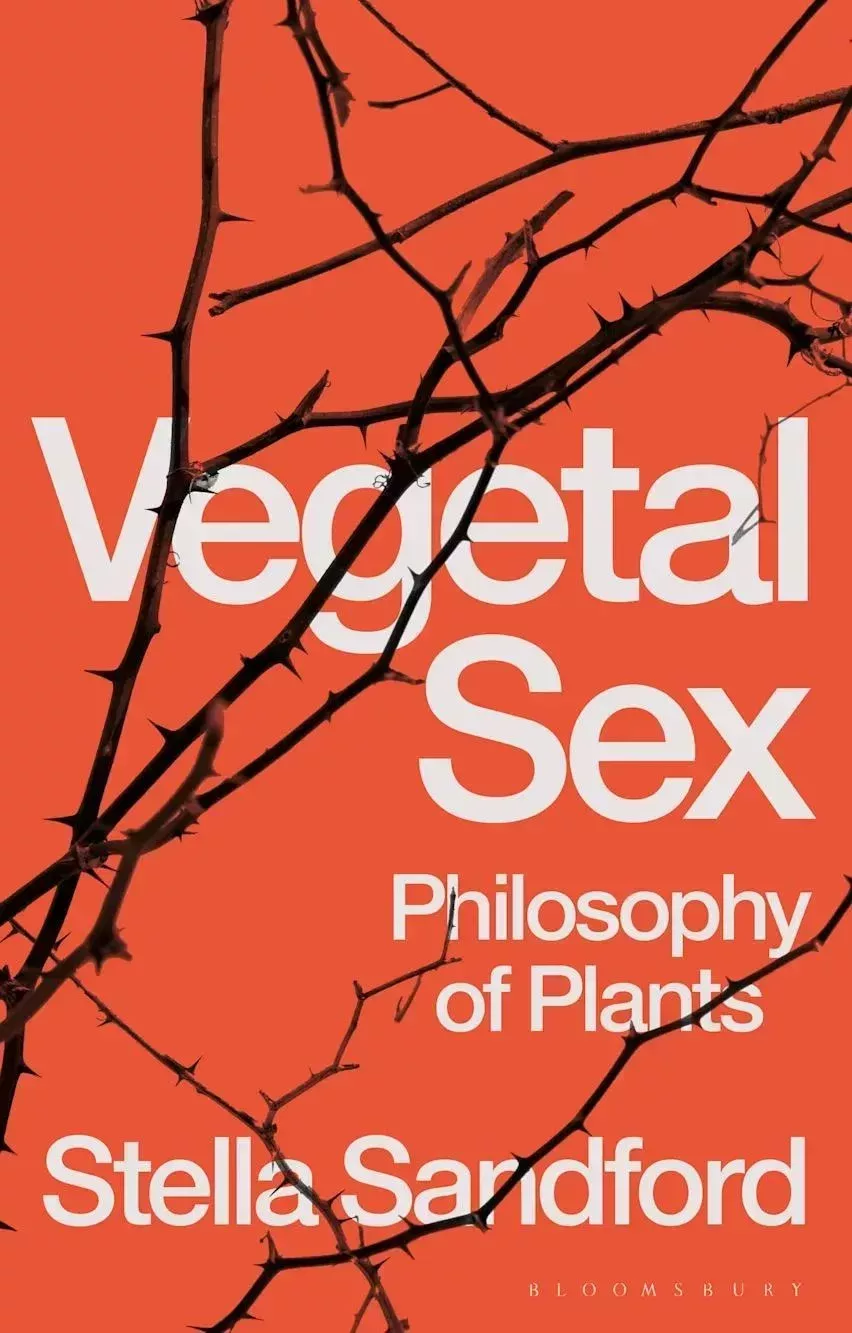
至少在西方社會裏,人們曾經普遍認爲,植物於動物生命而言是被動、惰性的背景,或者僅僅充當着動物的飼料。誠然,植物自身可能十分迷人,但它們缺乏動物和人類的許多有趣之處,例如能動性、智慧、認知、意圖、意識、決策、自我認同、社會性和利他性。然而,上世紀末以來,植物科學的突破性發展徹底推翻了這種觀點。我們纔剛剛開始窺見植物與環境之間、植物彼此之間、植物與其他生物之間異常複雜而微妙的關係。對植物的認識能取得這些重要進展,主要歸功於植物行爲研究(the study of plant behaviour)這一特定的研究領域。
鑑於“行爲”一詞與包括人類在內的動物的聯繫,“植物行爲”的概念可能看起來有些奇怪。當人們想到經典的動物行爲——蜜蜂跳舞、狗搖尾巴、靈長類動物相互梳理毛髮——我們可能會好奇,植物生命中會有哪些與之對應的行爲呢?
生物學家和生物學哲學家羅素(E. S. Russell)是動物行爲研究之重要性的早期倡導者之一。1934年,羅素主張,生物學應從研究整個有機體開始,並將有機體視爲一個動態統一體,經歷着維存、發展和繁殖的循環。他認爲,這些活動都是“目的指向的”,正是這種“指向性”活動將生命體與非生命體區分開來。按照羅素的說法,行爲涉及有機體與其外部環境的關係,是這種“有機體一般指向性活動”的形式。這意味着植物和動物一樣,都會表現出行爲。但由於植物是固着的(sessile),它們的行爲主要表現在生長和分化中(胚胎細胞發育成植物的特定部分),而不是像動物那樣表現在運動中。
到20世紀末時,我們對植物行爲的理解已經遠遠超出了生長和分化的範疇,並且這種理解還在繼續擴展中。正如植物學家安東尼·特雷瓦弗斯(Anthony Trewavas)所言,植物行爲就是“植物所做的事情”。事實證明,植物確實會做很多事情。讓我們以受傷爲例,大多數植物通過釋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來應對葉片受到的傷害。其中一些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能激活非生物應激相關基因(abiotic stress-related genes),另一些則具有抗細菌和抗真菌特性。有些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專門用難聞的氣味或毒素驅趕攻擊植物的食草動物;有些植物可以識別出是哪種特定的食草動物正在攻擊自己,並相應地作出不同的反應;還有些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會吸引正在攻擊植物的昆蟲的天敵。食草動物的攻擊還能誘使植物分泌更多的花蜜,從而促使昆蟲遠離葉片。(注:一種間接防禦機制。)
這些反應很容易被理解爲“目的指向性”行爲——指向植物自我保護與繁衍的目的。它們很可能賦予植物適應性的優勢。但是,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釋放也會誘使鄰近植物在自身受到攻擊之前產生同樣的反應,即使它們是不同的物種。一些實驗似乎表明,植物有可能對那些它們認爲與自己具有親緣關係的植物(由同一種植物的種子生長而成的植物)表現出不同的有利行爲。例如,在一項實驗中,研究人員將鳳仙花種植在共用的花盆中,以研究它們如何應對地上光照和地下根系空間的競爭。他們發現,在有親緣植物的花盆中生長的植物莖幹更長、分枝更多,而與非親緣植物生長在一起的植物則長出了更多的葉子,阻礙了其他植物獲得光照。因此,植物似乎與親緣植物進行合作,而試圖與非親緣植物進行競爭。
植物的“存在”挑戰了主導西方傳統的一些重要假設
對一些科學家來說,這項研究具有顛覆性的意義,它爲植物科學開創了新的範式,並且提出了一種新的植物生命觀。現在許多人認爲,這項實驗的結果要求我們承認,植物具有先前被認爲是動物甚至是人類所獨有的特性和能力。在一些人看來,如果不借助相關術語,我們根本無法理解科學向我們展示了什麼。
這些重要的進展也引起了哲學家們的關注。科學哲學是哲學學科中一個成熟的分支領域,而生物學哲學則是科學哲學中的成熟分支。但是最近,我們看到了一些似乎是新的東西:一個專門思考植物問題的哲學領域——“植物哲學”。它不僅是對植物科學研究的元批判分析,而且還受到植物科學研究的啓發,對植物重新展開哲學思考。
新植物哲學的出現在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植物科學的回應,尤其是對其中新範式的回應。標誌了新範式的一系列概念——能動性、意圖、意識等等——早已成爲哲學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主題。一旦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到植物上,更廣泛的問題就出現了。這不僅是因爲哲學對植物感興趣,也因爲我們發現,植物生命或植物存在(plant being)的特殊性,挑戰了幾個世紀甚至幾千年來主導西方傳統的一些重要假設。植物哲學不僅關乎植物,還關乎植物生命的特殊性如何迫使我們以新的方式來思考自身的存在。
在一些人看來,“植物哲學”這個概念似乎很荒謬,就像某種新潮的時尚,並且你也不會在任何一本最新的哲學詞典中找到它的條目。但事實上,植物與哲學之間的關係幾乎與西方哲學史一樣悠久。亞裏士多德爲理論植物學奠定了基礎,他將生物定義爲自身具有營養、生長發育和衰亡能力的事物。只有某些自然事物具有生命的潛能,而“靈魂”就是這種潛能的實在(reality)。因此,只要生物是活着的,它們就擁有靈魂(希臘語的“psuchē”翻譯成拉丁文即“anima”,意指有生命和無生命的區別)。
亞裏士多德將靈魂分爲三個“部分”:“營養靈魂”“感覺靈魂”和“理知靈魂”。“營養”能力是生命的基本原則,是包括植物在內的所有生物所共有的。此外,動物具有靈魂的“感覺”部分,而人類則獨有“理知”的部分。亞裏士多德認爲,靈魂的營養部分的功能是利用營養和生產(即後來所說的繁殖),這兩者都是一種“運動”或“變化”。由於植物也擁有這種靈魂,因此在亞裏士多德的著作中,它也被稱爲“營養”靈魂或“植物”靈魂(這就是爲什麼一個被認爲喪失了感覺或思維能力的受損人類,會被稱爲處於持續的“植物”狀態)。
直到17世紀,亞裏士多德關於植物靈魂的思想在植物學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僅舉一例:佛羅倫薩哲學家安德烈亞·切薩爾皮諾(Andrea Cesalpino)的《植物》一書(De Plantis,1583)第一次對植物進行了科學意義上的分類。他認爲,植物的本性在於營養和繁殖的功能,因爲這是它們所擁有的唯一一種靈魂的“本質”。隨着全球航海時代的到來,大量不同的植物物種被發現,對植物分類系統的需求也與日俱增,而植物的分類系統被認爲應當基於植物的本性。因此,切薩爾皮諾根據產生種子與果實的方式,建立了他的植物分類系統(在屬的層次上)。在致他的贊助人阿方索·託納布奧尼(Alfonso Tornabuoni)的一封信中,他寫道,自己之所能成功地制定這一分類系統,是因爲他將“植物學專業知識與哲學研究相結合,沒有哲學研究,(植物學)就無法取得進展”。
植物學史將 19 世紀從哲學中獲得“解放”視爲其科學進步的關鍵因素
對亞裏士多德哲學相關思想的繼承也推動了植物學研究。在其生物生育理論中,亞氏認爲,雄性“原則”有能力通過爲其他被動(雌性的)物質“賦予靈魂”來傳遞運動或生命。但由於亞氏的生育理論實際上只是關於動物的繁殖理論,這種雄性力量通常被定義爲製造感性靈魂的力量。由於植物不具有感性靈魂,因此植物似乎不可能存在雄性和雌性之別。但是,如果像亞氏認爲的那樣,雄性原則生成了更普遍的生命或運動,那麼,既然植物是有生命的,植物中就一定存在雄性與雌性之類的差異。
這一難題困擾着植物學早期歷史上所有的開拓者們。但它非但沒有阻礙研究,反而推動了該領域的發展。雖然在植物生理學中,沒有與動物的性器官和性物質相對應的明顯特徵,但研究人員認爲一定存在着某種與之相應的東西,因爲植物和動物共享了負責繁衍的“植物靈魂”。英國植物學家尼希米·格魯(Nehemiah Grew)被認爲發現了花朵的生殖器官,這一發現正是緣於他在尋找亞裏士多德所說的“雄性器官”(或功能)的生命原則。格魯將這一原則與花粉聯繫起來,儘管這種聯繫是混亂的。
如今,植物科學認爲自己與哲學毫無關係。事實上,植物學史將19世紀植物學從哲學中“解放”出來視爲其科學進步的關鍵因素。但是,這忽略了一些最重要的植物學研究者的哲學熱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科學工作。認爲科學的發展可以脫離關於現實本質的基本形而上學假設,這是一種天真的想法。
堅持把植物學與哲學相分離也意味着,我們將無法理解植物學在傳統意義上的哲學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讓-雅克·盧梭(1712-1778)都熱衷於植物學。對於這些哲學家來說,這只是一種非哲學的愛好嗎?還是他們對植物的研究影響了他們的哲學思考?在提出這些問題時,我們又回到了新植物哲學,它既試圖挖掘哲學與植物學相互糾葛的歷史,又旨在重新激活兩者之間的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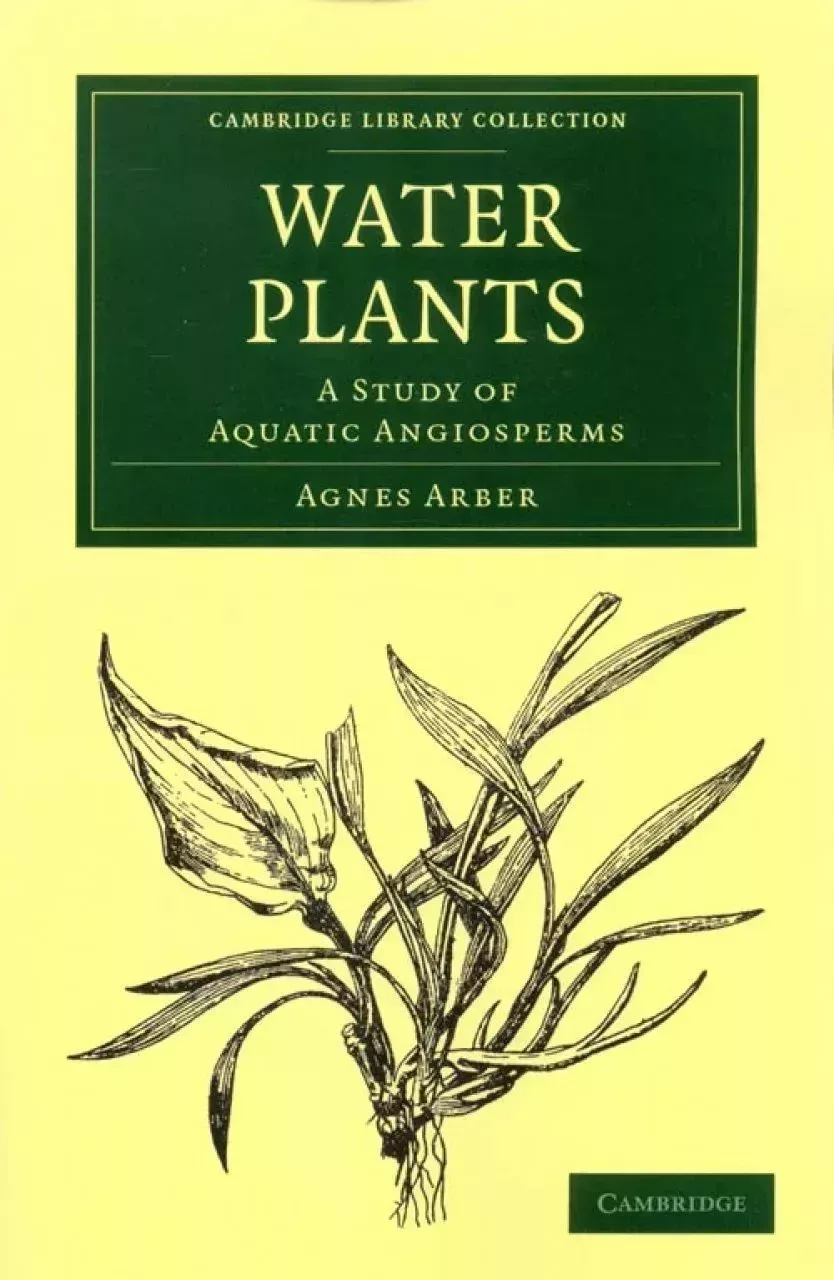
英國植物學家阿格尼絲·阿爾伯(Agnes Arber,1879-1960)是20世紀深耕這一領域的傑出人物,她主張將歷史和哲學研究視爲現代科學實踐的一部分。阿爾伯在許多文章和專著中對植物形態學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水生植物》(Water Plants,1920)《單子葉植物》(Monocotyledons,1925)和《禾本科植物》(Grasses,1934)。在《植物形態的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 of Plant Form,1950)中,她的研究方法的哲學基礎得到了明確闡述。對阿爾伯來說,植物形態學——對植物形態的研究——不僅僅是對植物外部特徵的描述,而是對植物形態進行的更全面的研究。她回溯了亞裏士多德的“形式”(eidos)概念,並將其理解爲“任何特定個體都是其內在本質的體現”。她的這種理解大大超越了亞裏士多德,將“內在本質”涵蓋了植物的整個生命史,包括植物的大小和外形的變化。這將形式重新定義爲動態的,並拒絕對形式進行與功能相分離的分析。這一“形式”概念對阿爾伯至關重要,它讓她看到了純粹分析方法所忽略的方面。
阿爾伯論證了植物畸形學對“正常現象”的研究非常重要,對此,斯賓諾莎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阿爾伯將植物的“異常現象”,即“未被實現的潛能的揭示”,表述爲“植物能做什麼”的說明,這呼應了斯賓諾莎“身體能做什麼”的名言。她的枝葉關係理論明確引用了斯賓諾莎關於“自我持存的衝動”的論述。對阿爾伯來說,這些哲學資源是她提出植物學假說的靈感來源。隨後,她試圖用通常的科學方法,即通過觀察獲得的證據來證實這些假說(這通常是成功的)。
阿爾伯強調哲學對植物學的重要性,這一觀點最近得到了一些植物學家和生態學家的支持,他們爲當代植物哲學的一個分支做出了貢獻。法國植物學家弗朗西斯·哈雷(Francis Hallé)專門研究熱帶雨林和樹木結構(他參與發明瞭浮筏,這讓科學家第一次能夠進入熱帶樹冠層)。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哲學家開始思考,對植物生命的科學研究專注於化學時,以及“將植物簡化爲染色體數目、鹼基對序列、拉丁二項式、細胞器的電子圖像、曲線上的一點、一份參考書目、計算機存儲器中的一個數據、離心機裏的殘渣或試管底部的愈傷組織(callus)”時,我們失去了什麼——哈雷正是其中的一員。除此以外,哈雷在他的書《植物禮讚》(In Praise of Plants,1999/2002)中提倡迴歸對植物的整體研究,“從它的根到它的花,它的土壤,以及它在歷史上的用途。這很重要,因爲我們需要用我們的感官來感知它,而不僅僅是以一種思維的、失活的方式。”
對植物生命本體論的思考具有超越植物的意義
在哈雷看來,對植物生命的特殊性進行反思,不可避免地會引出哲學問題,而植物學家和哲學家同樣需要探討這些問題。如果動物個體是一個單元(珊瑚是一個例外),而植物是通過單元的重複而發展起來的,那麼植物“個體性”的本質是什麼?動物和植物的“個體”概念是否相同?我們是否需要重新定義“個體性”的概念,以便將植物納入其範疇?
法國生態學家雅克·塔桑(Jacques Tassin)同樣堅信,在理解植物生命的過程中,哲學是不可缺席的。他的著作《植物在想什麼?》(À quoi pensent les plantes?,2016)從這樣一個哲學問題出發:成爲植物意味着什麼?塔桑認爲,這一提問很有必要,因爲“不可抗拒的動物中心主義讓我們根據動物的狀態來衡量世界”。誠然,基於動物生命的模型在植物研究中很有幫助,但我們是否也需要根據植物自身的模式,找到更貼近植物自身“存在”的方法來研究植物呢?
很顯然,對植物生命本體論的思考有着超越植物的意義。無論是在西方哲學中還是日常生活中,我們都傾向於以二元對立的方式來進行思考。這些佔據支配地位的對立項的集合,被認爲在思維中捕捉到了類似於現實結構特徵的東西,一些人將其簡稱爲“西方形而上學”。它們包括內/外、物質/形式、心靈/身體、個人/集體、生/死、一/多、男/女等對立項。20世紀西方哲學和相關領域(如女性主義理論)的很大一部分都致力於對其中的一些組合進行批判性研究,有時甚至是正式的“解構”,但它們仍然形塑了我們大部分的思想與行動。在許多情況下,這是因爲它們很有效,而且確實描述了我們經驗的直觀特徵。譬如,在冬天,屋子裏比屋外暖和,因此我想保持內/外的區別,非常感謝!這些區別可以在日常使用的環境中存在,並能包容一些極限情況(例如,一扇打開的窗戶通向一個微風習習的房間)。這當中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當這些區別的有效性與現實各方面結構中的明確劃分相混淆時——當它們成爲強烈意義上的“形而上學”時——它們可能是阻礙性的,甚至是壓迫性的(尤其因爲,這些二元對立通常是根據歷史上確立的等級制度來發揮作用的,在其中一個比另一個享有特權或更受重視)。如果自然和社會現實的某些方面在這些術語中根本無法得到充分的描述(是的,自然/社會是其中的另一種區分),那麼它們的假定就會妨礙我們理解這些現象。因此,植物哲學的另一個分支聚焦於,植物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無法用西方形而上學的傳統術語來充分描述。譬如,如果把植物生命的某些方面劃分到個體/集體的任何一方中來理解的話,它可能無法捕捉到植物模塊化結構或重複現象的迷人之處。這表明,這種形而上學區分的普遍性假定是錯誤的。在著作《植物思維:植物生命的哲學》(Plant-Thinking: A Philosophy of Vegetal Life,2013)一書中,哲學家邁克爾·馬爾德(Michael Marder)甚至認爲,植物的存在“引爆”了西方形而上學:“植物的存在本身就完成了對(西方)形而上學的生動的破壞。”
如果說植物存在的基本特徵無法通過西方哲學傳統的對立概念來充分理解,那麼這一哲學傳統的某個意想不到的特徵就浮現出來了。儘管我們傾向於認爲哲學是在最高抽象層次和純粹的“智力”領域中運作的,但它的形而上學實際上可能只是從具體的動物生命中被剪裁出來的。關於人類存在的哲學思考,需要從承認人類有限的、具身的社會心理存在開始。但是,一種包含了植物存在的形而上學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根據新的範式,在對植物行爲的解釋中,我們已經開始重新定義一些通常與哲學而非科學相關的術語,如“意向性”“行動”與“目的”。植物智能的概念是其中的核心。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假定“智能”是動物行爲的獨有特徵,認爲它依賴於大腦和中樞神經系統,或者它是一種具有大腦和中樞神經系統的有機體的可量化的屬性或能力,那麼我們當然會拒絕植物智能的概念。不過,植物智能的支持者們還是有充分的理由否認這種假設的合理性。
我們完全可以提供適用於植物行爲的“智能”定義,並且我們已經將這個詞應用於非生物。如果把生物個體的智能定義爲“個體一生中適應性變化的行爲”,並將其區別於由基因決定的發展過程,那麼將植物行爲描述爲智能即是有意義的,並且進一步明確植物的定義也是可行的。因此,特雷瓦弗斯將植物智能定義爲“個體生命週期內的適應性變化行爲”。植物中這種適應性變化行爲的例子包括:根部朝向水源定向生長、向光性(植物朝向光的方向生長)、釋放揮發性化學物質作爲對食草動物攻擊的反應。
這裏所使用的“智能”的一般定義意味着,任何不具有智能的生物(不能使自己的行爲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的生物)根本無法生存。因此,根據這一定義,智能是生物體能夠生存的內在特徵。它並非是對人們可能在某些植物行爲中認識到的特定特徵的定義,否則缺乏這一特徵的其他植物行爲則可被歸類爲非智能的。相反,它把智能作爲研究一般植物行爲的不證自明的起點。這裏的任何爭論都不是關於某種行爲是否是智能的分歧——在後者中,雙方都會嘗試收集實驗性證據以證明該行爲是否符合智能的標準。在這裏,爭論的焦點是智能本身的定義。這是一個哲學問題:什麼是智能?植物科學的新範式背後不可避免地蘊含着這個哲學維度。哲學是這種植物科學的一部分。
我們真的需要“能動性”這個概念來理解植物的表型可塑性嗎?
當然,我們不必等到植物科學中出現這一新範式——如果它確實是一種新範式的話——才提出“生物智能”的概念。在這方面,植物智能並不像它乍看之下那樣不可思議。它只是將現有的關於生物智能的思想擴展到了植物。何樂而不爲呢?但新範式並不止步於此。例如,有人聲稱,植物智能要求我們也將植物視爲“能動者”,或者被賦予了能動力量的生物,而不是一種按照程序對外界條件做出機械和化學反應的活體自動機。正如特雷瓦弗斯和西蒙·吉爾羅伊(Simon Gilroy)在2022年寫道的:“有許多行爲都證明植物是能動者,它們的行動是有目的的,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可塑性。”
那麼,什麼是能動者?擁有能動性意味着什麼?植物是否與動物,尤其是人類一樣具有能動性?吉爾羅伊和特雷瓦弗斯將植物描述爲“自主地引導自身行爲,以實現外部和內部的目標或規範,同時與現實世界的環境進行持續的長期互動”的能動者。例如,在一項實驗室實驗中,生長在乾燥土壤和充足光照條件下的植物長出了較大的根系(以最大限度地獲取土壤水分),以及窄小、節水、角質層厚的葉片;而生長在潮溼土壤和相對陰暗條件下的基因複製體則長出了寬大、角質層薄的葉片(以最大限度地擴大光合作用面積)。因此,我們說植物是能動者,因爲 “它們會靈活地改變自己的表型(phenotype),以提高生存能力”,這種調整被稱爲“自主行動”。但是,我們真的需要“能動性”這一概念來理解和欣賞植物的表型可塑性嗎?將這一概念應用於植物,我們究竟能獲得什麼呢?
生物學哲學家薩米爾·奧卡沙(Samir Okasha)在他所說的“有機體作爲能動者”的論斷和“有機體作爲能動者”的啓發性方法(heuristic)之間進行了有益的區分。前者對有機體是什麼樣的存在提出了本體論的主張,奧卡沙將它與生物學中反對以基因爲中心的範式聯繫起來。而“有機體作爲能動者”的啓發法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方法,出於科學理解的目的,它將有機體視爲具有目標的能動者。
不過在實踐中,這種區別並不總是顯而易見的。例如,進化生態學家索尼婭·蘇丹(Sonia E. Sultan)在她的植物研究工作中提倡所謂的“生物能動者視角”的“解釋策略”。這種策略使得科學家能夠解決基因中心主義方法在解釋上的一些缺陷。這聽起來更像是“有機體作爲能動者”啓發法,因爲它強調的是植物能動者假設的解釋性收益,而不是在本體論上對植物有機體給予關注。但是,蘇丹也寫道,能動性是生物系統的“一種經驗屬性”,“是有機體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其組成系統對環境做出適應性反應的能力”。能動性視角“始於對生物是能動者的觀察”。認識到這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生物是如何發展、運作和進化的。
但是,能動性視角到底增加了什麼?它是否抓住了新範式提倡者們想要表達的植物能動性與植物智能的理念?它是否捕捉到了植物存在的特殊之處呢?
蘇丹認爲,能動性概念或許可以爲發育生物學和進化生物學中有關基因表達、發育、遺傳性質和適應基礎的新研究“提供一個統一的框架”。“能動性”本質上是這樣一個術語,它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基因轉移到主動反應機制上,這種機制會導致在某些情況下可遺傳的發育變化。因此,“能動性視角”並不一定是對植物特殊能力的歸因,而是可以理解爲對以基因爲中心的研究方法進行補充的研究方案。此外,和幾乎所有的生物學哲學家一樣,蘇丹明確否認能動性視角意味着植物具有任何行動的“意圖”,更不用說是有意識的意圖了。
植物研究新範式的倡導者們不僅提出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案,而且試圖用一套來自哲學和其他學科的概念以構建一幅植物生命的新圖景。我稱之爲“植物鼓吹文學”(plant advocacy literature)。因爲除了其科學基礎之外,它也代表了植物,併爲植物發聲。其目的不僅是推動植物科學的發展,更是爲了讓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植物,珍視植物生命並給予它們更多的尊重。
許多這類文獻都並不迴避使用“意圖”的語言,而是暢談植物的“選擇”。譬如,特雷瓦弗斯聲稱,研究表明,沙丘上的克隆植物(clonal plants)生長在資源豐富的區域而避開資源貧乏的區域,這就讓人“難以避免地得出結論:植物存在意圖與智能選擇,並具有選擇有益棲居地的能力。……對棲居地的有意選擇是顯而易見的。”在其著作《植物行爲與智能》(Plant Behaviour and Intelligence,2014)中,特雷瓦弗斯將“目的”或“目標”的含義等同於“意圖”,並作出了以下結論:植物確實有意抵抗食草動物,也確實有意對重力做出反應,但這僅僅意味着“植物意識到自己所處的環境,並採取行動應對那些削弱了自身生存和/或繁殖能力,從而削弱了其適應性的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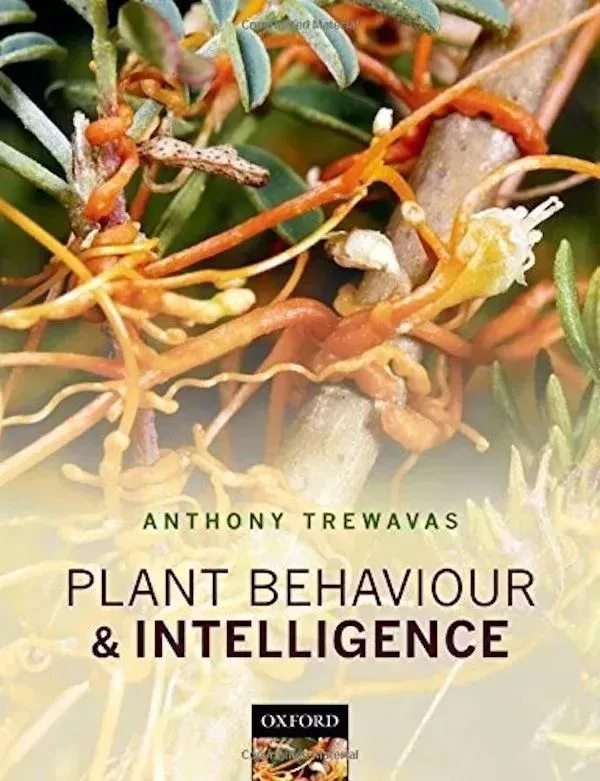
然而,某種人類中心主義的“意圖”和“選擇”敘述,在有關植物的流行著作中大行其道。意大利植物學家斯特凡諾·曼庫索(Stefano Mancuso)和亞歷山德拉·維奧拉(Alessandra Viola)甚至聲稱,植物自己選擇了固着的生活方式,選擇了由可分割的部分組成。流行讀物的讀者們看到的是,植物通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進行的交流被稱爲植物之間的對話,通過菌根從老樹向幼樹進行的營養傳遞則被形容爲母親對幼樹的哺育。這種將植物擬人化的做法與植物哲學的目標背道而馳,後者的追求是(儘可能)將植物理解爲植物——從植物的術語,而非動物或人類的術語來理解植物。
在日常生活中,欣賞這些生活在我們身邊的另一種生命對我們來說意味着什麼?
植物哲學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在於,它不僅要努力澄清在植物科學中使用能動性和智能等概念的合法性,而且要找到概念化“植物行爲”的方法——這種方法既要避免基因決定論的預設,又要避免某些植物鼓吹文學和大衆媒體中的人類中心主義或動物中心主義。當然,這種重新概念化的行動將包含現有的生物學哲學思想,但也必須超越它們。
生物學哲學所關注的問題無論多麼具體,都是一般性的生物學問題,因爲這些問題原則上涉及所有的生物體以及它們共有的生命過程(例如進化)。而植物哲學專門關注植物,研究植物區別於大多數動物的特性,以及這種特性對一些一般性哲學問題的影響。我們是否必須重新認識“個體”的概念,才能把由重複單元構成的植物視爲一種個體?如果我們開始嘗試用“植物行爲”來構建一種關於生物能動性的一般哲學解釋,而不是事後再將其納入其中的話,這會產生一種新的“生物能動性”概念嗎?在日常生活中,欣賞這些生活在我們中間的別種生命對我們來說意味着什麼?事實上,正是它們讓我們得以存活。
當代植物哲學纔剛剛開始提出這些問題。對此,答案依然是開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