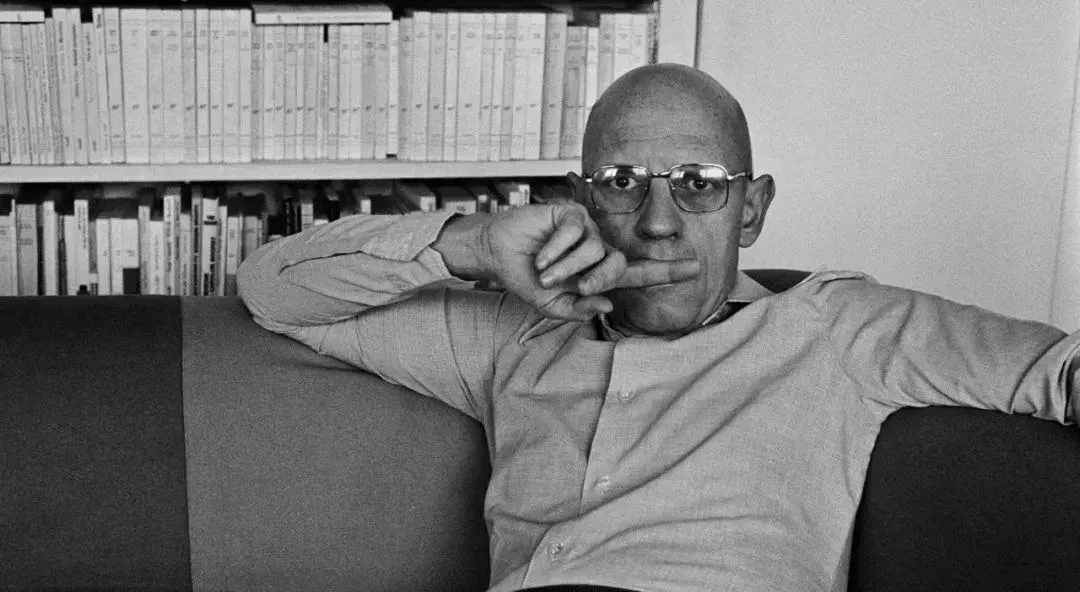
福柯廣爲人知的三部著作《古典時代的瘋癲史》《詞與物》和《規訓與懲罰》講述的歷史時段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從文藝復興到十八九世紀的現代時期。
但是這些歷史的主角不一樣。
《古典時代的瘋癲史》講述的是瘋癲(瘋人)的歷史;《詞與物》講述的是人文科學的歷史;《規訓與懲罰》講述的是懲罰和監獄的歷史。這三個不相關的主題在同一個歷史維度內平行展開。爲什麼要講述這些從未被人講過的沉默的歷史?就是爲了探索一種“現代主體的譜系學”。
因爲,正是在瘋癲史、懲罰史和人文科學的歷史中,今天日漸清晰的人的形象和主體形象緩緩浮現。福柯以權力理論聞名於世,但是,他“研究的總的主題,不是權力,而是主體”。即,主體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說,歷史上到底出現了多少種權力技術和知識來塑造主體?有多少種模式來塑造主體?歐洲兩千多年的文化發明瞭哪些權力技術和權力/知識,從而塑造出今天的主體和主體經驗?福柯的著作,就是對歷史中各種塑造主體的權力/知識模式的考究。
總的來說,這樣的問題可以歸之於尼采式的道德譜系學的範疇,即現代人如何被塑造成型。但是,福柯無疑比尼采探討的領域更爲寬廣、具體和細緻。
由於福柯探討的是主體的塑形,因此,只有在和主體相關聯,只有在鍛造主體的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福柯的權力和權力/知識。權力/知識是一個密不可分的對子:知識被權力生產出來,隨即它又產生權力功能,從而進一步鞏固了權力。知識和權力構成管理和控制的兩位一體,對主體進行塑造成形。就權力/知識而言,福柯有時候將主體塑造的重心放在權力方面,有時候又放在知識方面。
如果說,《詞與物》主要考察知識是如何塑造人,或者說,人是如何進入到知識的視野中,併成爲知識的主體和客體,從而誕生了一門有關人的科學的;那麼,《規訓與懲罰》則主要討論的是權力是怎樣對人進行塑造和生產的:在此,人是如何被各種各樣的權力規訓機制所捕獲、鍛造和生產?而《古典時代的瘋癲史》中,則是知識和權力的合爲一體從而對瘋癲進行捕獲:權力製造出關於瘋癲的知識,這種知識進一步加劇和鞏固了對瘋人的禁閉。這是福柯的權力/知識對主體的塑造。
無論是權力對主體的塑造還是知識對主體的塑造,它們的歷史經歷都以一種巴什拉爾所倡導的斷裂方式進行(這種斷裂在阿爾都塞對馬克思的閱讀那裏也能看到)。
在《古典時代的瘋癲史》中,理性(人)對瘋癲的理解和處置不斷地出現斷裂:在文藝復興時期,理性同瘋癲進行愉快的嬉戲;在古典時期,理性對瘋癲進行譴責和禁閉;在現代時期,理性對瘋癲進行治療和感化。同樣,在《規訓與懲罰》中,古典時期的懲罰是鎮壓和暴力,現代時期的懲罰是規訓和矯正;古典時期的懲罰意象是斷頭臺,現代時期的懲罰意象是環形監獄。在《詞與物》中,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型是“相似”,古典時期的知識型是“再現”,而現代知識型的標誌是“人的誕生”。儘管瘋癲、懲罰和知識型這三個主題迥異,但是,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它們同時經歷了一個歷史性的變革,並且彼此之間遙相呼應:正是在這個時刻,在《詞與物》中,人進入到科學的視野中,作爲勞動的、活着的、說話的人被政治經濟學、生物學和語文學所發現和捕捉:人既是知識的主體,也是知識的客體。
一種現代的知識型出現了,一種關於人的新觀念出現了,人道主義也就此出現了;那麼,在此刻,懲罰就不得不變得更溫和,歐洲野蠻的斷頭臺就不得不退出舞臺,更爲人道的監獄就一定會誕生;在此刻,對瘋人的嚴酷禁閉也遭到了譴責,更爲“慈善”的精神病院出現了,瘋癲不再被視作是需要懲罰的罪惡,而被看做是需要療救的疾病;在此刻,無論是罪犯還是瘋人,都重新被一種人道主義的目光所打量,同時也以一種人道主義的方式所處置。顯然,《詞與物》是《古典時代的瘋癲史》和《規訓與懲罰》的認識論前提。
無論是對待瘋癲還是對待罪犯,現在不再是壓制和消滅,而是改造和矯正。權力不是在抹去一種主體,而是創造出一種主體。對主體的考察,存在着多種多樣的方式:在經濟學中,主體被置放在生產關係和經濟關係中;在語言學中,主體被置放在表意關係中;而福柯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將主體置放於權力關係中。主體不僅受到經濟和符號的支配,它還受到權力的支配。對權力的考察當然不是從福柯開始,但是,在福柯這裏,一種新權力支配模式出現了,它針對的是人們熟悉的權力壓抑模式。壓抑模式幾乎是大多數政治理論的出發點:在馬克思及其龐大的左翼傳統那裏,是階級之間的壓制;在洛克開創的自由主義傳統那裏,是政府對民衆的壓制;在弗洛伊德,以及試圖將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結合在一起的馬爾庫塞和賴希那裏,是文明對性的壓制;甚至在尼采的信徒德勒茲那裏,也是社會編碼對慾望機器的壓制。
事實上,統治壓抑模式是諸多的政治理論長期信奉的原理,它的主要表現就是司法模式——政治—法律就是一個統治和壓制的主導機器。因此,20世紀以來各種反壓制的口號就是解放,就是對統治、政權和法律的義無反顧的顛覆。
而福柯的權力理論,就是同形形色色的壓抑模式針鋒相對,用他的說法,就是要在政治理論中砍掉法律的頭顱。這種對政治—法律壓抑模式的質疑,其根本信念就是,權力不是令人窒息的壓制和抹殺,而是產出、矯正和造就。權力在製造。
在《性史》第一卷《認知意志》中,福柯直接將攻擊的矛頭指向壓制模式:在性的領域,壓制模式取得了廣泛的共識,但福柯還是挑釁性地指出,性與其說是被壓制,不如說是被權力所造就和生產:與其說權力在到處追逐和捕獲性,不如說權力在到處滋生和產出性。一旦將權力同壓制性的政治—法律進行剝離,或者說,一旦在政治法律之外談論權力,那麼,個體就不僅僅只是被政治和法律的目光所緊緊地盯住,進而成爲一個法律主體;相反,他還受制於各種各樣的遍佈於社會毛細血管中的權力的鑄造。個體不僅僅被法律塑形,而且被權力塑形。
因此,福柯的政治理論,絕對不會在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傳統中出沒。實際上,福柯認爲政治理論長期以來高估了國家的功能。國家,尤其是現代國家,實際上是並不那麼重要的一種神祕抽象。在他這裏,只有充斥着各種權力配置的具體細微的社會機制 ——他的歷史視野中,幾乎沒有統治性的國家和政府,只有無窮無盡的規訓和治理;幾乎沒有中心化的自上而下的權力的巨大壓迫,只有遍佈在社會中的無所不在的權力矯正;幾乎沒有兩個階級你死我活抗爭的宏大敘事,只有四處湧現的權力及其如影隨形的抵抗。無計其數的細微的權力關係,取代了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普遍性的抽象政治配方。對這些微末的而又無處不在的權力關係的耐心解剖,毫無疑問構成了福柯最引人注目的篇章。
這是福柯對十七八世紀以來的現代社會的分析。這些分析佔據了他學術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同時,這也是福柯整個譜系學構造中的兩個部分。《詞與物》和《臨牀醫學的誕生》討論的是知識對人的建構,《規訓與懲罰》和《古典時代的瘋癲史》關注的是權力對人的建構。不過,對於福柯來說,他的譜系研究不只是這兩個領域,“譜系研究有三個領域。第一,我們自身的歷史本體論與真理相關,通過它,我們將自己建構爲知識主體;第二,我們自身的歷史本體論與權力相關,通過它,我們將自己建構爲作用於他人的行動主體;我們自身的歷史本體論與倫理相關,通過它,我們將自己建構爲道德代理人。”顯然,到此爲止,福柯還沒有探討道德主體,怎樣建構爲道德主體?什麼是倫理?“你與自身應該保持的那種關係,即自我關係,我稱之爲倫理學,它決定了個人應該如何把自己構建成爲自身行動的道德主體。”這種倫理學,正是福柯最後幾年要探討的主題。
在最後不到10年的時間裏,福柯轉向了倫理問題,轉向了基督教和古代。爲什麼轉向古代?福柯的一切研究只是爲了探討現在——這一點,他從康德關於啓蒙的論述中找到了共鳴——他對過去的強烈興趣,只是因爲過去是現在的源頭。他試圖從現在一點點地往前逆推:現在的這些經驗是怎樣從過去轉化而來?這就是他的譜系學方法論:從現在往前逆向回溯。在對17世紀以來的現代社會作了分析後,他發現,今天的歷史,今天的主體經驗,或許並不僅僅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而是一個更加久遠的歷史的產物。因此,他不能將自己限定在對十七八世紀以來的現代社會的探討中。
對現代社會的這些分析,毫無疑問只是今天經驗的一部分解釋。它並不能說明一切。這正是他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差異所在。事實上,十七八世紀的現代社會,以及現代社會湧現出來的如此之多的權力機制,到底來自何方?他抱着巨大的好奇心以他所特有的譜系學方式一直往前逆推,事實上,越到後來,他越推到了歷史的深處,直至晚年抵達了希臘和希伯來文化這兩大源頭。
這兩大源頭,已經被反覆窮盡了。福柯在這裏能夠說出什麼新意?不像尼采和海德格爾那樣,他並不以語文學見長。但是,他有他明確的問題框架,將這個問題框架套到古代身上的時候,古代就以完全的不同的面貌出現 ——幾乎同所有的既定的哲學面貌迥異。福柯要討論的是主體的構型,因此,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之所以受到關注,只是因爲它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塑造主體。
只不過是,這種主體塑形在現代和古代判然有別。我們看到了,17世紀以來的現代主體,主要是受到權力的支配和塑造。但是,在古代和基督教文化中,權力所寄生的機制並沒有大量產生,只是從17世紀以來,福柯筆下的學校、醫院、軍營、工廠以及它們的集大成者監獄纔會大規模地湧現,所有這些都是現代社會的發明和配置(這也是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的探討)。同樣,也只是在文藝復興之後的現代社會,語文學、生物學、政治經濟學等關於人的科學,纔在兩個多世紀的漫長曆程中逐漸形成。在古代,並不存在這如此之繁多而精巧的權力機制的鍛造,也不存在現代社會如此之煩瑣的知識型和人文科學的建構,那麼,主體的塑形應該從什麼地方着手?
正是在古代,福柯發現了道德主體的建構模式——這也是他的整個譜系學構造中的第三種主體建構模式。這種模式的基礎是自我技術:在古代,既然沒有過多的外在的權力機制來改變自己,那麼,更加顯而易見的是自我來改變自我。這就是福柯意義上的自我技術:“個體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幫助,進行一系列對他們自身的身體及靈魂、思想、行爲、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達成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通過這樣的自我技術,一種道德主體也因此而成形。
這就是古代社會塑造主體的方式。在古代社會,人們自己來改造自己,雖然這並不意味着不存在外在權力的支配技術(事實上,城邦有它的法律);同樣,現代社會充斥着權力支配技術,但並不意味不存在自我技術(波德萊爾筆下的浪蕩子就保有一種狂熱的自我崇拜)。這兩種技術經常結合在一起,相互應用。有時候,權力的支配技術只有藉助於自我技術才能發揮作用。不僅如此,這兩種技術也同時貫穿在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並在不斷地改變自己的面孔。古代的自我技術在現代社會有什麼樣的表現方式?反過來也可以問,現代的支配技術,是如何在古代醞釀的?重要的是,權力的支配技術和自我的支配技術是否有一個結合?這些問題非常複雜,但是,我們還是可以非常圖式化地說,如果在70年代,福柯探討的是現代社會怎樣通過權力機制來塑造主體,那麼,在這之後,他着力探討的是古代社會是通過怎樣的自我技術來塑造主體,即人們是怎樣自我改變自我的?自我改變自我的目的何在?技術何在?影響何在?也就是說,在古代存在一種怎樣的自我文化?從希臘到基督教時期,這種自我技術和自我文化經歷了怎樣的變遷?這就是福柯晚年要探討的問題。
事實上,福柯從兩個方面討論了古代的自我文化和自我技術。一個方面是,福柯將自我技術限定在性的領域。即古代人在性的領域是怎樣自我支配的。這就是他的《性史》第二卷《快感的運用》和第三卷《關注自我》要討論的問題。對於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時代的希臘人而言,性並沒有受到嚴厲的壓制,並沒有什麼外在的律法和制度來強制性地控制人們的慾望,但是,人們正是在這裏表現出一種對快感的主動控制,人們並沒有放縱自己。爲什麼在一個性自由的環境中會主動控制自己的慾望和快感?對希臘人而言,這是爲了獲得一種美的名聲,創造出個人的美學風格,賦予自己以一種特殊的生命之輝光:一種生存美學處在這種自我控制的目標核心。同時,這也是一種自由的踐行:人們對自己慾望的控制是完全自主的,在這種自我控制中,人們獲得了自由:對慾望和快感的自由,自我沒有成爲慾望和快感的奴隸,而是相反地成爲它們的主人。因此,希臘人的自我控制恰好是一種自由實踐。這種希臘人的生存美學,是在運用和控制快感的過程中來實現的,這種運用快感的技術,得益於希臘人勤勉的自我訓練。我們看到,希臘人在性的領域所表現出來的自我技術,首先表現爲一種生活藝術。或者也可以反過來說,希臘人的自我技術,是以生活藝術爲目標的。但是,在此後,這種自我技術的場域、目的、手段和強度都發生了變化,經過了羅馬時期的過渡之後,在基督教那裏已經變得面目全非。
在基督教文化中,性的控制變得越來越嚴厲了,但是,這種控制不是自我的主動選擇,而是受到聖律的脅迫;自我技術實施的性領域不再是快感,而是慾望;不是創造了自我,而是摒棄了自我;其目標不是現世的美學和光輝,而是來世的不朽和純潔。雖然一種主動的禁慾變成了一種被迫的禁慾,但是,希臘人這種控制自我的禁慾實踐卻被基督教借用了;也就是說,雖然倫理學的實體和目標發生了變化,
但是,從希臘文化到基督教文化,一直存在着一種禁慾苦行的自我技術:並非是一個寬容的希臘文化和禁慾的基督教文化的斷裂,相反,希臘的自我技術的苦行通過斯多葛派的中介,延伸到了基督教的自我技術之中。基督教的禁慾律條,在希臘羅馬文化中已經萌芽了。
在另外一個方面,自我技術表現爲自我關注。它不只限定在性的領域。希臘人有強烈的關注自我的願望。這種強烈的願望導致的結果自然就是要認識自我:關注自我,所以要認識自我。希臘人的這種關注自我,其重心、目標和原則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在蘇格拉底那裏,關注自我同關注政治、關注城邦相關;但是在希臘文明晚期和羅馬帝政時代,關注自己從政治和城邦中抽身出來,僅僅因爲自己而關注自己,與政治無關;在蘇格拉底那裏,關注自己是年輕人的責任,也是年輕人的自我教育;在羅馬時期,它變成了一個普遍原則,所有的人都應當關注自己,並終其一生。最重要的是,在蘇格拉底那裏,關注自己是要發現自己的祕密,是要認識自己;但在後來的斯多葛派那裏,各種各樣的關注自己的技術(書寫、自我審察和自我修煉等),都旨在通過對過
去經驗的回憶和辨識,讓既定真理進入主體之中,被主體消化和吸收,使之爲再次進入現實做好準備——這決不是去發現和探討主體的祕密,而是去改造和優化主體。而在基督教這裏,關注自己的技術,通過對罪的懺悔、暴露、坦承和訴說,把自己傾空,從而放棄現世、婚姻和肉體,最終放棄自己。也就是說,基督教的關注自己卻不無悖論地變成了棄絕自己,這種棄絕不是爲了進入此世的現實,而是爲了進入另一個來世現實。同“性”領域中的自我技術的歷史一樣,關注自我的歷史,從蘇格拉底到基督教時代,經過斯多葛派的過渡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我們正是在這裏看到了,西方文化經歷了一個從認識自己到棄絕自己的漫長階段。到了現代,基督教的懺悔所採納的言詞訴說的形式保留下來,不過,這不再是爲了傾空自我和摒棄自我,而是爲了建構一個新的自我。這就是福柯連續三年(1980、1981、1982)在法蘭西學院的系列講座《對活人的治理》《主體性和真理》以及《主體的解釋學》所討論的問題。
不過,在西方文化中,除了關注自我外,還存在大量的關注他人的現象。福柯所謂的自我技術,不僅指的是個體改變自我,而且還指的是個體在他人的幫助下來改變自我——牧師就是這樣一個幫助他人、關注他人的代表。他關心他人,並且還針對着具體的個人。它確保、維持和改善每個個體的生活。這種針對個體並且關心他人的牧師權力又來自哪裏?顯然,它不是來自希臘世界,希臘發明瞭城邦—公民遊戲,它衍生的是在法律統一框架中的政治權力,這種權力形成抽象的制度,針對着普遍民衆;而牧師權力是具體的、特定的,它針對着個體和個體的靈魂。正是在此,福柯進入了希伯來文化中。他在希伯來文獻中發現了大量的牧人和羊羣的隱喻。牧人對於羊羣細心照料,無微不至,瞭如指掌。他爲羊羣獻身,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益於羊羣。這種與城邦—公民遊戲相對的牧人—羊羣遊戲被基督教接納了,並且也做了相當大的改變:牧人—羊羣的關係變成了上帝—人民的關係。在責任、服從、認知和行爲實踐方面,基督教對希伯來文化中的牧師權力都進行了大量的修改:現在,牧人對羊的一切都要負責;牧人和羊是一種徹底的個人服從關係;牧人對每隻羊有徹底的瞭解;在牧人和羊的行爲實踐中貫穿着審察、懺悔、指引和順從。這一切都是對希伯來文化中的牧人— 羊羣關係的修改,它是要讓個體在世上以苦行的方式生存,這就構成了基督教的自我認同。不過,這種從希伯來文化發展而來,在基督教中得到延續和修正的牧師權力,同希臘文化中發展而成的政治—法律權力相互補充。前者針對着個體,後者針對着全體;前者是拯救性的,後者是壓抑性的;前者是倫理的和宗教性的,後者是法律和制度性的;前者針對着靈魂,後者針對着行爲。但是,在18世紀,它們巧妙地結爲一體,形成了一個福柯稱之爲的被權力控制得天衣無縫的惡魔國家。因此,要獲得解放,就不僅僅是要對抗總體性的權力,還要對抗那種個體化的權力。
顯然,這種牧師權力的功能既不同於法律權力的壓制和震懾,也不同於規訓權力的改造和生產,它的目標是救贖。不過,基督教發展出來的一套拯救式的神學體制,並沒有隨着基督教的式微而銷聲匿跡,而是在十七八世紀以來逐漸世俗化的現代社會中以慈善和救護機構的名義擴散開來:拯救不是在來世,而是在現世;救助者不是牧師,而變成了世俗世界的國家、警察、慈善家、家庭和醫院等機構;救助的技術不再是佈道和懺悔,而是福利和安全。最終,救贖式的牧師權力變成了現代社會的生命權力;政治也由此變成了福柯反覆講到的生命政治:政治將人口和生命作爲對象,力圖讓整個人口,讓生命和生活都獲得幸福,力圖提高人口的生活和生命質量,力圖讓社會變得安全。就此,救贖式的牧師權力成爲對生命進行投資的生命權力的一個重要來源。
以人口—生命爲對象,對人口進行積極的調節、幹預和管理,以提高生命質量爲目標的生命政治,是福柯在70年代中期的重要主題。在《性史》的第一卷《求知意志》(1976),在法蘭西學院講座《必須保衛社會》(1976),《安全、領土、人口》(1978)、《生命政治的誕生》(1979)中,他從各個方面探究生命政治的起源和特點。我們已經看到了,它是久遠的牧師權力技術在西方的現代回聲;同時,它也是馬基雅維利以來治理術的邏輯變化:在馬基雅維利那裏是對領土的治理,在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變成了對人的治理,對交織在一起的人和事的治理,也即是福柯所說的國家理性的治理:它將國家看成一個自然客體,看成是一套力量的綜合體,它以國家本身、國家力量強大作爲治理目標。這種國家理性是一種既不同於基督教也不同於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合理性,它要將國家內的一切納入到其治理範圍之內(併爲此而發展出統計學),它無所不管。顯然,要使國家強大,就勢必要將個體整合進國家的力量中;要使國家強大,人口,它的規律、它的循環、它的壽命和質量,或許是最活躍最重大的因素。人口的質量,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國家的質量。人口和國家相互強化。不僅如此,同這樣的促進自己強大的國家理性相關,國家總是處在同另外國家的對抗中,正是在這種對抗和戰爭中,人口作爲一個重要的要素而存在,國家爲了戰爭的必要而將人口納入到考量中。所有這些,都使得人口在18世紀逐漸成爲國家理性的治安目標。
國家理性的治理藝術是要優化人口,改善生活,促進幸福。最後,國家理性在18世紀中期出現了一個新的方向:自由主義的治理藝術開始了。自由主義倡導的簡樸治理同包攬一切的國家理性是如此不同,以至於它看上去像是同國家理性的決裂。自由主義針對“管得太多”的國家理性,它的要求是儘可能少的管理。它的質疑是,爲什麼要治理?治理的必要性何在?因爲自由主義的暗示是,“管得過多”雖然可能促進人們的福祉,但也可能剝奪人們的權利和安全,可以損害人們的利益,進而使人們置身於危險的生活——在整個19世紀,一種關於危險的想象和文化爆發出來。而自由主義正是
消除各種危險(疾病的危險、犯罪的危險、經濟的危險、人性墮落的危險等)的方法,它是對人們安全的維護和保障。如果說,17世紀開始發展出來的國家理性是確保生活和人口的質量,那麼,18世紀發展起來的自由主義則是確保生活的安全。“自由與安全性的遊戲,就位居新治理理性(即自由主義)的核心地位,而這種新治理理性的一般特徵,正是我試圖向大家描述的。自由主義所獨有的東西,也就是我稱爲權力的經濟的問題,實際上從內部維繫着自由與安全性的互動關係……自由主義就是通過對安全性/自由之間互動關係的處理,來確保諸個體與羣體遭遇危機的風險被控制在最低限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福柯將自由主義同樣置放在生命政治的範疇之內。
就此,十七八世紀以來,政治的目標逐漸地轉向了投資生命:生命開始被各種各樣的權力技術所包圍、所保護。福柯法蘭西學院講座的標題是:社會必須保護!生命政治,是各種治理技術、政治技術和權力技術在18世紀的一個大匯聚。由此,社會實踐、觀念和學科知識重新得以組織——福柯用一種隱喻的方式說 ——以血爲象徵的社會進入到以性爲象徵的社會,置死的社會變成了放生的社會,尋求懲罰的社會變成了尋求安全的社會,排斥和區分的社會變成了人道和救贖的社會,全面管理的社會變成了自由放任的社會。與此相呼應,對國家要總體瞭解的統計學和政治經濟學也開始出現。除此之外,福柯還圍繞生命政治,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談論18世紀發生的觀念和機制的轉變:他以令人炫目的歷史目光談到了醫學和疾病的變化、城市和空間的變化、環境和自然的變化。他在《認知意志》中精彩絕倫的(或許是他所有著作中最精彩的)最後一章中,基於保護生命和保護社會的角度,提出了戰爭、屠殺和死亡的問題——也即是,以保護生命爲宗旨的生命政治,爲什麼導致屠殺?這是生命政治和死亡政治的弔詭關係。正是在這裏,他對歷史上的各種殺人遊戲作了獨具一格的精闢分析。這些分析毫無疑問擊中了今天的歷史,使得生命政治成爲福柯在今天最有啓發性的話題。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福柯的塑造主體的模式:一種是真理的塑造(人文科學將人同時建構爲主體和客體);一種是權力的塑造(排斥權力塑造出瘋癲,規訓權力塑造出犯人);一種是倫理的塑造(也可以稱爲自我塑造,它既表現爲古代社會的自我關注,也在古代的性快感的領域中得以實踐)。後兩種塑造都可以稱爲支配技術,一種是支配他人的技術,一種是支配自我的技術,“這種支配他人的技術與支配自我的技術之間的接觸,我稱之爲治理術”。它的最早雛形無疑是牧師權力,經過基督教的過渡後轉化爲國家理性和自由主義,最終形成了現代社會的權力結構。這就是福柯對現代主體譜系的考究。
這種考究非常複雜。其起源既不穩定也不單一。它們的線索貫穿於整個西方歷史,在不同的時期,相互分叉,也相互交織;相互衝突,也相互調配。這也是譜系學的一個核心原則:起源本身充滿着競爭。正是這種來自開端的競技,使得歷史本身充滿着盤旋、回覆、爭執和喧譁。歷史,在譜系學的意義上,並不是一個一瀉千里、酣暢淋漓的故事。
顯然,在主體的譜系這一點上,福柯對任何的單一敘事充滿了警覺。馬克思將主體置於經濟關係中,韋伯和法蘭克福學派將主體置於理性關係中,尼采將主體置入道德關係中。針對這三種最重要的敘事,福柯將主體置於權力關係中。這種權力關係,既同法蘭克福學派的理性相關,也同尼采的道德相關。儘管他認爲法蘭克福學派從理性出發所探討的主題跟他從權力出發探討的主題非常接近,他的監獄羣島概念同韋伯的鐵籠概念也非常接近,並因此對後者十分尊重,但他還是對法蘭克福學派單一的理性批判持有保留態度。他探討的歷史更加久遠,絕不限於啓蒙理性之中;他的自我支配的觀點同法蘭克福學派的單純的制度支配觀點相抗衡;他並不將現代社會的個體看做是單面之人和抽象之人(這恰恰是人們對他的誤解),同樣,儘管他的倫理視野接續的是尼采,他的懲罰思想也來自尼采,但是,他豐富和補充了尼采所欠缺的制度維度,這是個充滿了細節和具體性的尼采;儘管他對權力的理解同尼采也脫不了幹係,但是,權力最終被他運用到不同的領域。正如德勒茲所說的,他把尼采射出來的箭揀起來,射向另一個孤獨的方向。
事實上,福柯的獨創性總是表現在對既定的觀唸的批判和質疑上面。針對希臘思想所發展的普遍性的政治—法律權力,福柯提出了緣自希伯來文明中針對個體的牧師權力;針對國家對民衆的一般統治技術,福柯提出了個體內部的自我技術;針對權力技術對個體的壓制,福柯提出了權力技術對個體的救助;針對着對事的治理,福柯也提出了對人口的治理;針對着否定性的權力,福柯提出了肯定性的權力;針對着普遍理性,福柯提出了到處分叉的特定理性;針對着總是要澄清思想本身的思想史,福柯提出了沒有思想內容的完全是形式化的思想史;針對着要去索取意義的解釋學,福柯提出了擯棄意義的考古學;針對着往後按照因果邏輯順勢推演的歷史學,福柯提出了往前逆推的譜系學。針對自我和他人的交往關係,福柯提出了自我同自我的關係;針對着認知自己,福柯提出了關注自己。他總是發現了歷史的另外一面,並且以其淵博、敏感和洞見將這一面和盤托出,劃破了歷史的長久而頑固的沉默。
福柯雄心勃勃地試圖對整個西方文化作出一種全景式的勾勒:從希臘思想到20世紀的自由主義,從哲學到文學,從宗教到法律,從政治到歷史,他無所不談。這也是他在各個學科被廣爲推崇的原因。或許,在整個20世紀,沒有一個人像福柯這樣影響瞭如此之多的學科。關鍵是,福柯文化歷史的勾勒絕非一般所謂的哲學史或者思想史那樣的泛泛而談,不是圍繞着幾個偉大的哲學家姓名作一番提綱挈領式的勾勒和回顧。
這是福柯同黑格爾的不同之處。同大多數歷史學家完全不一樣,福柯也不是羅列一些圍繞着帝王和政權而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在這些歷史事件之間編織穿梭,從而將它們貫穿成一部所謂的通史。在這個意義上,福柯既非傳統意義上的哲學家,也非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學家。他也不是歷史和哲學的一個奇怪的雜交。他討論的是哲學和思想,但這種哲學和思想是在歷史和政治中出沒;對於他來說,哲學就是歷史和政治的詭異交織。
不過,福柯出沒其中的歷史,是歷史學無暇光顧的領域,是從未被人賦予意義的歷史。福柯怎樣描述他的歷史?在他這裏,性的歷史,沒有性;監獄的歷史,沒有監獄;瘋癲的歷史,沒有瘋子;知識的歷史,沒有知識內容。用他的說法,他的歷史,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歷史——這是他的考古學視角下的歷史。他也不是像通常的歷史學家那樣試圖通過歷史的敘述來描寫出一種理論模式。
福柯的歷史,用他自己的說法,是真理遊戲的歷史。這個真理遊戲,是一種主體、知識、經驗和權力之間的複雜遊戲:主體正是藉助真理遊戲在這個歷史中建構和塑造了自身。
他晚年進入的希臘同之前的海德格爾的希臘完全是兩個世界,希臘不是以一種哲學起源的形象出現。在福柯這裏,並沒有一個所謂的柏拉圖主義,而柏拉圖主義無論如何是尼采、海德格爾、德里達和德勒茲都共同面對的問題。在希臘世界中,福柯並不關注一和多這樣的形而上學問題,甚至也不關注城邦組織的政治問題;儘管在希臘世界,他也發現了尼采式的生存美學,但是這種美學同尼采的基於酒神遊戲的美學並不相同,這是希臘人的自由實踐——福柯闖入了古代,但決不在前人窮盡的領域中斡旋,而是自己新挖了一個地盤。他的基督教研究的著述雖然還沒有完全面世(他臨終前叮囑,他已經寫完的關於基督教的《肉慾的告白》不能出版,現在看到他討論基督教的只有幾篇零星文章),但毫無疑問同任何的神學旨趣毫無關聯。他不討論上帝和信仰。基督教被討論,只是在信徒的生活技術的層面上,在自我關注和自我認知的層面上被討論。
他談到過文藝復興,但幾乎不涉及人的發現,而是涉及一個獨特的名爲“相似”的知識型,涉及大街上談笑風生的瘋子。他談及他所謂的古典時期(17世紀到18世紀末),他談論這個時期的理性,但幾乎沒有專門談論笛卡爾(只是在和德里達圍繞着有關笛卡爾的一個細節展開過爭論)和萊布尼茲,他津津樂道的是畫家委拉斯貴支。
作爲法蘭西學院的思想系統史教授,他對法國的啓蒙運動幾乎是保持着令人驚訝的沉默 ——即便他有專門的論述啓蒙和批判的專文,他極少提及盧梭、伏爾泰和狄德羅。而到了所謂的現代時期,他故意避免提及法國大革命(儘管法國大革命在他的內心深處無所不在,大革命是他最重要的歷史分期)。他談到了19世紀的現代性,但這個概念同主導性的韋伯的理性概念無關。他的19世紀似乎也不存在黑格爾和馬克思。他幾乎不專門談論哲學和哲學家(除了談論過尼采),他也不討論通常意義上的思想家,不在那些被奉爲經典的著述的字裏行間反覆地去爬梳。福柯的歷史主角,偏愛的是一些無名者,即便是被歷史鐫刻過名字,也往往是些聲名狼藉者。不過,相對於傳統上的偉大的歐洲姓名,福柯倒是對同時代人毫不吝惜地獻出他的致敬:不管是布朗肖還是巴塔耶,不管是克羅索夫斯基還是德勒茲。
在某種意義上,福柯寫出的是完美之書:每一本書都是一個全新的世界,無論是領域還是材料;無論是對象還是構造本身。他參閱了大量的文獻 ——但是這些文獻如此地陌生,似乎從來沒有進入過學院的視野中。他將這些陌生的文獻點燃,使之光彩奪目,從而成爲思考的重錘。有一些書是如此地抽象,沒有引文,猶如一個空中樓閣在無窮無盡地盤旋和纏繞(如《知識考古學》);有一些書如此地具體,全是真實的佈滿塵土的檔案,但是,從這些垂死的檔案的字裏行間,一種充滿激情的思想騰空而起(《規訓與懲罰》);有一些書是如此地奇詭和迥異,彷彿在一個無人經過的荒漠中發出狄奧尼索斯式的被壓抑的浪漫吶喊(《古典時代的瘋癲史》);有一些書如此地條分縷析,但又是如此艱深晦澀,這兩種對峙的決不妥協的風格引誘出一種甜蜜的折磨(《詞與物》);有一些書如此地平靜和莊重,但又如此地充滿着內在緊張,猶如波瀾在平靜的大海底下湧動(《快感的運用》)。福柯溢出了學術機制的範疇。除了尼采之外,人們甚至在這裏看不到什麼來源。但是,從形式上來說,他的書同尼采的書完全迥異。因此,他的書看起來好像是從天而降,似乎不活在任何的學術體制和學術傳統中。他彷彿是
自己生出了自己。在這方面,他如同一個創造性的藝術家一樣寫作。確實,相較於傳承,他更像是在創作和發明——無論是主題還是風格。我們只能說,他創造出一種獨一無二的風格:幾乎找不到什麼歷史類似物,找不到類似於他的同道(就這一點而言,他和尼采有着驚人的相似),儘管在他寫作之際,他的主題完全溢出了學院的範疇,但是,在今天,他開拓的這些主題和思想幾乎全面征服了學院,變成了學院內部的時尚。
他的思想閃電劈開了一道深淵般的溝壑:在他之後,思想再也不能一成不變地像原先那樣思想了。儘管他的主題征服了學院,並有如此之多的追隨者,但是,他的風格則是學院無法效仿的 ——這是他的神祕印記:這也是玄妙和典雅、繁複和簡潔、疾奔和舒緩、大聲吶喊和喃喃低語的多重變奏,這既是批判的詩篇,也是佈道的神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