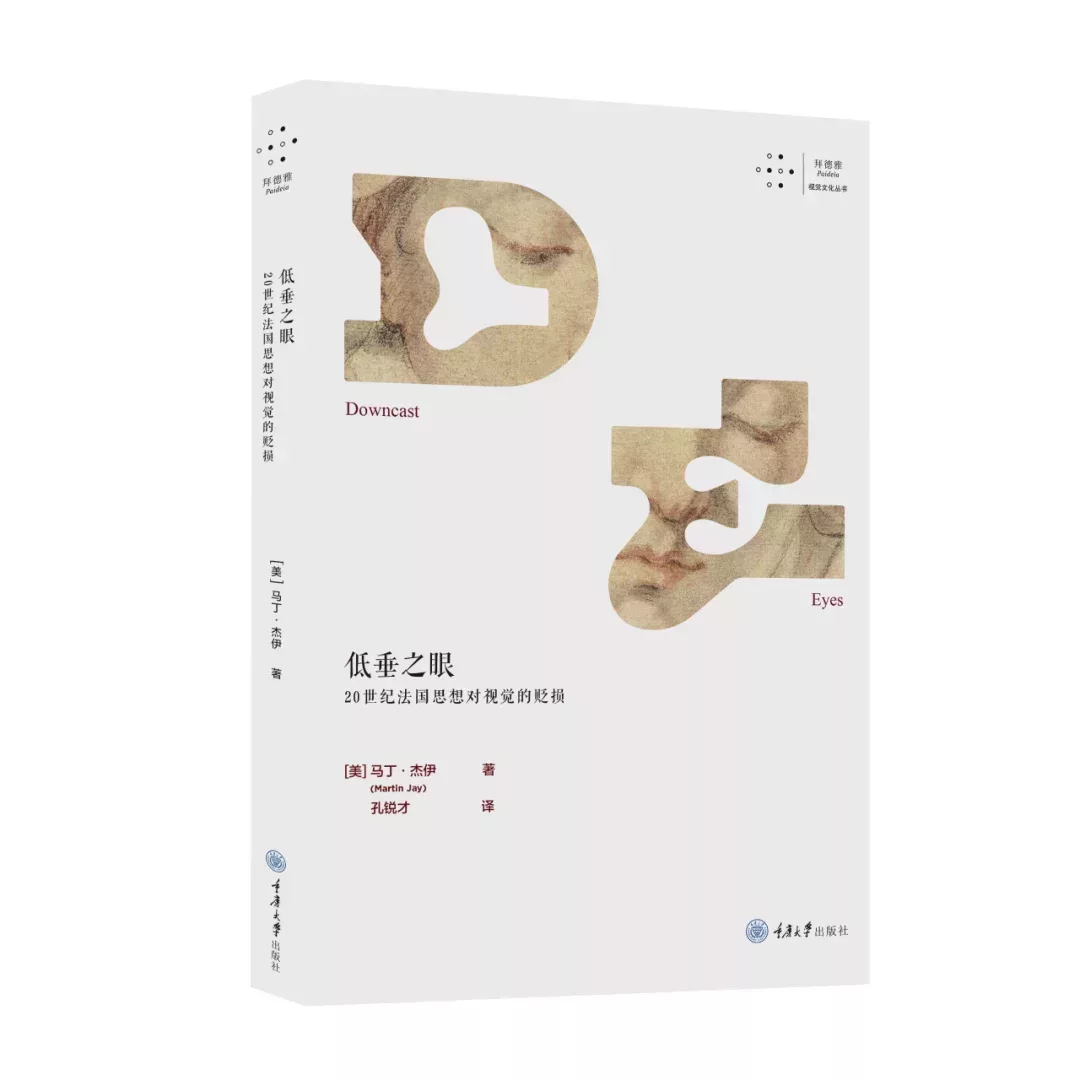
文晗 /文
毫無疑問,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以視覺爲核心的時代。當我們追求2k、4k甚至8k的電視電腦屏幕,當我們給手機配備以往只在相機上纔有的潛望長焦鏡頭,當我們越來越熟悉各種圖片編輯技術,越來越沉迷於短視頻之中時,我們所追求的無非是某種極致清晰、同時也精緻多樣的視覺效果。雖然現代技術帶給我們的是視聽綜合體驗,聽覺的享受在現代技術中也佔據着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但聽覺自身的特點似乎就決定了,它不如視覺的直觀在場那麼震撼人心。
視覺中心主義
訴諸歷史,我們會看到,這樣一種視覺的中心地位在哲學史、思想史中也是一個十分古老的現象。從柏拉圖的太陽喻、洞穴喻,到基督教中的光照說,再到笛卡爾的屈光學以及對一個透視自我的發掘,一直到被海德格爾稱爲“世界圖像時代”的現當代,視覺作爲隱喻或實指的統治地位亦隨處可見。
也正是在這一技術和思想的背景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視覺文化研究(Visual Culture Studies)成爲了西方思想界的一門顯學。當然,視覺文化研究雖然指向的是以視覺爲核心的一系列領域,如藝術史研究、圖像學研究以及各色社會批判理論,但這些研究的主旨卻並不是弘揚或強調視覺的優先性。恰恰相反,視覺文化研究在絕大多數時候都以反思那些以視覺爲核心的思想研究範式爲己任。
這或許是因爲在當代思想界中,學者們幾乎都會將光、視覺和漫長的形而上學傳統聯繫起來。因此,對視覺中心主義的批評和反思,實際上就是對某種本質主義和主體性形而上學的批評和反思。我們會看到,視覺文化研究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與對現代性的批判以及對啓蒙運動的反思聯繫在一起的。
如果將範圍限定在哲學領域的話,我們更會看到,20世紀以來,幾乎所有的哲學家在談到與視覺相關的問題時,都對其持批判態度,並將這一問題與對形而上學的批判聯繫起來。在他們看來,從柏拉圖一直到胡塞爾的形而上學傳統,都是一種以視覺和光爲核心的哲學傳統。與這種傳統相伴隨的思想,一方面將主體看作一個以視覺活動爲核心觀看着世界的主體,另一方面則將外在世界看作一個被主體的觀看活動所“表象”的客觀世界。而這些哲學家都在批判這樣一種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的同時,試圖在此基礎上重新理解主體,並由此重新理解主體與外在世界的關係。這樣一種批判性的思路,在20世紀以來的法國哲學中表現得尤爲明顯。
批判視覺之含混
馬丁·傑伊(Martin Jay)的名著《低垂之眼:20世紀法國思想對視覺的貶損》(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就是一本論述當代法國哲學對“視覺中心主義”(ocularcentric)批判的哲學史、思想史著作。此書卷帙浩繁、牽涉衆多,作者在前兩章中勾勒了從古希臘到笛卡爾再到啓蒙運動對視覺核心地位的不斷提升和強調,並以此爲背景,在此後的八章中詳細論述了當代法國哲學對這一傳統的批判。書中涉及當代法國哲學幾乎所有的重要人物,從開端處的柏格森,到現象學傳統中的薩特、梅洛-龐蒂和列維納斯,從難以歸類但構成了當代法國理論另一開端的巴塔耶,到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拉康、福柯、德波、羅蘭·巴特、德勒茲、德里達、利奧塔等人。可以說,馬丁·傑伊以“低垂之眼”這一形象的說法,總括了一部以視覺問題爲核心的20世紀法國哲學史。
然而,相較於一般的以概括哲學家思想爲主的哲學史,“低垂之眼”這一主題也爲其研究帶來了不小的挑戰。其原因在於,雖然熟悉20世紀哲學的學者可能都能從中發現一條隱含着的對視覺中心主義的批評線索,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一位哲學家以專門性的主題將視覺這一問題視爲自己思想的核心。我們可以在海德格爾、薩特、梅洛-龐蒂、福柯、德勒茲、德里達甚至列奧·施特勞斯等哲學家的著作中看到他們對聽和看以及對圖像、影像、直觀等問題的討論,但沒有一個哲學家會說,他的思想主題是“聽覺優先於視覺”。在絕大部分哲學家的思想中,視覺主要是起隱喻性的作用。當然,這也與視覺作爲人的一種感覺,本身很難成爲一個哲學概念有關。尤其當我們以視覺爲核心去編織相關概念的時候,我們不禁會好奇,薩特和德勒茲、梅洛-龐蒂和巴塔耶、拉康和列維納斯,這些差異巨大的哲學家,真的是針對同一個“視覺”在加以批判嗎?這也就導致了在論述這些哲學家對視覺中心主義的批評時,對“視覺”概念的討論很難達到一般哲學概念的清晰。
更進一步我們會發現,除了貶損視覺之外,不同哲學家關於反視覺的論述,看起來相互之間好像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每個哲學家似乎都處在一種分散的點狀結構之中,而沒有被邏輯性地串聯起來。馬丁·傑伊所提到的諸多不同的哲學家,爲什麼都會共同針對視覺中心主義進行批判?這些分屬不同流派、遵循不同方法、思維方式差異巨大的哲學家,真的有某種共同的契機和目標嗎?
思想史的嚴格性
實際上我們會發現,馬丁意識到了他將要面對的問題。他在“引言”中就說道,“這個研究的重點是一種話語(discourse)”,而“話語是一團或多或少鬆散編織在一起的觀點、隱喻、斷言、偏見,它們在‘話語’這個詞的任何嚴格意義上更多知識關聯性地而非邏輯性地凝聚在一起”。可以看到,馬丁充分意識到了討論反視覺問題中的困難,雖然有許多哲學概念在類比和隱喻的意義上都與視覺相關,但視覺自身很難直接作爲一個哲學概念被加以討論。因此,這種對反視覺的研究也就很難在嚴格哲學意義上被加以論述,而只能在福柯意義上的話語結構中去加以辨析。
同時,一旦我們認同這樣一種話語分析的合理性,那麼我們可能就必須得同時接受這種話語分析相對於概念分析式寫作的含混和模糊。當然,這樣一種含混和模糊也許並不是一個致命的問題,它的合理性可能來自於給視覺提供基礎的生命和生活本身的含混和模糊。換言之,也許正如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所一再強調的,人的感覺活動本身相較於形式化的自然科學就是含糊的,這種含糊也許沒有形式科學那樣的精確性(accuracy),但並不意味它自身沒有嚴格性(rigorous)。
這種嚴格性也就意味着,要如其所是地面對其所研究的對象。要將所論述的哲學家的思想回置到其所處的時代和語境當中,同時又不能將語境和時代過分凌駕於哲學家本人所思考的問題之上。換言之,這要求研究者既要充分理解和闡明每一個不同哲學家所處的語境、所置身的時代背景、所受的思想影響,又要求其能夠把握哲學家本人的根本問題,能夠辨析哲學家的思想源流,這顯然是一個極高的要求。
馬丁無疑充分理解了這樣一種處境。他在鋪墊20世紀反視覺的史前史的敘述中,花了大量筆墨論述19世紀以來的各種視覺奇觀,從1859年奧斯曼男爵對巴黎的改造到百貨商店在歐洲城市的興起,從廣告圖像的爆炸到銀版照相法以及最早的照片PS技術的發明,從世界博覽會的誕生到各種藝術流派的產生。正是19世紀以來人類在技術上的長足進步,才構成了20世紀反視覺潮流的興起。
同時我們也會看到,馬丁在對薩特的討論中,除了強調現象學運動對薩特的影響之外,還特別強調了薩特童年喪父對其思想的影響,“一個孤兒在他缺席的父母眼睛中感到特別內疚”。再如,在對西方哲學開端時對視覺的強調中,他並沒有大而化之地認爲柏拉圖是一種典型的視覺中心主義者,而是細緻地剖析,認爲柏拉圖對一般所說的肉眼視覺持十分負面的態度,同時也導致其對模仿藝術的厭惡。這種相對客觀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即便如此,馬丁的語境分析相對來說還是太少了,大量論述仍然是圍繞着哲學家們的觀點展開,同時也有不小的篇幅貢獻給了法國反視覺論者們的德國前輩。與此同時,他在考察哲學家們思想的同時,似乎又有意不去直接敘述哲學家們的相互關係。比如,就柏格森、薩特、梅洛-龐蒂甚至列維納斯、德里達來說,他們對於視覺中心主義的批評實際上比較明顯地偏重於哲學層面,而拉康、阿爾都塞、福柯和德波等人的批判則更多與政治、社會以及權力話語相聯繫。這就又回到了那個根本性問題:一種好的思想史研究到底應該是怎樣的?
從馬丁有關“低垂之眼”的敘述中,筆者時常會聯想到劍橋思想史學派的風格。佩蒂特在給波考克《馬基雅維利時刻》一書的評價中曾說,“《馬基雅維利時刻》提出了上千個問題,解決了兩三個,給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們留下了幾十年的工作”。問題繁複、歧路百出的感覺,也許是思想史研究成功的標誌,那些看似清晰的思想源流也許是略過了太多歷史曲折的後果。當然,即便如此,類似於福柯式的、將洞見和語境相結合的方式仍然是思想史研究應該效仿的對象。只不過,馬丁常有,而福柯不常有,能夠對前者提出如此之高的要求,也許已經說明瞭其不可磨滅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