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馬斯·潘恩的《常識》是改變美國的20本書之一,還位居榜首。
潘恩的一生就是一部傳奇,他啓蒙了美、英、法三個國家的革命。然而,他很快又被三個國家拋棄。法國人嫌棄他太保守,要把他送上斷頭臺,他幫助大革命起草的憲法條款,最後全部被刪除。英國人嫌棄他太激進,對他進行了缺席審判,開除了他的國籍,讓他永遠無法回到故土。美國人嫌棄他不安分,他被迫辭去議會的職務,美國人只給了他一個莊園。
他來到這個世界之時,是個貧民,離開這個世界時,還是一貧如洗。他完全可以用手中的筆讓自己成爲百萬富翁,因爲在那個時代,沒有一個人的作品像他一樣可以長時間霸榜暢銷書。可是他分文不取,把全部稿酬都捐給了英美法三國的民主事業。

潘恩一生,命途多舛,或許只有盧梭與之有一拼,但盧梭死後很快就被捧上了神壇,而潘恩死後一百多年才迎來正名。
最初的北美,對於獨立的合法性爭論不休。最先是爲了抗稅,口號是“無代表、不納稅”,但英國議會做出了妥協。後來是爲了自由民主,口號是“不自由、毋寧死”,但彼時的北美,識字率不足5%,經濟基礎也是農業,農民對於知識分子爭取自由民主的號召嗤之以鼻。
所以如果北美的獨立鬥爭僅僅停留在這一層認識上,儘管最終還會取勝,但結局很可能是——趕走了英國總督,卻迎來了美國國王。
就在這時,潘恩發表了《常識》。他不僅僅呼籲獨立,而且還喊出了革命的新口號:讓我們爲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以這一口號爲標誌,美國的獨立戰爭就不再同於歷史上所有的農民起義,而是獲得了全新的含義。
北美人民從此意識到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他們不僅僅是爲了十三州而戰,而是爲人類開創全新的政體模式。

《常識》一齣,震聾發聵,猶如劃破黑夜的閃電。不出三個月,便風行北美大陸。當時200萬北美居民中,幾乎每一個成年男人都讀過或者聽過這本小冊子。當時的北美人民,如果有幸擁有一本藏書,那自然是《聖經》,可如果擁有第二本,那便是《常識》。
他用一本僅50頁紙的小冊子《常識》,劃破了人類思想的夜空,深遠影響了人類關於權利和自由的認識,也永久性地改變了人類未來的政治格局。
《常識》原本定名爲“簡單的真理”,但最後起名爲《常識》。因爲潘恩常說:真理如同常識一樣,簡單但有力量。
第一、關於社會和政府
《常識》開宗明義的指出,社會和政府不能混爲一談。任何形態的社會均是幸福之源,而政府即使處於最佳的狀態也只是必要之惡,最差的狀態則是無法忍受之惡。
人類建立政府的初衷是爲了保障安全和自由,這裏的安全不單單是人身安全,還有財產安全。因此人們上交部分財產,“讓渡”部分權利來建立政府。所以能夠實現目的且花費最少、福利最豐的政府,必然是最佳選擇。
《常識》首倡共和:北美獨立之後,建立共和政體。在《常識》勾勒的國家政體藍圖裏,大陸會議、各州議會或制憲會議的成員,要經過人民的授權,才能擁有真正合法的權力。

第二、關於國王和權貴
《常識》火力全開:人人生而平等,可爲什麼有這麼一個物種,生來就比他人高貴?
《常識》尖銳地指出:當我們扯掉權貴的遮羞布,追溯他們的發家史,便能發現,他們的先輩不過是某個強盜團夥的賊魁。
《常識》毫不留情的指出了君主的悖論:不受監督的國王不可信,國王的地位註定其遠離塵囂,而其職責卻要求其洞悉世事。因爲權貴的生活圈子與普羅大衆的世界有着本質區別,他們很少有機會知曉民衆真正的需求和利益。所以當那些權貴子孫掌權時,他們通常是整個國家中最無知且最不適宜掌權的人。
《常識》語重心長的對人們說:我們無權替後世的子子孫孫認領君主。
就這樣,潘恩用一己之力,把國王拉下了神壇,也撕碎了那些貴族老爺們的權威。
第三、關於法治和理想
《常識》一針見血的指出:在專制政府中,國王就是法律,而在自由的國家中,法律纔是國王。每個國家的發展史中,僅有一次機會,但大部分國家不能把握這一良機自主制定法律。
《常識》發出了號召:讓我們爲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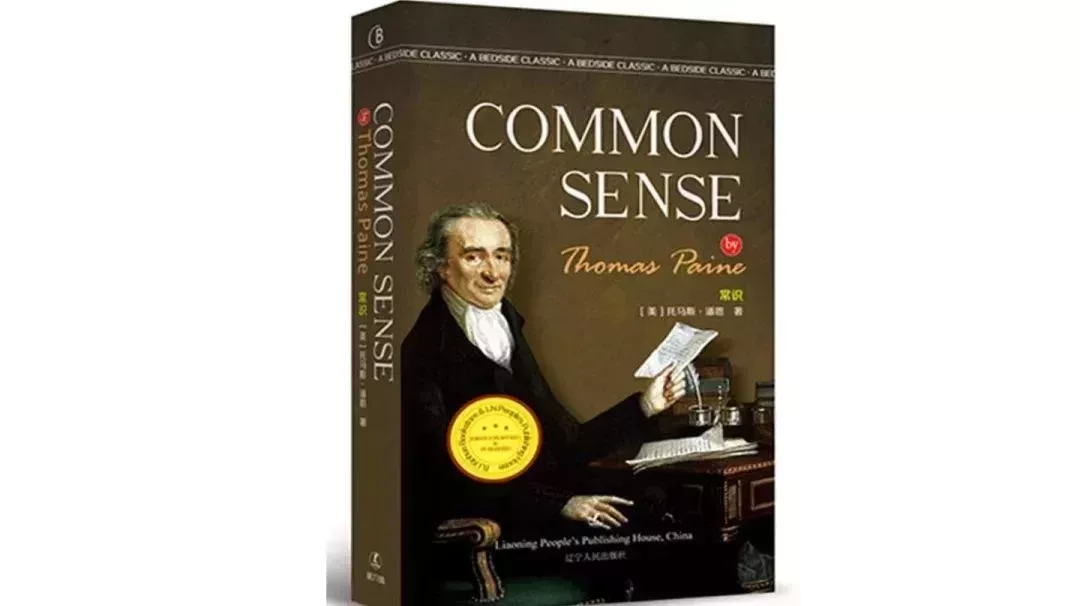
潘恩一生都在戰鬥,他知道《常識》肯定會引起一些人的反對,所以他在《常識》中寫道:不認可這些簡潔真理的人,不外乎四類,一是從舊政體中獲益的人,二是無法看清真相且判斷力低下的人,三是不願承認真相的偏執之人,四是把世界想象得過分美好的人。
《常識》不僅僅是引領了一個大陸的獨立解放運動,最關鍵的是指導建立了具有示範意義的政治制度,它把北美人的獨立和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嶄新時代聯繫在了一起。
時隔200多年,無數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仍在盛讚這本書。可悲的是,兩百多年前的常識,如今還要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