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家務是指那些叫不上名字,在生活中容易被忽略或是不被在意,但卻重複、毫無成就感,且不得不幹的勞動。
比如裝上新垃圾袋、整理玄關散落的鞋子、將衣物從洗衣機裏取出來等等。
經營一個家庭,理應由每個家庭成員共同承擔,而實際上在大多數家庭裏,這些隱形家務,都被妻子們“默契”地承擔了下來。我們長久以來聽到的,類似是這樣的話:
“男人是做不好家務的。”
“女人就該做好賢內助。”
“小姑娘不學着做家務,長大以後無法做一個合格的妻子。”
隱形家務類似的問題不得不引發我們對於女性處境的思考,事實上,不光是隱形家務,女性從出生開始,就會遭遇一系列的不公平和歧視,韓國作家趙南柱曾寫過一本書《82年生的金智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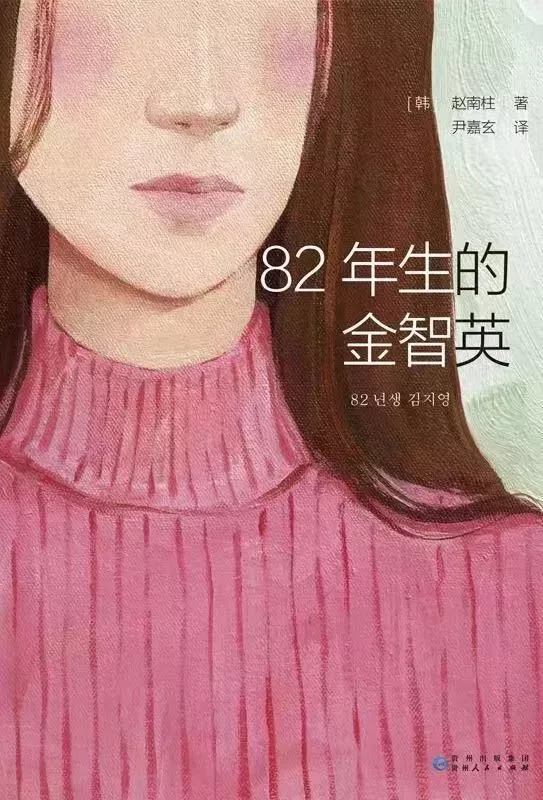
趙南柱以質樸、日常的敘事風格,讓書裏的主角“金智英”成爲了女性話題的代名詞,呈現了一位36歲平凡女性如履薄冰的一生,也讓無數普通女性從中找到了自己的聲音。

《82年生的金智英》就像紀錄片一樣,完整還原了一個女性一生中所遭遇的,日積月累的性別歧視。
你只要翻開,或多或少都能想起自己曾經的某段經歷。我們集中講述金智英的故事,你會有很多次不舒服卻特別熟悉的感受,這個過程也是在喚醒我們自身的女性意識。
金智英出生在一個非常傳統的東亞家庭,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家庭主婦,她上面有個大她兩歲的姐姐,下面有個小她五歲的弟弟,家裏還有一位重男輕女的定海神針,奶奶。
媽媽因爲連生兩胎女兒,哭着向奶奶鞠躬道歉。結果三胎髮現又是女孩,媽媽懷抱着一絲希望,去金智英爸爸那裏小心試探,結果換來一句特別寒心的話,“少烏鴉嘴了,別淨說些觸黴頭的話”。

她哭了一整晚,然後把孩子做掉了。幾年後,母親終於懷上了一個男孩,也就是金智英的弟弟。可想而知,金智英從小就在這個家裏經受着生而爲女的差別待遇。
家裏盛米飯的順序都是有講究的:爸爸、弟弟、奶奶,順序絕對不能亂。弟弟的襪子、衛生衣褲永遠都是成雙成對的,但金智英和姐姐的總是湊不成一對。好東西都是弟弟的,姐姐們絕不允許侵犯。
金智英最難忘的記憶就是因爲偷喫弟弟的奶粉,後背被奶奶狠狠拍了一掌,其實她不過是趁媽媽泡奶粉的時候,用手指蘸了不小心灑在桌上的零星半點。
小學是金智英接觸的第一個小型社會,她開始感受到家庭以外的世界,原來也存在赤裸裸的性別不公。被鄰座男同學惡作劇,甚至升級到霸凌的程度,可媽媽和姐姐只說那是玩笑,不必當真。

後來有一次,男生闖禍被老師抓了個現行,老師雖然懲罰了對方,卻拍了拍金智英的肩膀,說:“他是因爲喜歡你啊。”
上高中以後,金智英又遭遇了另一種困境——性騷擾。她在公交地鐵上會遇到變態對自己動手動腳,但她從不敢吭聲,只能忍受迴避,然後逃離。有一次在上完補習班回家的路上,她被一個男生尾隨。
這件事把金智英嚇壞了,可父親不僅沒有安慰她,反而嚴厲地斥責了她一頓。那些話刺耳又熟悉:你爲什麼到那麼遠的地方上補習班?爲什麼裙子那麼短?爲什麼跟陌生人說話?
這是不是像極了這些年,每次有女孩遇害的新聞登上熱搜,網上那些苛責受害人的言論。在這樣的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下長大的金智英們,遇到侵犯不再敢於求救,甚至在被傷害後會覺得羞恥。
大三求職季,金智英發現韓國女性是很難進入大企業的。書裏提到一項針對韓國百大企業進行的問卷調查,發現2005年,也就是金智英大學畢業的這一年,女性錄取率只有29.6%,而且這個數值在當時還是用來說明女性的社會地位得到大幅提升的。
短短20年的人生,金智英把一個女性會經歷的所有不公統統經歷了一遍:重男輕女、受害者有罪論、職場歧視、性騷擾……緊接着,她又開始在婚姻裏歷劫。

金智英遇到了她的老公鄭代賢,兩個人戀愛結婚,不久後公婆開始催生。金智英甚至都還沒有把“暫時不打算生小孩”說出口,婆婆已經斷定是這個兒媳婦出了問題:年紀太大,身形太瘦,手腳冰冷肯定是血液循環不良,下巴上長了顆痘那估計是子宮不好……
總之,他們似乎已經得出結論,問題就是出在金智英身上。丈夫也勸她:“反正遲早要生孩子,趁我們還年輕,就生一個吧。”語氣輕鬆的樣子好像是在說“我們去買條魚吧”。
男性無法理解女性恐懼生孩子的原因,他們覺得這就是一個女人的天性。金智英沒有放棄,她試圖和丈夫溝通“生孩子如何照顧、自己是否能繼續上班”等等問題。
可鄭代賢又搞不明白了,他勸金智英:“你怎麼老想着自己失去什麼,你獲得了那麼多啊!”
金智英得到了特別的優待嗎?真的懷孕之後,在下班晚高峯的地鐵上,智英扶着痠疼的腰站在車門旁,旁邊位置上的女大學生起身讓座,卻故意撞了一下她的肩膀,還說了句:“肚子都大成這樣了,竟然還坐地鐵出來賺錢, 真不知道在想什麼。”
你看,不同年齡段的女性之間都難以感同身受,更別說男女之間了。預產期臨近,智英與先生商量未來誰帶孩子,他們列了很多方案,最終得出並不意外的結論:夫妻之中有一人放棄工作專職帶小孩。而那個人肯定是金智英。

不僅僅是因爲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風氣,還包括兩個人的收入對比,照顧孩子的細緻程度。所有的考量把金智英推回了家庭內部,而這些理由偏偏還顯得如此理性和划算。
其實我女兒剛出生的時候,家裏有一位半日制的家政阿姨處理家務,還有一位育兒嫂專門帶孩子,按理說我簡直命太好,完全不要操心吧?不是的。首先,我沒有放棄工作,所以工作上不能划水。
其次,阿姨處理的是“具體家務”,不包括“規劃和安排”。孩子的教育、服裝、奶粉、防疫針不會自動跳出,買菜做飯、衣食住行都是瑣碎。
另外,還有處理家裏老人和阿姨之間的各種矛盾,有段時間育兒阿姨走馬燈一樣換,我成了朋友裏的“家政中介能手”,還做了一張家政公司分析表。
最後,主婦全年無休,阿姨放假時,就是主婦上崗時,這種無縫對接的生活,密度實在太大、太消耗了。另一方面,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一點在於,主婦承擔的勞動不被男性和整個社會看見和計算在內。
這兩年在中國特別受歡迎的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在上世紀80年代,從歐美引入了“無償勞動”的概念。她提出,主婦在家中做的家務、看護、育兒等工作放到經濟市場中,是可以獲得報酬的,而在家庭環境下,這種勞動變成被迫的無償勞動。
上野還解釋了爲什麼家務是無償勞動,以及怎麼判斷一個行爲是不是勞動。她提出了一個很簡單的定義,叫做“第三者標準”。
意思是,能夠轉移給第三者的活動就是勞動,而大部分家務是可以交由他人做的。她讓我們意識到,其實女性一直是在白乾活。

趙南柱還有個小心思藏在這本書裏,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她抹去了金智英丈夫以外的所有男性角色的名字,所以我們在書裏只能看到“父親”“學長”“上司”“弟弟”……
這些指代身份的詞,這其實是趙南柱對於性別不平等的一種反抗。趙南柱在書里正是用這樣一種反諷的方式,來表達整個社會對於女性的忽視。
正如我們在日常生活裏,看到無數女性被冠以誰的太太、誰的母親、誰的奶奶,像是無法獨立存在的附屬品,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聲音被淹沒,形象也變得模糊。
這是屬於作者趙南柱的女性意識,小說裏的金智英也很早就獲得了這種發現性別不公的意識。實際上,正是因爲擁有女性意識,她纔會覺得處處不舒服、不自在。
在金智英的原生家庭裏,三代女性都在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性別歧視,但真正的差別就在於這種女性自覺。從奶奶開始,她生活的時代充滿了戰爭、疾病、飢餓而不幸喪命,能不能存活下來都是問題。
但奶奶特別能幹,不僅替人種田、做生意、做家務,還把自己家打理得很好。咬牙苦撐,還養大了四個兒子。而金智英的爺爺一輩子從未徒手抓過一把泥土,始終養尊處優。
可是,奶奶從未對爺爺有過任何怨言,她發自真心地認爲,丈夫只要不在外偷腥,不動手打妻子,就已經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了。

在我看來,正是因爲有金智英在前,讓很多女性覺察到了各種性別歧視的普遍性,今天更加深刻的“上野熱”才擁有了比較大的施展空間。
趙南柱說,“曾經我以爲小說沒什麼意義,只是自說自話,但現在我也有了自信,原來小說也可以促進社會的變化。”
這句話也讓我想到上野在《始於極限》裏的一段自白,她寫,“儘管我沒有孩子,但活到這個年紀也產生了類似的念頭,想把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交到下一代手裏,而不是跟他們道歉說:‘對不起啊,我們把世界搞成了這副樣子’。”
任何進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願我們有覺察、有勇氣,更有責任心,把一個對女性更友好的時代交付到下一代人手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