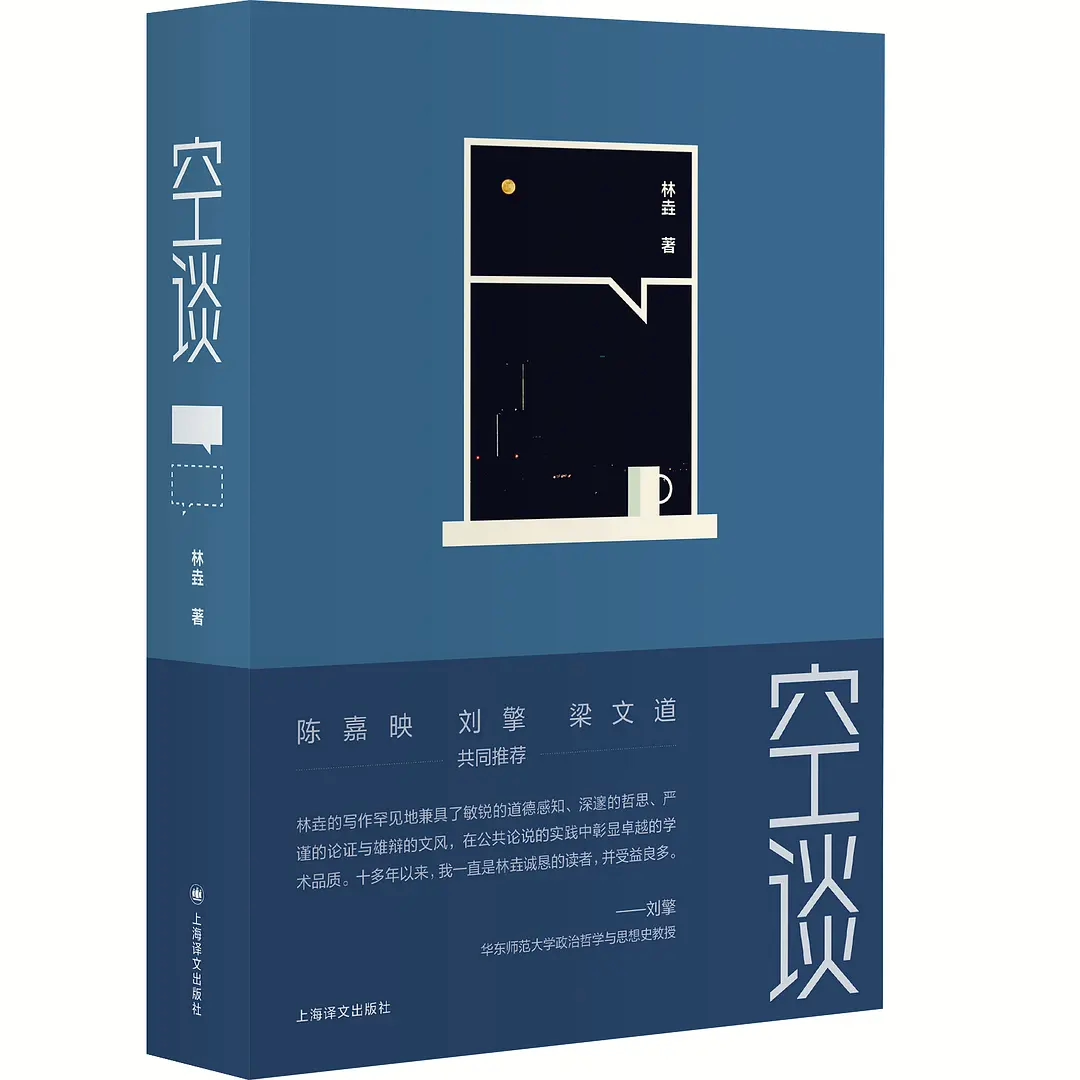感謝世界上最瞭解我的人舉賢不避親,在百忙之中爲《空談》寫了篇書評:P
2010年暑假,我和三土碰巧在同一個讀書小組裏討論《韓非子》。那時我還在北大讀碩士,他已經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他是讀書小組裏發言最積極的人,旁徵博引,有理有據,而且風趣幽默,我以爲他是一個外向陽光的人——直到我們在一起之後,我才發現那是個讓人好笑又好氣的誤會。日常生活中的三土安靜內斂,不喜社交,尤其迴避站在聚光燈下;但他告訴朋友時,別人往往不信,因爲他們看到的總是他在公共場合侃侃而談的樣子,聽他聊起各種話題,文學、電影、政治、哲學……三土今年出版了一本書,叫《空談》。我覺得這名字起得好,既讓我想起他認真說話時的精氣神,又隱隱透露了他心底“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的無奈。或者倒過來說吧:“空談”既是對書生百無一用的自嘲,同時在這自嘲背後,又下意識地體現出對書中那種細緻的社會觀察、嚴謹的倫理探究和純粹的智性之樂的內在價值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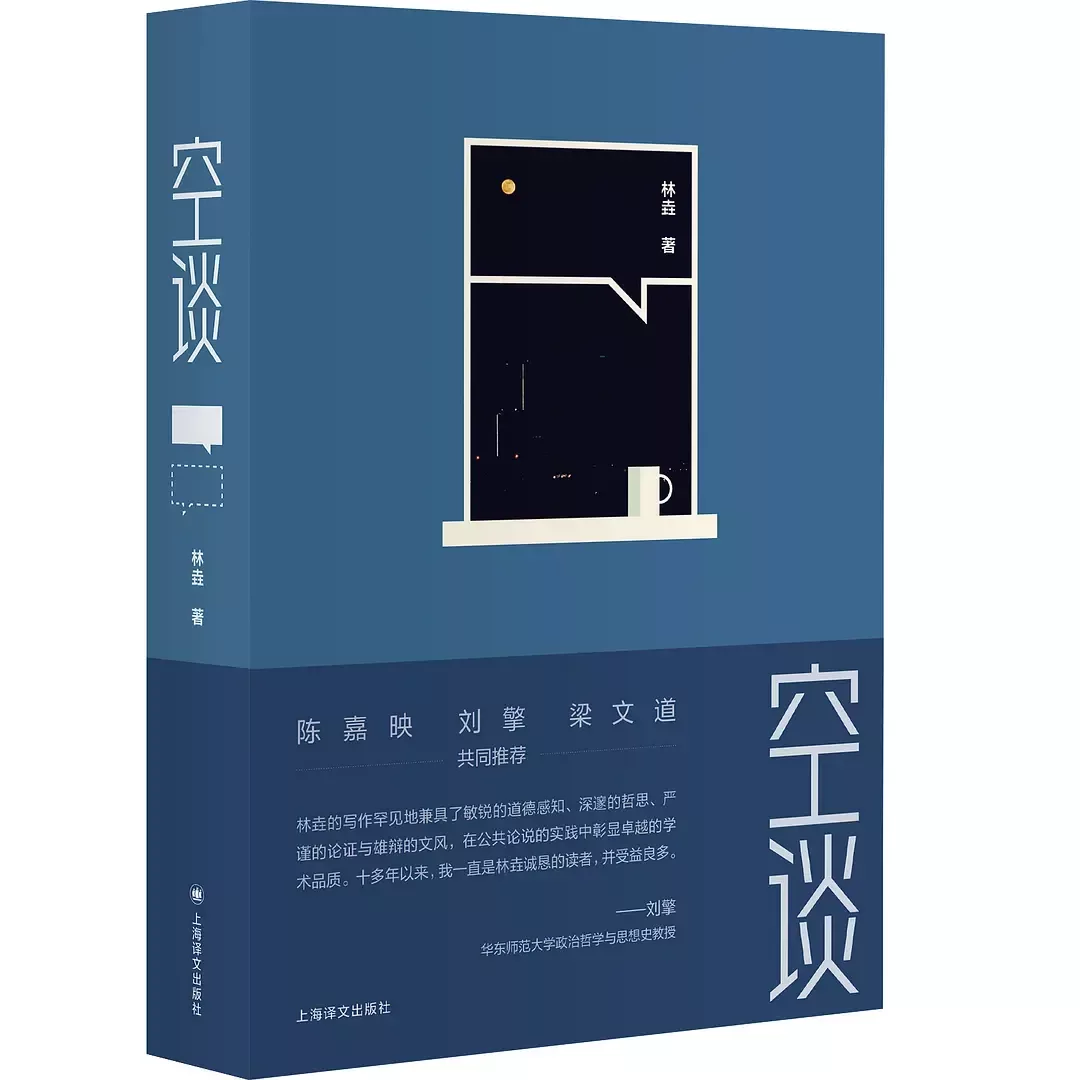
一、攪夢頻勞西海月
《空談》收錄的大多數文章寫在我和三土共同生活的十幾年中。早期幾篇關於美國政治的評論,比如《美國大選暗戰》、《金錢與選舉》等等,寫於我們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對面一間狹小的公寓裏。女兒才幾個月,三土經常一手把她抱在懷裏,一手在鍵盤上敲字,也會在寶寶入睡後熬夜趕稿。那時我剛到美國,對美國還充滿了玫瑰色的想象。因爲專業原因,我閱讀的政治哲學論著往往都是關於“個人權利”、“自由”、“民主”等抽象概念的分析。記得第一次跟他一塊去華盛頓參觀國會,看國會裏的意識形態宣傳片,聽到對民主理想擲地有聲的概括:“聚衆成一”(“Out of many, one”),我激動得流下眼淚。怕他看見笑我,趕緊悄悄擦掉。三土的政治評論往往資料詳實,條分縷析,又一針見血。閱讀他的文章慢慢卸去我的玫瑰色眼鏡,讓我看見一個更復雜的美國,揹負着沉重的歷史罪孽和制度包袱。三土的文章揭示美國法治設計上的缺陷、種種壓迫的制度化、以及各種政治力量如何在制度框架下消長和重組等等。這些文章很少像政治哲學論著那樣抽象討論“權利”、“民主”等理想。但通過展示種族性別壓迫如何被制度化、制度又如何深刻地影響個人生活和社會走向(比如看似合情合理的投票人證件驗真如何剝奪一些選民的選票,選舉人團制和選區劃分如何在“一人一票”表層邏輯下讓某些人的選票比另一些人的選票更有分量,不被人重視的“輸不起法”如何推動美國政治的兩極化),這些文章往往比抽象的概念分析更直觀、真切地道出“權利”、“平等”、“民主”等等價值的真意。
三土的政論往往處理的都是很沉重的問題:人的權利如何被漠視和踐踏,平等共治的民主理想如何被金錢、權力、偏見侵蝕。但他的文章從不陷入犬儒主義,或者和稀泥地總結說“天下烏鴉一般黑”。對每一個盤根錯節的問題(墮胎、槍支氾濫、警察暴力等等),他都就事論事,通過追溯歷史和事態演變的過程來正本清源,同時給出自己的判斷和建議。他給讀者傳遞着理想的珍貴和脆弱:離開良性的制度和願意保護良性制度的人們,理想什麼都不是。同時,他也深入淺出地說明制度細節的重要性;可以說,制度細節往往具有蝴蝶效應。《休會任命和權力制衡》,《最高法院與政黨初選改革》以及沒有收入本書但非常值得一讀的《“輸不起法”與美國政治的兩極化》等等,充分展現出制度設計中的毫釐之差往往導致今後政治局面的千里不同,讓人窺見在紛繁的政治、經濟、媒體環境中追求正義的複雜機理。
雖然我和三土都研究政治問題,但我接受的是政治哲學(political philosophy)訓練,而三土在此之外還接受了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訓練。政治哲學研究理解社會正義需要的概念以及社會正義的基本原則,而政治科學研究制度設計的細則,政治與經濟、法律、人口、文化、國際關係等等方方面面的具體互動,及其帶來的種種現實結果。三土作爲政治科學學者遠比我這個政治哲學學者接地氣。這些年來,閱讀他的文章讓我對民主的理解不斷超越“聚衆成一”式的宣言。
二、究窮象塔屠龍術
對美國政治的觀察只是三土政治關切中不那麼“核心”的一環。更讓他感興趣的還是政治哲學中的理論難題。這些難題既包括自由主義傳統下曠日持久的核心爭議,也包括跟時事政治緊密相關的道德困境。前者例如:如果我們相信自由、平等、經濟繁榮、甚至美德和愛都是值得追求的重要價值,爲什麼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中我們應該優先保護自由而不是分配平等、經濟效益最大化、或推動美德的養成呢?後者例如:言論自由,與“政治正確”、亦即利用社會壓力甚至各種規則去限制看似道德上站不住腳的言論,是兼容的嗎?承認嬰兒的生命權,就意味着否定女性的墮胎權麼?如何平衡鼓勵女性講出私人空間中遭遇的性侵,和保護被指控者的名譽不遭受無妄破壞的權利?這些政治、道德難題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我們很可能都在某些時刻停下來想過其中的某些問題。但作爲難題,在這些問題上的對立觀點似乎各有其理。面對這些問題,因爲理不清頭緒,一想就頭疼,人們容易要麼陷入懷疑或冷漠(覺得這些問題或許沒有對錯,不必較真),要麼陷入很深的無助感(相信有對錯,卻因爲講不明道理而感到無力、委屈)。
三土處理這些難題如剝繭抽絲,能把看起來再錯綜複雜的謎團也理出個頭緒。雖然不同的理由在把我們往不同的方向撕扯,他會把這些理由逐次考慮進來,擺放在我們思考過程中的恰當位置,把我們一步步引導到他希望我們接受的結論。希臘古諺說:修辭像一隻溫柔的手,攬你入懷,讓你心甘情願地相信修辭家兜售的信念;而論證像一個握緊的拳頭,如果它前提爲真又邏輯有效,即便你在情感上不想接受它的結論,你也必須接受。如果用來傳遞有價值的理念,美好的修辭和嚴謹的論證都很有益。三土是那種不訴諸修辭而僅依靠論證的辯手。三土多年前寫的那篇《同性婚姻、性少數權益與道德滑坡論》在同志朋友圈中有很多讀者。文章反駁那些將同性戀與戀童癖、屍交、人獸交等同起來的常見論調。我不止一次聽朋友說到,他們遇到這種滑坡論時就把三土的反駁砸過去,對方往往啞口無言。反對歧視的有力論證本身就是對被歧視、壓迫、邊緣化的羣體的賦權。
三土駁斥了對MeToo運動的常見反調,尤其是最深入人心的對MeToo運動的擔憂:MeToo運動是狂歡式的“指控即定罪”,默認了被指控者有罪,容易冤枉好人。三土闡明瞭“無罪推定”是刑法中獨特的證據標準。在MeToo事件中不採用“無罪推定”並不意味着採用了“有罪推定”。而且對任何惡行的“定罪”都無法完全避免冤枉好人的可能性,但這不意味着我們應該放棄“定罪”(幾乎沒人因爲刑法審判可能冤枉好人就要求社會拋棄刑法審判);如三土所說,“真正的問題永遠是……如何在假陽性結果與假陰性結果之間找到最合理的平衡”。MeToo運動在短短幾年中通過此起彼伏的對性騷擾的揭示讓公衆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看似正常的職場和人際交往下潛藏的冰山。它不僅推動整個社會對性騷擾問題的廣泛認知,並通過集體發聲實現對施害者追責、爲受害者賦能。與此同時,有一系列數據表明虛假性侵指控的比例不比其他類型的指控(盜竊、人身傷害等)高。在這樣的背景下,“儘管虛假性侵擾指控的情況確實存在,但對此不成比例的恐慌,其實只是父權社會文化一手締造的庸人自擾”。
三、蛇毛兔角多雞犬
大多數讀者都是通過閱讀三土關於美國政治的文章而知道他的,但三土心底的願望是成爲一位融會貫通各個哲學領域的哲學家。三土把觀察政治現實、鍼砭時弊、反思制度當成一種責任,而思考哲學纔是他的樂趣。如果想了解一個人,不要看他在做什麼,而要看他樂做什麼。知道一個人的職業,我們往往對這個人還是知之甚少,而知道一個人真正的愛好,我們跟他就走近了很多。從這個角度講,《空談》的下卷《蛇毛兔角多雞犬》是全書“最三土”的部分。這部分看起來比較散亂,有關於宗教的、中醫的、進化論的、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大都篇幅短小,讀來有趣。但其實這些雜亂的短文背後藏着三土對“哲學”的哲學反思,以及他對善好人生的“終極理想”。
對“哲學”的哲學反思試圖回答哲學應該研究什麼,把哲學跟其他學科區分開來的獨特之處是什麼,哲學已經或最終會被科學取代嗎,哲學研究的方法應該是怎樣的,等等。在哲學領域中,這種對哲學本身的哲學探究被稱爲“元哲學”。三土正在將他的想法寫成學術論文,但在本書第三卷中提到了他的核心想法:“哲學問題根本上是規範性層面的問題(normative questions),而非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旨在研究的描述性層面的問題(descriptive questions)。描述性,有時也稱‘實然’,追問的是我們身處的經驗世界(包括自然、社會,以及個體的內心世界)之中究竟存在哪些事物、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哪些事件,以及作用於這些事物及事件的因果法則或統計規律;規範性,有時也稱‘應然’,追問的則是我們應當相信什麼、應當如何行動,以及當我們在思考應當相信什麼和如何行動時究竟應當出示怎樣的理據和完成怎樣的論證。”
《上帝與罪惡問題》、《“大造必有主”嗎?》、《簡析康德“上帝存在的道德論證”》等幾篇文章都在從不同角度展現“上帝是否存在”這個看似“實然”層面的問題(上帝存在還是不存在?)爲什麼其實是一個“規範”層面的問題(當上帝的存在既不能通過經驗來證實又不能通過經驗來證僞的情況下,我們是不是應該相信上帝的存在?)。這些文章一方面梳理了歷史上關於上帝存在的種種證明和反駁,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三土自己的判斷:上帝對於解釋世間看似精巧的萬物或證成道德的約束力都不是必要的,而世上那麼多無端的痛苦跟存在一個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很難兼容。
在《霍金悖論》中,三土剖析不少大科學家不僅是“哲學盲”而且“反哲學”這一現象:它體現的是科學沙文主義。這些科學家們根本的盲點在於看不見“實然”之外,“應然”問題(我們應該相信什麼、應當如何行動)真實存在而且對人類社會至關重要。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一個人中槍死亡,精通人體科學的法醫可以告訴我們受害者幾點中彈,失血多少,傷口如何影響他身體的其他功能,最終如何導致他的死亡。然而再精通科學的法醫,也無法通過觀察他的死亡而得出“謀殺是一種嚴重的惡,它剝奪了人的基本生命權”。人爲什麼有生命權?其它動物怎麼好像沒有這樣的生命權?生命權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剝奪麼?還是說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比如殺掉一個人可以救五十個人,可以剝奪呢?應然層面的問題不僅包括倫理問題(比如怎樣的行爲、動機、情感纔是善好的?怎樣的制度、法律纔是正義的?),也包括認識論問題(比如在證據有限,或在意見紛繁、相互矛盾等情況下,我們應該相信什麼?),還包括形而上學問題(比如胎兒是人嗎?它們什麼時候成爲人的?如果“種族”沒有生物學依據,那它究竟存在嗎?人類如果不是隻有兩性,那究竟有多少種性別呢?)。很多問題跟“上帝存在與否”一樣,看似是“實然”層面的問題,其實是“應然”層面的問題。而對於一切應然層面的問題,科學再發達,也不能給出答案;它們的答案只有依靠哲學的反思平衡來靠近。所以,探尋應然問題的答案是哲學獨特的領地。只要應然問題持續存在,哲學就不可能被科學取代。
說到底,三土對善好人生的“終極理想”是啥呢?我覺得是一種可以把《空談》的三個部分貫穿起來的人生態度,即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性,去認識、尊重彼此的尊嚴,建設合理的制度,追求科學知識,並在理性的約束下構想科學之外的意義世界。不是啥高大上的東西,是一種樸實又堅定的人文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