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巴嫩各派勢力扶持的政治、軍事團體如山頭林立,不少組織以三個縮寫字母的代號稱呼自己,什麼LAF、NLP、LRP、INM、ADF、AFL、LAA、ALL等等。
2005年後,到2018年爲止,黎巴嫩經歷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其後,這個國家再度跌入新的不幸——2019金融大崩盤,2020港區大爆炸。眼下,以色列—哈馬斯戰爭背景下,黎巴嫩被迫又一次面對哈馬斯的盟友真主黨與以色列之間可能爆發戰爭的威脅。
1970年代中後期,世界上有三個被割裂的首都:柏林、尼科西亞和貝魯特。我已經到過前兩個,現在終於見到了貝魯特。三個城市裏,柏林和貝魯特尤其悲壯,有一種令人心碎的感染力。
1.難民美食
我在貝魯特喫的第一頓正餐,按照旅館工作人員的推薦去了“阿勒頗之家”,點了塔布勒沙拉和翡麥烤雞。前者是典型的黎凡特(地中海東岸地區)涼拌菜,很有家常風味,切得細細的小圓蘿蔔、番茄、黃瓜和三種生菜,沉浸在歐芹、生蔥和檸檬的混合氣息中,清新微酸,點睛之筆是散落其中的石榴籽。跟我在別處喫過的塔布勒相比,“阿勒頗之家”的版本似乎有改良,澆汁清淡,不放烤饢片。
平生第一次嘗試敘利亞菜,想不到是在貝魯特。但再一想,其實也合理。黎巴嫩這個中東小國在獨立前就是“大敘利亞”的一部分,由法國託管,獨立後的幾十年裏一直受周邊國家動盪局勢的衝擊。先說埃及,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義德在回憶錄《鄉關何處》裏寫到好幾個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後離開埃及到黎巴嫩避難的巴勒斯坦基督徒,薩義德的母親甚至在黎巴嫩內戰時期滯留貝魯特許多年。再比如約旦,1971年,約旦國王侯賽因發動“黑九月”驅逐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當時整個阿拉伯世界只有黎巴嫩願意收留無家可歸的巴解民兵,阿拉法特竟然以一名流亡者的身份成爲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實際統治貝魯特西區的“西貝魯特市長”。更不用說黎巴嫩南邊的鄰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從1948年到今天,巴以衝突循環往復,每一次都會波及黎巴嫩。至於敘利亞,“阿拉伯之春”引發的敘利亞內戰從2011年持續至今,已有超過一百萬敘利亞難民湧入國土面積不及敘利亞6%的黎巴嫩,據說“阿勒頗之家”的老闆在逃出敘利亞以前是阿勒頗大學的哲學講師,從這家餐廳受歡迎的程度看,他應該是在黎巴嫩謀生的敘利亞難民中罕見的成功人士。
陌生的糧食品種總是令我感覺新奇,比如被稱爲“江南水八仙”之首的雞頭米、摩洛哥“庫斯庫斯”裏的粗麥和青海甜醅裏的青稞粒。翡麥也是一樣,口感和味道都有趣,我最終沒能喫完大塊的烤雞,但作爲配角的翡麥卻喫得一顆不剩。它是黎凡特和中東的一種古老穀物,由綠色硬粒小麥經過烘烤和揉搓後製成,搭配烤肉要比米飯或土豆更出色。

餐館生意火爆,佈置也喜慶,掛滿紅紅綠綠的聖誕裝飾,這在土耳其或其他中東北非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伊斯坦布爾最歐化的貝伊奧盧區時髦高檔的加拉塔郵輪港購物區,也只敢低調放出用虛線裝飾的聖誕樹,只見淡淡輪廓而沒有色彩。
一邊喫飯,我全程都在觀察旁邊一張大桌的一家三口,女主人三十歲左右,戴頭巾,身材富態,其實從眉眼看應該是個美女,這家人明顯是中產或富裕階層,或許不太需要體力勞動,於是發了福。男的也很年輕,正眼不看她,自顧自抽着水煙玩手機。兒子與父母有些單線交流,但夫妻之間零交流。待我喫到一半,呼喇喇來了七八個大人小孩,一大桌頓時擠擠挨挨坐滿了,其中一個年輕女子徑直走到先來的那家男人面前與他寒暄,然後拿過他手中的水煙吞吐幾口再還給他。之前服務生端來水煙伺候男人時先自己吸了幾分鐘,讓炭燒到火候剛好,再拔掉木菸嘴套上一次性塑料嘴交給顧客。我猜想,那女人只能是男人的親姐妹,不然無法解釋她怎能毫無顧忌地把男人抽了一半的菸嘴放進自己嘴裏。親友團到齊,那對夫妻終於有了第一次對話,我看他們倆的眼神表情,看着對方說話時我不曉得該形容那是輕蔑、冷漠,還是恨。
2.戰爭疑雲
2023年聖誕節前,我從土耳其第四大城市阿達納飛到貝魯特時,哈馬斯10月7日對以色列的襲擊已經過去兩個多月,戰爭在加沙激烈進行,不時傳出慘烈的消息。但在兩百公里外的黎巴嫩,戰爭還只是懸浮在地平線上的疑雲,沒有人知道它會不會突然降臨,以及何時纔會降臨。這種懸疑幾乎是一場心理戰,讓我這個不合時宜的遊客覺得刺激又茫然,但對於早已見識過戰爭的貝魯特人來說或許根本不算什麼,戰爭的懸念只是疊加在日常生活之上的另一種常態,因爲據說在貝魯特,“不穩定是一種身份認同”。這句話裏包含了一種本地生存哲學,外人未必理解得了。貝魯特人的生活裏向來不缺少動盪因素,於是他們變得好像喜歡與動盪共存。薩義德的母親年輕時曾經在貝魯特度過了她一生中最好的時光,若干年後被迫逃出埃及當流亡者時,她選擇了貝魯特作爲棲身之地。在黎巴嫩內戰正酣時,她不聽家人勸說,拒絕移民美國,寧願孤身一人在貝魯特過着沒有電話、沒水沒電的艱苦生活。這種對“Hard模式”的堅持,在我看來很貝魯特。
認識了翡麥,又看到當地食客的家常短劇,我心滿意足地走出“阿勒頗之家”,沿濱海路向不遠處的橄欖灣走去。這裏是市中心北端的濱水商旅區,弧形的地中海岸邊闢出一條木質行人步道,向東延伸到遊艇俱樂部,向西延伸到內戰前很有名的聖喬治飯店。海邊步道的高度低於濱海路,兩者之間有落差的空間被設計成一系列錯落交疊的平臺,讓人聯想到層層海浪,平臺下是一層樓高的商業空間,我看到美國的星巴克、法國的保羅等連鎖餐飲、零售店品牌。
橄欖灣看起來是個國際化的商業地產項目,它由美國建築設計師史蒂文·霍爾設計,霍爾的前作包括受馬蒂斯畫作《舞蹈》啓發的北京當代萬國城MOMA和“躺平的摩天樓”——深圳大梅沙萬科中心。
貝魯特不是一個賞心悅目的城市,但在此刻,日落剛過,城市細節在逐漸轉暗的光照下顯得曝光不足,從橄欖灣回望貝魯特的天際線,我發現它其實沒有丟失一座海濱城市與生俱來的美。儘管從2020年8月貝魯特港區大爆炸以來持續至今的電荒導致岸邊不少高樓只能點亮零星燈光,但不可否認這些樓房連同它們在海灣中的倒影與遊艇一起構成了一幅典型的地中海沿岸城市風景圖。

只有仔細觀察,才能看出這個畫面裏的恐怖之處。
岸邊的樓羣中有一些看上去較新,應該是1990年黎巴嫩內戰結束後新建的,也有一些明顯有着1970年代或更早的建築風格,應該是戰前的老建築,歷經長達15年的戰爭屹立不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兩座老牌旅館:聖喬治飯店和腓尼基飯店。前者建於1930年代法國託管時期,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貝魯特的黃金時代它是城中首屈一指的豪華飯店,碧姬·芭鐸、馬龍·白蘭度、伊麗莎白·泰勒、理查德·伯頓、約旦國王侯賽因、伊朗末代國王巴列維和王后索拉雅都曾在聖喬治做客。冷戰時代,聖喬治贏得了間諜窩的名聲,其酒吧被稱爲“情報旋轉門”。著名雙面間諜、“劍橋五君子”之一金·菲爾比離開英國軍情六處後移居貝魯特,以駐外記者身份爲掩護替蘇聯蒐集情報,曾在聖喬治飯店的酒吧度過許多個夜晚。菲爾比身份敗露、叛逃蘇聯之前最後一次露面就在聖喬治,幾個月後他在莫斯科出現。

從1975年內戰爆發到現在,聖喬治飯店一直處於停業狀態。把視線移向一街之隔的腓尼基飯店,我看到1961年開業的它舊貌換了新顏,掛上洲際酒店集團牌子重新營業。但如果把視線繼續移向腓尼基飯店背後那座更高的建築,驚悚一幕便出現了:整座大樓不見任何燈光,黑黢黢的窗洞全都沒有玻璃,酒店外牆被燻得發黑,像遭過火災,最觸目驚心的是,十幾層以上的牆體竟被打穿,露出一個個大洞。它就是1974年開業的假日酒店,只運營了一年多,貝魯特就從烈火烹油的繁榮巔峯直墜地獄烈火般的戰爭深淵,這座酒店成了黎巴嫩內戰最有標誌性的廢墟和紀念碑。
3.酒店大戰
我在白天再次走向這片高檔酒店集中的區域,希望能近距離觀察假日酒店的現況。透過鐵絲網,清楚看見混凝土牆上的塗鴉和數不清的彈孔,地面層野草瘋長,高層窗洞裏探出灌木的綠芽。這座千瘡百孔的摩天樓只剩了一具空殼,頂層明顯有個鼓出來的圓盤結構,想必是旋轉餐廳。五十年前,在它作爲酒店的一年多時間裏,金色的窗簾掛在四百間客房裏的每一間,室內裝修大量使用銀色、亮黃色塗料和飾品,迎合阿拉伯世界流行的奢華風。起初,它代表貝魯特曾被譽爲地中海明珠的黃金時代,卻不幸成了殘酷內戰的象徵。它讓我想起柏林最繁華的商業區選帝侯大街上那座被二戰炮彈削去半邊的德皇威廉二世紀念教堂,戰後它既沒有被拆除也沒有被複建,而是保留殘骸,化身爲戰爭紀念碑。
諷刺的是,假日酒店沒有被拆除也沒有被複建,並非因爲它被有意識地留作內戰紀念物,而是因爲股東們在如何處置這座廢墟的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一方傾向於把它修復成公寓樓,另一方傾向於徹底拆除並另起一座全新的大廈。於是假日酒店在戰後只能繼續扮演鬼樓角色,偶爾,一些年輕人翻越圍擋溜進酒店,在廢墟里喝酒狂歡,通宵達旦。幾十年前,他們的父輩或許曾在這裏互相殘殺。

1975年4月,內戰爆發時,還只是一場低烈度的宗派衝突,敵對雙方之一是右翼基督教馬龍派民兵武裝“長槍黨”(簡稱KRF),另一方是左翼穆斯林民兵,包括兩支武裝力量:本土穆斯林民兵“黎巴嫩民族運動”(簡稱LNM)和外來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簡稱PLO)。黎巴嫩國土面積還不到海南島的三分之一,社會內部卻存在巨大差異和對立,各種族、宗教團體極其複雜,有馬龍派基督徒、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德魯茲派、亞美尼亞人、希臘正教徒、敘利亞天主教徒、阿拉維派等,再加上幾大外來勢力: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和1971年約旦“黑九月”事變以來分批次流入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1982年入侵黎巴嫩的以色列軍隊,內戰後期入黎參加戰鬥的敘利亞部隊,以及伊朗意識形態的滲透,各派勢力扶持的政治、軍事團體如山頭林立,有“阿邁勒運動”“真主黨”“雪松守護者”“老虎民兵”等千奇百怪的名稱,不少組織以三個縮寫字母的代號稱呼自己,什麼LAF、NLP、LRP、INM、ADF、AFL、LAA、ALL等等,令人眼花繚亂的“三字經”。
衝突在1975年夏季升級爲第一階段激戰,長槍黨控制了包括酒店區在內的貝魯特東部大部分地區,導致東貝魯特的穆斯林平民遷往西部,西貝魯特的基督徒遷往東部,城市分裂成兩塊,一條界線逐漸清晰。


進入秋季,最激烈的交戰就發生在酒店區,左翼穆斯林民兵發起反攻,試圖奪回對酒店區的控制權。1975年10月起,到1976年3月止,雙方爲爭奪具有戰略價值的高層建築控制權展開殊死戰鬥,聖喬治飯店、腓尼基飯店和酒店區最後一家新酒店希爾頓(它未能開業便淪爲狙擊手陣地)都被捲入這場耗時五個月的“酒店大戰”,但26層高的假日酒店纔是最令人垂涎的目標,因爲高度決定一切,誰控制了假日酒店,就等於控制了它周圍的地區。酒店區恰好處在貝魯特東區和西區分界線上,長槍黨狙擊手在假日酒店高層就位,把這家酒店作爲襲擊穆斯林聚居區西貝魯特的基地。穆斯林民兵要想扭轉這個劣勢,就必須奪取假日酒店,把它變爲向基督徒聚居區東貝魯特傾注火力的陣地。
酒店大戰,本質上是一場針對城市制高點、最佳狙擊點的爭奪戰,這也解釋了爲什麼假日酒店遭受的炮擊集中在高層,那裏是狙擊手的地盤。
4.藝術休戰
施隆多夫拍攝於1981年的《僞證》(Die Fälschung)讓我看到內戰期間貝魯特假日酒店的樣貌,影片根據尼古拉斯·玻恩的同名小說改編,講一個對婚姻心灰意冷的西德記者去內戰中的貝魯特採訪,故事背景恰好設在1975-1976年“酒店大戰”期間,在我看過的一批涉及黎巴嫩內戰的故事片裏它是唯一一部在戰地實地取景的,非常真實。有一場戲,男主角和他的搭檔攝影師被允許進入假日酒店採訪狙擊手,從一個被火炮擊穿的牆洞裏往外看,樓下的市中心已被催毀,長槍黨領導人卻對記者談起戰後重建,說市中心的蘇克(Souk,阿拉伯城市裏的傳統集市,類似巴扎)太過陳舊,等將來和平了,應該把整個市中心拆掉,規劃一片新的商業區。我沒想到,德國虛構作品裏這一番出自長槍黨之口的誇誇其談,如今竟然在現實中兌現,蘇克的原址上出現了一座現代化的購物中心,我看到很多熟悉的國際品牌店,從耐克到愛馬仕。雖然這座購物商場名字就叫“貝魯特蘇克”,但我相信它跟歷史上的蘇克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取其名字而已。
從古代腓尼基人的時代起,這一帶就是城市商業中心。1990年代,貝魯特戰後重建,市中心變身爲大型房地產項目,前總理拉菲克·哈里里創建的貝魯特中心區開發和重建公司(法語縮寫爲Solidere)合法徵用了市中心大部分土地,先前的產權持有者獲得公司股份作爲補償,棲身在戰爭廢墟中的非法居住者被驅逐。接着,市中心被夷爲平地,再啓動填海造地工程,開闢出超過50萬平方米的新土地。哈里里政權曾經夢想把戰後黎巴嫩建設成中東的瑞士,誰料到哈里里本人2005年在一場針對他的卡車炸彈襲擊中喪生,聖喬治飯店和腓尼基飯店也被炸彈傷及。

2005年後,到2018年爲止,黎巴嫩經歷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內戰沒有重演,有過一次接近內戰邊緣的試探(2008)、一次真主黨與以色列的戰爭(2006)、敘利亞難民潮的衝擊(2011年後)、48次爆炸和21次針對政界人士、黨派領袖、媒體記者、軍官和情報人員的暗殺。其後,這個國家再度跌入新的不幸——2019金融大崩盤,2020港區大爆炸。眼下,以色列—哈馬斯戰爭背景下,黎巴嫩被迫又一次面對哈馬斯的盟友真主黨與以色列之間可能爆發戰爭的威脅。
危險性讓這個城市獲得存在感,因此貝魯特的日常總有一種荒謬感,即使在和平時期,戰爭的威脅也始終在不遠處徘徊,但即使在戰時,這裏的人也依然能找到內心的平衡。或許正因爲他們學會了與荒謬相處的藝術,當年那場內戰才能綿延15年之久,像一場停不下來、讓人不能自拔的噩夢。
這種荒謬感會讓文藝家興奮和迷戀。納粹德國戰敗後,柏林還是一片廢墟時,羅西里尼及時地以柏林作爲外景地拍攝了《德意志零年》。他知道鏡頭裏被毀滅的城市有一種力量。施隆多夫彷彿是羅西里尼的接班人,敏銳地意識到必須實地拍攝《僞證》。它與《德意志零年》的一大差別在於,拍攝過程中,貝魯特的戰事仍在進行中。爲了能在貝魯特拍攝,導演會見了所有交戰各方並達成“藝術休戰”——類似於“奧運休戰”,交戰各方被施隆多夫說服在某個地區同時停止戰鬥,然後劇組入駐,在戰地拍攝虛構的戰鬥,待拍攝結束,真實的戰鬥又會重新啓動。據說參與拍攝的羣衆演員都堅持使用真槍實彈,其中一些人結束白天的拍攝後就會拿着拍攝時用過的槍迴歸各自所屬的民兵武裝,投入晚上的戰鬥。
有一幕戲的內容是記者在貝魯特海灘上發現燒焦的屍體碎片,劇組使用了塑料假肢道具,一個當地孩子見狀問劇組,爲什麼要用這種人造材料,他提出可以爲拍攝提供真實的東西。第二天,孩子帶來了真的人類遺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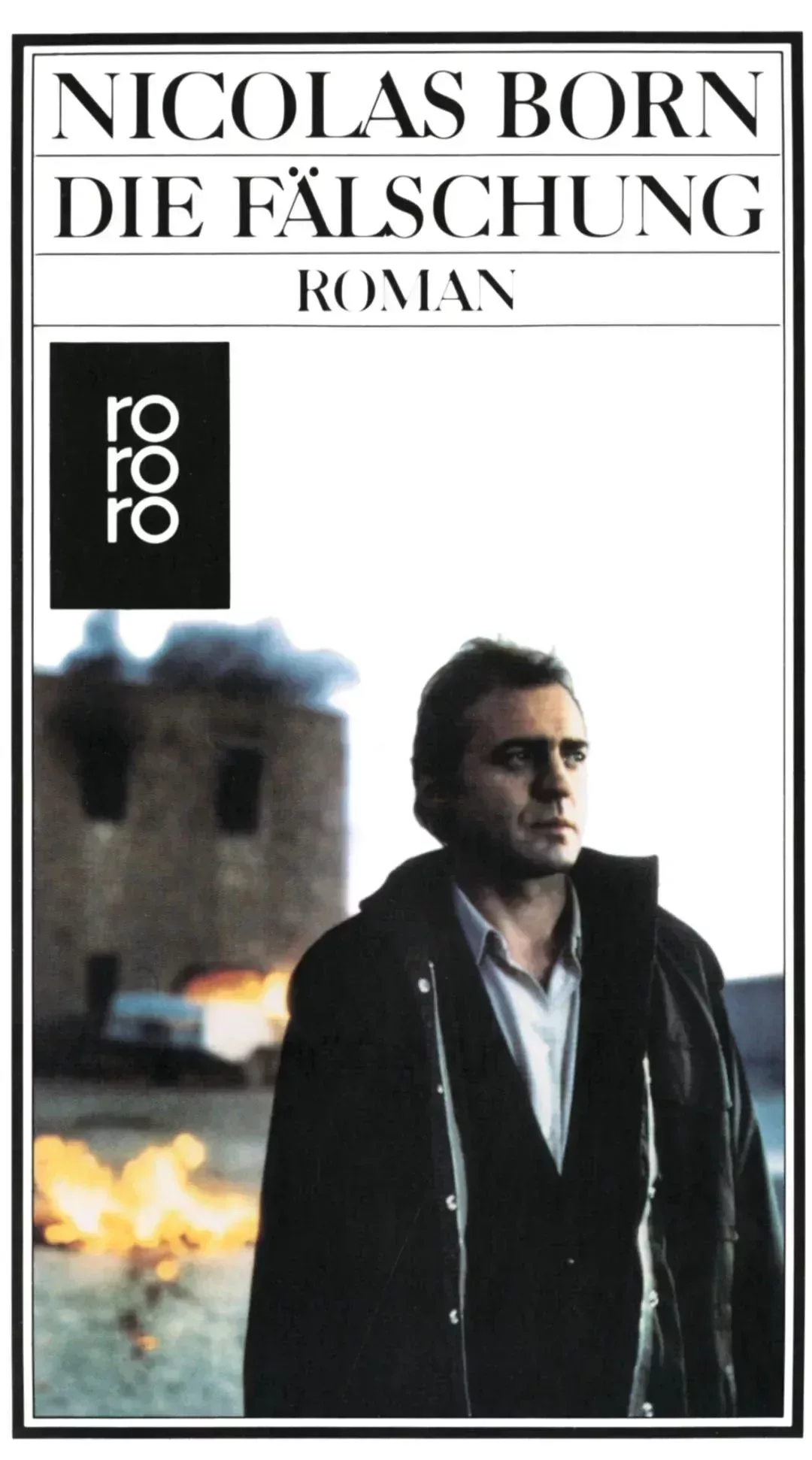
5.中東卡門
1970年代中後期,世界上有三個被割裂的首都:柏林、尼科西亞和貝魯特。我已經到過前兩個,現在終於見到了貝魯特。三個城市裏,柏林和貝魯特尤其悲壯,有一種令人心碎的感染力。
貝魯特很像某類愛情悲劇裏的主角,熱烈,真實,性感,雖然有暴力傾向,但令人着迷,欲罷不能。相比中東北非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貝魯特從來沒有跪在單一意識形態腳下讓所有女性遮住臉部,你甚至可以在濱海路上看到露肩、露臂、露大腿跑步健身的女子,開放程度令人側目。當然,從頭到腳裹得嚴嚴實實的也比比皆是,這很正常。
1956年,作家簡·莫里斯還叫做詹姆斯·莫里斯並且還在爲《泰晤士報》當記者時,曾以男兒身遊歷蘇伊士運河危機籠罩下的貝魯特。他在《塞琉基亞的集市》裏把貝魯特比作放蕩不羈的卡門:“她就在那裏,披着一頭捲髮,甩動荷葉邊的裙子,是衆多城市中的卡門……她給人這種感覺:儘管享受過一百萬次風流韻事,卻從未真正愛過誰。她迷人得像一個肉感的妓女,或一個來路不明的富家子,像茉莉的一縷香氣,或炫目的一樁豔情。”莫里斯寫下這些文字時,距離內戰爆發還有將近二十年,腓尼基飯店和假日酒店還不存在,但貝魯特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和危險性都已經很明顯。
歷史學者安德魯·阿桑在《黎巴嫩:一個支離破碎的國家》中發問:“在非常時期想方設法過上正常的生活,這意味着什麼?感覺又如何?經歷過這些非常時期的男男女女,生活中有着哪些歡樂和期許、恐懼和焦慮、抱負、希望、失望和悲傷?他們如何努力掌控自己的生活,不讓歲月被不可預測的潮流沖走?”

有一天,我穿過昔日分割穆斯林西區和基督徒東區的“綠線”,到東邊的亞美尼亞街溜達,在平民食雜店買了些食物:巧克力(3.6美元或32.3萬里拉)、蔬果(花菜、小圓蘿蔔、黃瓜、石榴,一共17.6萬里拉)、火腿和意麪(47萬里拉)、雞蛋(4只,10萬里拉)。走出小店,心算着黎巴嫩的物價水平是否比土耳其和中國高,大概高多少。這時聽見後面有個女人衝我的方向大聲說話,講的是阿拉伯語。我以爲她在跟別人說話,就沒有轉頭,悶頭往前走。不料身後女人話音更響了,而且變成英語,我突然聽懂了:“Don’t walk!”我趕緊停下腳步,回頭看去,是個戴眼鏡的老太太。她走近我,氣鼓鼓地說:“現在的人真很無禮!”我以爲她在說我裝作沒聽見很無禮,她卻說,剛從醫院出來,那裏辦事的小年輕都非常傲慢,對她這個75歲老人愛搭不理。她說,她有這個病,那個病。我聽不大懂。她的英語令人費解,我只是聽着,應聲附和。我們一起慢慢往前走,一路聽她發牢騷。她說她是亞美尼亞正教信徒。又抱怨藥越來越貴,60粒要36美元。我沒聽懂是什麼病,什麼藥,只能附和:太貴了!陪着她走了大約十分鐘,我們在一個路口分手,互道聖誕快樂。不知爲何,心裏有些難過。我在這個城市不認識任何人,無從知道普通人的生存狀況,這位長得像特蕾莎嬤嬤的老人卻不把我當外人,對我傾吐的那許多怨言似乎剛好跟安德魯·阿桑在書裏提出的問題對得上,儘管並不能解答那些問題。

很奇怪,在這個“支離破碎的國家”,總體上依然存在着堅定的集體認同。比如被稱爲“黎巴嫩的靈魂”的歌手菲魯茲,半個多世紀以來她一直是這個國家的國民歌后,我在貝魯特的每一家唱片店都看到她的舊專輯《黎巴嫩萬歲》被擺在醒目位置,無論是國際連鎖店還是二手黑膠唱片店。也許,戰爭疑雲下的黎巴嫩又到了一個危難關頭,菲魯茲的歌聲再次讓黎巴嫩人找到共鳴。初聽她的《致貝魯特》時我嚇了一跳,旋律那麼熟悉,竟然是根據羅德里格斯作曲的《阿蘭胡埃斯協奏曲》第二樂章填的詞。往下聽,感覺慢慢好起來,不僅詞曲合拍,情緒也跟音樂契合得很好——“貝魯特,是用人民的靈魂釀成的酒/用汗水製成的麪包和茉莉/可是爲何如今它的味道/變成了烈火和硝煙?”
